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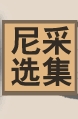
|
悲剧的诞生 第二十四章 |
|
在歌乐悲剧的特殊效果中,我们要举出梦境幻觉:我们靠这幻觉,才得免于陶醉音乐中,并与之合一,同时,我们的音乐激情,便在这梦境领域以及其间的鲜明的缓冲境界,得以尽量渲泄。因此,我们认为:正是通过激情的渲泄,剧中的缓冲境界,即戏剧本身,才从里及表地显得了如指掌,达到一切其它梦境艺术所不能翼及的程度;所以,既然这种艺术仿佛附在音乐精灵的翅膀上凌空飞去,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力量达到最高的扬举,从而梦神与酒神的兄弟般的同盟,就是这两型艺术的目的的高峰。 当然,正当音乐从内部予以阐明之际,梦境的光辉画景是不能达到低级梦境艺术的特殊效果的。史诗的雕刻的效果,强使静观者默然神往于个性化的境界,在戏曲方面就不能实现了,尽管戏曲是更生动更鲜明。我们欣赏戏曲,用洞察的慧眼深入其内部激动人心的动机境界;但是我们仍觉得,仿佛只是一个象征世界掠过眼前而已,我们自以为已经揣摩到它的最深刻意义,但愿拉开它,像拉开帐幔,看看幕后的真相。最鲜明如画的地方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因为它好象显露了,而同时也隐藏了一些东西;正当它似乎以其象征的启示,鼓舞我们去撕破帐幔,以暴露其神秘的背景之际,那充满光辉的景象,却迷住我们的眼睛,阻止它去看深一步。 谁没有体验过这种情况;既不得不看,又同时向往视野之外的东西;谁就很难想象,在欣赏悲剧神话之际,这两种过程明明是同时并存,同时感受的。真正的审美观众会证实我的话;我认为,在悲剧的特殊效果中,只有这种并存现象最值得注意。现在,如果把观众的审美现象转化为悲剧艺术家的审美过程,您不难明白悲剧神话的起源了。悲剧神话,具有梦境艺术那种对假象和静观的快感。但同时它又否定这快感,而在这鲜明的假象世界之毁灭中,得到更高的满足。悲剧神话的内容,首先是歌颂战斗英雄的史诗事件。然而,英雄的厄运,极惨淡的胜利,极痛苦的动机冲突,简言之,西烈诺斯智慧之明证,或者用美学术语来说,丑恶与和谐,往往再三出现在许多民间文学形式中,尤其是在一个民族的精力充沛的幼年时代:——这种莫明其妙的特点从何而来呢,难道人们对这些东西真的感到更高的快感吗? 因为,虽然生活中确实有如此悲惨的遭遇,但这事实很难说明一种艺术形式的起源,设使艺术不仅是自然真相的模仿,而且其实是自然真相的哲理说明,为了战胜自然而创造的。悲剧神话既然主要是属于艺术范围,它也就完全参予一般艺术美化现实的哲理目的。然而,如果它以受难的英雄形象来表现现象界,它到底美化了甚么呢?它绝不可能美化了现象界的"现实",因为它对我们说:"你看这个!留心细看呀!这是你的生活!这是你们生存时计上的时针!" 那么,神话指示出这种生活,是为了替我们美化它吗?否则,我们将如何解释,甚至这样的形象也带给我们审美快感呢?我讨论的是审美快感,我也深深知道:除了审美快感以外,许多这类形象间或还能唤起一种道德快感,例如怜悯,或道义胜利之类。然而,如果你认为悲剧效果完全出自这种道德根源,像许久以来在美学上所认为当然如此,那末,你切莫以为,你因此就对艺术颇有贡献。因为艺术首先必须坚持它范围内的纯粹性。为了说明悲剧神话,第一个要求是:它的特殊快感。必须在纯粹审美范围内寻求,而不应侵入怜悯和恐惧,或道德崇高等领域。然而,丑恶和不和谐、悲剧神话的内容,又怎能唤起审美快感呢? 现在,我们必须勇往直前,跃入艺术哲学的领域。所以,我要重复我上文的命题: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与世界才显得合情合理。在这一意义上,悲剧神话的功能,就在于使我们相信:甚至丑恶与不和谐也是一种艺术游戏,意志便以此自娱,而永远充满快乐。然而,这种难以领悟的醉境艺术的原始现象,在所谓"音乐的不和谐"的特殊意义上,立刻显得无比地明晰,而且可以直接体会;正如,一般地说,唯有以音乐同世界对照,我们对于所谓为世界辩护的审美现象之意义,才能有一个概念。悲剧神话所唤起的快感,与音乐上不和谐所唤起的快感,本是同出于一个根源。酒神祭的热情,及其在痛苦中体验到的原始快感,就是音乐与悲剧神话的共同根源。 借助于音乐的不和谐关系,我们岂不是能够同时把悲剧效果这个难题基本上简化了吗?因为,我们现在明白了,所谓"意欲看悲剧,而同时又憧憬着视野以外的东西"是甚么意思。就音乐上的不和谐而言,我们不妨指出这种心情的特征如下:我们愿意谛听,而同时又憧憬着听觉以外的东西,向往无限的境界,对了如指掌的现实感到最高快乐而神飞天外。这种现象,使我不由得想到:必须把这两种心情看作同一的醉境现象,我们不断地看到个性世界忽而建成,忽而毁掉的儿戏,仿佛原始的快感在横流旁溢,正如玄秘的赫拉克利图把创造世界的力量譬作顽童嬉戏,这里那里叠起石块,筑成沙堆,而又把它推翻那样。 所以,为了正确的估计一个民族的醉境能力,我们不但要想到他们的音乐,而且要把他们的悲剧神话视为这种能力的第二佐证。至于音乐与神话的密切关系,也同样必须设想:一者的蜕化衰落,势必引起另一者的凋败。一般地说,神话之衰微,往往表示醉境能力之削弱。然而,关于这两者,试看德国天才的发展,便毋庸置疑。在歌剧上,正如在我们那无神话存在的抽象状态,在堕落为娱乐的艺术上,正如我们凭概念指导的生活方面,我们都见到苏格拉底乐观主义,它既否定艺术,又虚度人生,幸而还有一些使我们快慰的征兆。虽然如此,但德国精神还睡在深不可测的渊壑中,安然无恙,奥妙莫测,还保持着醉境力量,如同一个好梦正浓的武士;酒神祭的歌声,从这深渊飘送到我们的耳朵,教我们知道:这位德国武士,在快乐而庄严的梦境中,尚且梦着他的原始的酒神神话。你不要以为:德国精神已经永远失掉它的神话故乡,因为它依然清楚地听到灵岛的啼声在诉说故乡的美景。有朝一日,它一旦从酣睡中觉醒,朝气焕发,那时它将斩蛟龙,杀掉狡猾的侏儒,唤醒勃伦希德(Brunhild)①,——那时甚至沃顿(Wotan)②的长矛也不能阻止它前进! 我的朋友,您是相信酒神音乐的,您也知道悲剧对我们的意义。在悲剧中,我们见到悲剧神话从音乐里再生——在诞生时,我们能希望到一切,而忘掉最痛苦的事情。然而,使我们大家感到最痛苦的,是德国天才离家去国,为狡猾的侏儒们效劳,屈辱久矣!您是明白我的话的,最后您也将了解我的希望。 ①德国神话史诗中之一女王。 ②德国传说中一武士。 |
|
□ 作者:尼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