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拜占庭的“展示”研究
朱迪·海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9期
【原文出处】《古代文明》(长春)2008年3期第74~82页
【作者简介】朱迪·海琳,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
【关 键 词】拜占庭的“展示”/自觉意识的/世俗的/被禁止的
既然所有社会都寻求各种方法来展示它们的特征和理念,那么拜占庭就不是唯一的发展出至少3种“展示”类型的国家了。第一种是公示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展示”:大教堂、宫廷服饰、宗教祈祷礼仪及庆典上的队列游行,这些都试图给观众以帝国庄严尊贵的印象。第二种是日常生活方面更为世俗的“展示”形式,如拜占庭人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自由人与奴隶,家长权的理念,所有这些理念都凭借“展示”而得以宣扬和强调。第三种是被禁止的“展示”,这种被禁的“展示”通常是隐匿的,这类展示可以通过那些从未根除的传统探寻其踪迹。尽管有当权者的极力阻止——但是季节更替的节庆仪式,对于星相运程的探究,仍旧常常与拜占庭人在命运机缘方面的信仰相联系,也仍旧常与拜占庭人认为某些人具备预测及影响历史进程之能力这一观念(这必须被正确地理解)相联系。这类的“展示”常常与古老的习俗相关联,这种关联并非源于它们最初的目的,而是源于它们总是被重复地实施。
一、具有自觉意识的公开展示
如果我们从拜占庭“展示”中最具自觉意识的方面开始,会发现其中一些是有道理的,而另一些则是荒谬的,不过它们都是拜占庭世界的组成部分。许多的展示是以拜占庭高度发达的教育体制为基础的,这种教育体制的内容包括七门人文学科的古典课程。这些课程在1000年中一直是帝国所有高深知识的基础。当拜占庭的知识分子面对那些深植于古典世界的知识时,这种承袭于希腊罗马实践的教育体制给予了他们强大的自信。本人以为,有一点值得强调,一种认为古典知识极具价值的深刻理念,促使同样的教育体制不断地鼓舞着大约35代的学者。这一教育(体制)囊括了从诗歌写作到肢体损伤包扎术、从哲学到兵法、古代戏剧、法律与正义的原则以及兽医学、天文学、数学和历史学在内的各种知识领域。
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体制,是因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详细地记叙了他们的学习经历和卓越的技艺。我们可以对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数量进行具体地个案研究,他们可能是在任何一段时期(300年)进入这一群体的人,我们可以得知他们是多么微小的一个阶层。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获悉,有多少古希腊原始文本得到复制,并能够追寻到一些已遗失文本曾经存在的痕迹。但是这点只能提醒我们,已经遗失的拜占庭历史证据有多大数量。例如,我们都知道一个10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教师,他的书信宴飨着现代拜占庭学者,揭示了有关其嗜好的信息,这些存留至今的信函表明了他的教学方法和成就,可我们却无法得知其姓名。而既然能有一个我们不知其名的教师,就必定存在另外十个教师,但他们的书信没有被收集到,或许他们的学生也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此外,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学者与他人通信时,① 通信的对方领会其心意,也会以同样高雅的古希腊方式回信。由于太多文本的轶失,我们不能恢复他们之间通信的历史原貌,不过这类通信的确存在。
例如:一些在斯图迪乌修道院的圣狄奥多勒(St Theodore of the Stoudios)② 在世期间一直与其通信的上层社会的女性,因在该修道院被驱散至不同流放地期间对修院的资助而受到感谢。狄奥多勒的致谢信函得以妥善收藏,但是其通信对象的那部分信件却遗失殆尽。如果修女卡西娅与那个同狄奥多勒通信的卡西娅确为同一人,那么尽管她的一些隽语和赞美诗幸运地存有副本,但是她的大量书信却毫无记录。仅从书信学方面看来,更多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想要这样称呼他们的话——进行着一种特殊形式的书面交流,许多初级教士和世俗官员接收到来自诸如迈克尔·塞勒斯这样的大人物的信件时,会以同样的阿提卡希腊语回信,他们通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这种语言。
稍晚的时候,出现了方言版的文本,这些文本是专为那些认为古典希腊语难以掌握的人们准备的。(这种现象)表明读者群需要读一种比《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History of Niketas Choniates)③ 更通俗易懂的版本。在拜占庭,人们的读写能力似乎很高——至少到13世纪为止,一直高于西欧很多。这不仅以基督教经典文本和教会文献为依据。但凡接受过些许教育的人都知道荷马的诗歌,他们或许还牢记着古典文学作品。对于提及古希腊作家——特别是诗人和戏剧作家——的文献,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使用它们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了整理。正如我们所知,有知识的地方就会有展示的形式。
对异教文学的深刻理解和对异教古代神祇、哲人、英雄和反派人物的认识,激发拜占庭人去研究在整个基督教时期伫立于拜占庭城市中的雕像。这种理解也鼓舞着8世纪君士坦丁堡的“街市哲人”步出家门,颂读并誊写那些依旧可见的铭文。即便他们误解了这些铭文,援引伪典来求证铭文的渊源,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与现已遗失的历史遗迹相关的信息。同样的理解也鼓舞着13世纪的马克西莫斯·普兰诺德斯(Maximos Planoudes)④ 创作了一篇祈祷辞,乞求上帝在末日审判时免除对柏拉图(Plato)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惩罚,因为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只是由于生活在基督启示之前的时代才所知不善的。
拜占庭展示其教育传统的明显方式是对修辞学的应用:这在讲演辞、书信、布道辞、历史书籍和司法判决中都有所体现。如是,这种方式就会对它所表达的信息有所影响,不过不是影响全部的信息。许多只完成了初级基础训练⑤ 的学生仍然通晓一些修辞学,他们能够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那些未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属于无数默默无闻的即将成为拜占庭知识分子的群体——就像那些为这个文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国家提供服务的人一样。格里摩那的留特布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第二次出使君士坦丁堡时的记录,记载了一次未达成协议、结果惨淡的外交出使,从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瞥见这些人的基本工作:拜占庭皇帝提醒大使留特布兰德,即奥托一世(Otto I)的上述使节发誓不会做使帝国愤怒的举动——拜占庭政府已经对此记录在案,并且可以向留特布兰德展示这个记录。拜占庭帝国认为拥有高度发达的记录保管体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的这种体制在中世纪无可匹敌。不过,尽管与官方记录相关的印章曾记录了许多官员和书吏的姓名与职位,但是由他们发布的文件以及他们的档案系统却没有留存下来。于我们而言,拜占庭皇帝的这个提醒是一个有益的训诫,它提醒我们不要遗忘维持帝国行政运作的受过教育的历代文职官员。
宫廷和教堂是大多数华丽矫饰的仪式发生的场景,行省长官、高级官员、主教和修道院长则以此为典范在各地效仿。通过宫廷礼仪、典礼程式、教会的主要节日以及人生各年龄段的标识性仪式(个人的生命周期由出生洗礼、婚礼或修道誓礼、葬礼等标记),矫饰成为人为设计的、用来引人注目的一种直观的方式。对于丰富多彩的仪礼形式而言,君士坦丁堡无疑拥有最恢宏的舞台,而这些仪礼形式在行省中也一再地重复上演:当皇后伊琳娜(Irene)和她年幼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途径巴尔干的博洛亚城(Berroia)时,随行人员并非士兵而是歌舞艺人,这必然要引起当地人的瞩目,而我确信它确实达到了这一效果。当塞萨洛尼卡的督军(duke of Thessalonike)进入该城时,他也竭力设计了相似的仪礼活动。这种活动也为《蒂马里翁游记》(Timarion)⑥ 的作者所模仿。得胜的将军们在他们攻占的城市中为胜利举行足够盛大的庆祝活动——969年,迈克尔·保特哲斯(Michael Bourtzes)⑦ 和彼得(Peter,一个太监,曾是某位名叫福卡斯者的奴隶,以其前任主人的名字为名)胜利地进入安条克,6年后,约翰·齐米西斯(John Tzimiskes)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当瓦西里二世前往雅典感谢圣母⑧ (Theotokos)在抗击保加尔人入侵时的神佑时,他也必定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入城式,如同他在改建后的帕特农教堂(Parthenon)⑨ 举行的庄严华丽的祈祷式一样。在帕特农的祈祷式中,瓦西里二世授予该城大量银制器皿。
这种对丰富多彩的直观仪式活动的热情,以及对仪式活动具有引人注目的影响力的认识,在一些捐赠者建造自己的画像时以个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霍拉(Chora)修道院中,由狄奥多鲁斯·迈托克特斯(Theodoros Metochites)⑩ 资助下重建的教堂中,身着宫廷服饰的狄奥多鲁斯·迈托克特斯的画像不仅具有代表性,更彰显了他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中以同样姿势出现在画像中的捐赠人(君士坦丁大帝与查士丁尼大帝)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张显了他与阿克塔马(Achtamar)的卡吉克王(Gagik)、成百上千的其他国王、捐赠者、修士和较为少见的修女之间的联系。在镶嵌画、壁画和手稿中,这种对于个人虔诚加以展示的举动确认了个人对艺术作品的责任。拜占庭必定充满了丰富的绘画作品。在帕弗斯(Paphos附近)的安克雷斯特拉(Enkleistra)修道院,修道士尼奥菲托斯(Neophytos)无疑希望激发朝觐者的敬畏之情,为此他将自己的肖像置于天使之间,这样的姿势使朝觐者联想到他得道飞升进入天堂。这种自豪的因素以及自我展示在拜占庭是十分典型的。
另一方面,指导那些投身于独身禁欲生活的修道规则期待见习修士和修女展示他们安于贫穷的义举。特鲁兰会议的第45条规定清楚地表明,根据礼节,那些引荐年轻女子进入修道生活的人不能准许这些女子穿着丝制华服、佩戴金制饰品和珠宝。相应的,她们应当穿着朴素,当她们决定献身于上帝、致力于过禁欲与清贫的修道生活时,应当换上修道服。12世纪的狄奥多鲁·巴尔萨蒙(Theodoros Balsamon)对这一规则进行了评价,他注意到那些经常违反这条规定的人将被当地主教罚以适当的苦修。不过,即使是与世隔离和克己苦修的行为也都归于一种展示。柱头修士、基督愚人(11) (fools for Christ, saloi)以及沙漠圣徒如埃及的玛丽(12) 和斯拜里顿(13) (Spyridon),他们的苦修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展示行为。他们的肖像经常悬挂在教堂和修道院的墙上,即以绘画的方式来赞扬他们的行为。极端主义苦修的盛行——赤身生存在沙漠中、常年赤脚立于高柱之上——表明了基督徒对苦修者的崇拜,并颂扬他们的成就。
拜占庭教会的祈祷仪式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展示行为,弗拉吉米尔(Vladimir)的使节们第一次见证祈祷仪式时的记载反映了这一点。基督信仰的集体性展示行为不仅体现在教堂中,也体现在Hodigitria节(在首都每周举行一次)或Naupaktitissa地区的圣母节(Theotokos,在希腊中部地区每月举行一次)期举行的圣像游行活动中;圣母赞诗(Akathistos Hymns)的吟唱、或者军队出征前的祈福,都强化了拜占庭的一种身份意识,也强化了拜占庭人卓尔不群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属于一个比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记载更为悠远古老的世界。弗提乌斯(Photios)曾阅读过一部“5卷15本的”原始文献,这部书试图将所有的古代著作,包括波斯人、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色雷斯人和罗马人的著作与基督教信仰相联系,指出所有摘录的文献都“宣告了超自然的唯一存在的三位一体”,指出它们证实了“基督徒的神圣信仰”。然而即便是弗提乌斯也没有查证出这部7世纪作品的作者之姓名,我们却更已经遗失了他所有的作品。
拜占庭对正确释义基督教神学方面的自信,也部分地来自于对古代哲学概念和辨证方法的使用,这种概念和方法已经融入神学并增强了信仰(的影响力)。特别是由笔名为狄奥尼索斯的人(14) (Ps-Dionysios)构想、由忏悔者马克西莫斯(Maximos)发展的有关上帝神格的神秘主义认知,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进展,在基督教的外衣下巩固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分支的发展。在8世纪,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方法与圣像共同使用于宗教崇拜中,他曾强调一定的文本能够使人的心灵升华至更高尚的理解境界,他也曾强调对宗教画的凝视与沉思如何具有同样的功效。至14世纪,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成为支撑着静修派(15) (Hesychasm)的基础,以达到将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的理解升华到与上帝相同一的神学境界(theosis)。通过苦修沉思和肉体上的严苛历练,修士可能经历如变容般的启示,正如基督在塔泊尔山(Tabor)上为人所见那样。
所有这些自觉的展示行为,都在诸如加冕礼、皇室婚礼等重大庆典仪式中融为一体,1180年为阿列克修斯二世·科穆宁与法兰西的艾格尼斯一安娜所举办的婚礼庆典所示——整个庆典充斥着为向安娜致敬而创作和诵读的祝婚辞,祝婚辞中华丽的辞藻俯拾皆是,更有为宾客准备的场面宏大的娱乐节目以及大肆铺张的狩猎活动和盛宴,为她举行的接风仪式及订婚礼,场面宏大。在这些场面中,拜占庭无疑展示了它自己,它也十分相信这种展示能够使它更加引人注目。
二、世俗生活的展示
拜占庭展示的第二层更为世俗化:一个明晰的社会分层是以一种二分理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存在于自由人与奴隶、罗马人与异邦人(原文用“Barbara”,罗马人通常用这一名词指代非罗马人,过去统译为蛮族——译者注)之间。这种理论包含以下的理念,即某些人有责任去统治,而某些人则有义务服从统治。在每个拜占庭家族中,家长权是十分鲜明的。太监作为介于男性女性之间的一种必要的第三性,则是重要的社会角色,其中许多人位居要职,主管宫廷礼仪,掌握皇帝的私人生活空间,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和声望。
在拜占庭,没有人质疑男性的统治地位,他们统治着自己的家人,决定子女婚配的适当人选。尽管教会可能极力主张基督徒对奴隶要施以仁慈,但是无人质疑下等人的生存条件,“下等人”可以被严酷地殴打和惩罚。如果他们被抓获偷盗,会被砍掉一只手以示惩罚。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中,迪米特里欧斯·库马提安努斯(16) (Demetrios Chomatianos)阻止一个贵妇人砍掉一个惯偷奴隶仅存的手。受到同样处置的还有太监,他们也有可能被迫“扮演令人作呕的嗜男色者”,这种行为遭到圣愚者安德莱阿斯(Andreas)的严厉斥责。许多书面遗嘱中包含对奴隶致谢的词句,这削弱了关于社会地位、出身特权、主人与奴隶的自然秩序的观念:在主人死后,这些奴隶不仅获释得到自由,而且还被赠予土地、家具以及衣服等个人物品。但是这些个体性的仁慈行为对削弱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之间基本区分的观念功效甚微。
对界线分明的社会分层理论的认同及对家长依自己意愿处置其财产、奴隶和子女的父权的认可,仅仅在寡母为保护其子女继承之财产免受侵害的法定权力时受到微弱的抵制。这种权力使一些怀有雄心壮志的女性成为帝国的摄政,她们在其子成年后仍继续掌权。皇后伊琳娜无疑是这种与父权理论不相适宜的行为的主要实践代表,她也成为其他女性熟知并效仿的典范:忏悔者狄奥凡诺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指出,811年斯陶拉克奥斯(Staurakios)的妻子——狄奥法诺(Theophano)试图效法神佑的伊琳娜实行亲政,并得到了她奄奄一息的丈夫的支持。同样,842年的狄奥多拉(Theodora),912年的佐伊(Zoe Karbounopsina)和1118年的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e)都试图夺取帝国的统治权。1341年,萨瓦的安娜(Anna of Savoy)则成功地统治了帝国。然而我们有必要对安娜·科穆宁对其祖母安娜·达拉塞尼(Anna Dalassene)的描述进行解释,11世纪末在其子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于前线同敌人作战期间,这位妇人执掌着帝国大权。这一行为是母亲对子女的关爱与奉献精神的表现,不过它也表明在必要之时女性也被认为能够统治帝国。
这种女性权力的展示被认为违反了支撑拜占庭社会的基本等级理论。但是新近对讽喻和幽默文献的关注提醒人们,表面上不变的规则受到的潜在破坏可能比我们所预计的更为频繁。在宫廷内部以及在帝国的外在风貌中,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拜占庭皇廷从竞技场与海岸护城墙之间的大宫殿(Great Palace)(17) 迁移到位于君士坦丁堡西北角的布拉舍奈宫(Blachernai),(18) 这一举动包含了许多的变化。竞技场上的马车竞赛,曾是“面包与马戏”时代的一项重要的特色娱乐活动,当帝国国民的兴趣发生转变时,这种活动则让位于枪术比武和狂欢节庆。1204年后,帝国的节庆典礼更在新都特拉布松、尼西亚、阿塔和塞萨洛尼卡得以复演。
当拜占庭人使用着拾穗于古代箴言、神话、历史集锦的格言和知识时,表现出更不自觉的一面,这体现在对古典箴言的援引中。这些知识经常在新的摘录集中、在世俗的和教会的系列箴言录中重复出现(常为老生常谈),这使得那些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教益故事以及喻世名言经世不朽,唤起人们更无私的献身精神。在听闻尼斯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I)的诸多罪行后,狄奥凡诺斯(Theophanes)援引了古老的格言“窥一斑而见全豹”,这种援引行为与安娜·科穆宁使用一个惯常的古老观点——即“巴比伦之墙”永远是最坚固的城墙——如出一辙。
尽管拜占庭的文化水平很高,但多数的历史信息是经由口头而非文字得以流传的:大量实践领域中的技术,如筑路、修建城堡和防御工事等;医药知识和兽医学、农业、钻井、制磨等技术经由口头流传,助产妇可能从有经验的妇女处习得这一技艺,再将其传授于其他人,也许就是传授于自己的女儿。很明显,在出现乐谱及记谱方式之前,音乐方面的知识是以口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如果一首赞美诗的曲调被填入一首流行歌曲的旋律中,如同一些文学手稿所言,尽管并没有文字的记录,这种歌曲的曲调和歌词仍必定会广为流传。虽然如此,许多未受过教育的人仍然是通过聆听教堂中的诗朗诵才知晓福音故事的,或者是通过能够牢记福音的长辈们的讲述知晓的。如,从圣徒传记的记载中,我们获悉埃及的圣玛莉虽未从书本上学过旧约诗篇,但她却能够背诵;她感知到这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将其牢记于心。
三、遭到禁止的展示
最后,是展示的第三个层次。这就是遭到禁止的展示,尽管有官方的极大努力(为禁止这类展示所做的努力——译者注),这种展示仍可以通过对传统信仰的纪念和从未根除的实践行为探寻其踪迹。这里我将以有关天命、星像运程或机缘的观念(tyche)为例,在拜占庭未受过教育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承认这种“天命”的力量。当然,知识分子如普洛柯比(Prokopios)、普塞留斯(Psellos)、尼西塔斯(Niketas Cheniates)或狄奥多勒(Theodore Metochites)对天命影响的方面有自己的理解。其他不具备书本知识的人则仅仅是感知到一种需求,这是抚慰人们对无法理解之力量的恐惧的需求,或是人们试图逃避死亡而产生的需求。他们重现了一些迷信的习俗,这些习俗遭到教会的斥责,却被普通人认为具有某些价值。教会教规保存了谴责这种展示行为的文件。如692年举行的特鲁兰宗教会议第61条规定,直接反对占卜者或所谓的百夫长(centurions),或那些利用熊或其它动物解释天命、运程及宗谱来欺骗头脑简单的民众者。自称可预知未来之事、哄骗人们的巫师,追寻着虚幻仙境、向人们提供护身符,占卜师则从生辰八字或星相中卜算祸福,他们都被认为是应遭天谴的异教行为的执行者,受到政府或教会的谴责。
到12世纪狄奥多鲁·巴尔萨蒙(19) (Theodore Balsamon)评述教规时,有一种现象是十分明显的,即那些参与者(参与异教展示活动——译者注)对他们所遵循的节日礼俗所知甚少,这种现象与今天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在四旬斋前日食用烙饼的行为相似,即他们并不了解这样做的原因。他写道,“直至今日”(12世纪——译者注)一些农村居民在庆祝一月份的第一天时,不是依据罗马历的节期,而是根据月亮的圆缺。同样的,佐那拉斯(20) (Zonaras)指出农民虽然仍在举行与酒业丰收相关的酒神节祭典,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他们不知道这种倾倒酒水的庆典何以起源,甚至现在他们还保留着这一习俗。
巴尔萨蒙继续说明了第62款教规中收录的其它应受到谴责的异教节庆:初旬节(Kalends)是希腊的节日,在这月的前10天人们举行庆祝活动,行一些亵渎上帝的不敬之事(tina asemna)。在一月份,这一节日与新年庆典合二为一。Rousalia节是流行于偏远农村的一个不良习俗,其节期在复活节之后;Vota节和酒神节(Brumalia)是向绵羊、其他动物以及异教神牧神献祭的古希腊节日,在向酒神斟酒致敬时,人们也向牧神斟酒致敬;在3月份的一个盛大的希腊节日中,男人与女人跳着不合礼节的舞蹈,男人们甚至穿着女性的服装,这种性别的颠倒为圣教父们所禁止。他(巴尔萨蒙)将这种佩戴假面的行为与古代作家,如阿里斯多芬(喜剧)、欧里庇底斯(悲剧)、狄厄尼索斯(讽刺诗)及巴克卡尔(Bakchal,君士坦丁一世时期的音乐理论家)等相联系。他特别指出在早期的法律中(查士丁尼新律第123条,第64节)这些节日是被废止的,但这些禁令收效甚微。
随后他描述了那些从事戏剧性表演(ta skenika)的男女,他们穿戴着修士或隐修者的服装来嘲讽教会事务。在这些节日期间,神职人员也用各种的服饰装扮自己,佩戴面具来庆祝节日:他们扮成士兵,佩剑进入教堂,或者扮成修士或四足动物在街上游走。(在现代评论中,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假面哑剧”,不过既然今日无人理解假面哑剧的含义,它应该可以被认为与万圣节前夜相同,有面具、滑稽的帽子、服装和恶作剧或捉弄人的事)。“当我问及这是如何开始的,我得到的回答都是,这是一个久远的古代习俗(ek makras synetheias)”……某些现象的不断重复是因为在每年的同一时间人们总是这样行事,而没有提及其最初的目的和功能。
不仅农村居民的这类行为需要被纠正:在圣公证人节,受训律师戴着戏剧性假面进入广场,这种不当行为也是被禁止的。米蒂利尼(21) 的克里斯多弗(Christopher of Mytilene)也提到这一节日,巴尔萨蒙则把它与法律学生联系起来。特鲁兰会议的第71条教规禁止他们采用异教习俗,禁止他们以特殊的衣着来标明学习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禁止他们参与表演和进行所谓的杂耍表演行为。对于现今(指12世纪—译者注)仍发生在大竞技场中的预测命运的行为,克里斯多弗也认为其具有危害性,并将之归为杂耍表演。
很明显,这种被禁止的“展示”与深受人们喜爱的古老习俗相关。人们不希望放弃特别有趣的娱乐活动,如为庆祝新月的第一天新月节(noumeneia),人们在作坊或房屋前燃起篝火,并从火上跨跃过去,这成为人们寻求祥兆的一种方式。巴尔萨蒙指出这种在新月之初夕点燃篝火的疯狂习俗一直延续到大主教迈克尔三世(Michael Ⅲ)时期(1170—1178)。庆祝月亮重生是犹太教和异教的习俗,这一习俗早在“没有记忆的古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巴尔萨蒙称,承蒙上帝之恩,这种习俗现在(指12世纪——译者注)转变为一种祈祷吉祥和由教会虔诚的神职人员赐予神佑圣水的基督教礼俗。不过其它的习俗仍然保留了下来:6月23日(接近夏至日),巴尔萨蒙记录了整夜吵嚷不休的歌舞活动,这与预测福祸相关。许多人,包括男人,女人,都参加了这一仪式,仪式内容包括将一个年轻女孩关在屋内,房间里另有一些人将她装扮成新娘,然后女孩被带到海边,装入樽内,放入海中,演出一场祭祀仪式——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有助于预测天命。
教规再三地将古老的不良习俗与祈福或示祸等预言祸福的行为相联系。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即有多少被废止的行为涉及所谓预知未来的能力和抵御疾病及恶魔之眼的能力。穿着异性服装、在公众场合跳舞、大声喧哗地唱歌、佩戴戏剧化的面具化装演出以娱乐,这些行为都遭到692年教规的谴责。但是即使在12世纪,巴尔萨蒙也承认教会对这类行为的控制是失败的。即便人们已经长时间地遗忘了这些行为的初衷,不过由于它们总是不断地被重复,所以它们必定延续下来。它们成为持续不断的习俗,成为每年周而复始的生活流程中的一部分,其中一些传统已经对官方规定产生了持续的颠覆性破坏作用。拜占庭人还热衷于嘲弄当权者,如:当狄奥法诺打算下嫁约翰·齐米西斯(John Tzimiskes)时,有一首讽刺民谣传播甚广,而约翰却未能成为她期待中的第三位丈夫—皇帝。(22)
上述展示行为起源于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时期,当时基督徒试图抹去异教庆典仪式的痕迹。最初,教会不得不面对老一代人有意识地持续进行异教活动的行为,他们认为这种异教庆典十分重要。但是,随后的几代人在不了解这类庆典形成的方式、原因和时间的情况下扩展了这类庆典活动,它也就变成了一种承载了较少历史信息、“从未知时代起”就不断重复的程序。这种实践行为因长期存在而变得合理,并被纳入一种潜意识的传统中。在有意识行为与无逻辑性重复这两者之间,传统可能被集体的共同记忆所加强,这些习俗被人们口口相传持续下去,即使它们可能已经没有了实质性意义。
许多这种活动被认为是专属于那些头脑简单、易被术士和其他自称能预知未来命运者引入歧途的人,然而那些曾受过教育的、正在接受律师职业训练的年轻人也包括在热衷于这类活动的群体中。君士坦丁堡成为他们活动的中心,他们在大竞技场中进行幼稚的游行和竞赛,这种活动的目的仍然是为了预言祸福。因此这种信仰也为其它社会阶层所共有;并不局限于涉及农村生活的文献中所提及的无知农民。
四、结论
讨论上述三种“展示”之后,我希望最后谈论以下有关拼写的问题。正确的拼写无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拜占庭人的标志之一。但是当拜占庭的希腊语发展出许多听起来相同的元音时,学习拼写必定变得更加困难。到10世纪,听写已经十分困难。1930年6月发轫于英格兰的反对强化推行规范拼写方法运动的海莱勒·贝洛克(Hilaire Belloc)提醒了我这一点。海莱勒·贝洛克对推行规范拼写法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在莎士比亚时代人们对以不同方式拼写姓名看得并不重要。他还论述到掌握单词间的广泛联系比正确地拼写它们更为重要。他以单词“ink”为例,称“这个单词浓缩了欧洲与伟大的拜占庭为中心的整个历史——因为ink是只有位于君士坦丁堡皇位上的统治者在签署最威严的名字时才能使用的皇室书写液。”他承认无人能记得这一点,并指出拼写Constantinopolitan比拼写ink难得多。
在他写下这番话的76年中,关于拜占庭的观点发生了许多变化,今天,几乎无人使用蘸水钢笔和墨水进行书写。我们生活在21世纪,正因如此,第21届国际拜占庭学术会议决定展示这个遗失世界的魅力。也许,理解拜占庭文明会很困难,部分原因是在现代世界它没有直接的继承者,部分原因是许多有关其文化的原始资料已经遭到破坏。但是对狄奥多修斯港(地理位置)的鉴别,严格说是对考古学家认为它应处的地理位置的鉴别,以及对古典晚期船只龙骨、船锚、货物以及船上的货币和陶器的发掘提醒我们,丰富的历史证据就深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发掘。有了这些壮观的考古发现,我们能够填补有关“万城之女皇”早期贸易形式的知识空白,也能重构它的港口。就如同在数世纪的瓦砾残垣下总是埋藏着新的物件一样,众所周知的原始文献和艺术品也在等待我们对其进行新的解释,包括拜占庭与其周边世界的新联系:与伊斯兰、西方、巴尔干和罗斯的联系。拜占庭通过它的建筑、庆典仪式以及帝国货币方面的展示——这种展示也常作为权力与权威的象征而被效仿——将自己在时空的影响远远扩展出帝国本身。而揭开这种影响的不同层次,将它们展示给世界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译者注:本文是第21届世界拜占庭大会开幕式(2006年8月21日)上的讲演。主讲者朱迪·海琳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世界著名拜占庭学者。蒙作者特许,在此节译发表。“展示”原文为“display”,英文原意为“陈列”、“展览”、“显示”,亦有“夸示”、“炫耀”,或以肢体语言表述之意。在现代语义延伸中,指在计算机屏幕上提供信息或显示图形等。“Byzantine Display”(即“拜占庭的展示”)是21届世界拜占庭大会的主题。它有双重含义,一是以今人的视角揭示拜占庭文明的特点及其价值,二是从拜占庭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包括钱币、考古遗址、遗迹、碑铭、圣像、建筑、民俗及世俗的、教会的、法律的文献及历史文献等各种有形、无形事物,理解拜占庭时期的社会风貌及价值取向,即拜占庭人对他们自己文明的“展示”。
注释:
① 译者注:“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学者”指拜占庭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
② 译者注:St. Theodore of the stoudios(759-826),8、9世纪拜占庭著名的神学家、修道院制度改革家和圣者。出生于一个支持圣像崇拜的文职官员家庭。780年进入波西尼亚地区的Sakkoudion修道院。794年成为该院院长。795年因反对君士坦丁六世的宗教政策而被流放至塞萨洛尼卡。798年返回君士坦丁堡,重建斯图迪乌修道院。809年因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尼西弗鲁斯一世对皇帝尼西弗鲁斯一世的妥协被流放到普林斯群岛,815年因反对破坏圣像再次遭流放。821年迈克尔一世将其召回君士坦丁堡。他主张建立自主的修道院组织,抵制皇权对修道院和教会的渗透。强调修道院的戒律以及修士参与社会事务的必要性,同时还高度评价了家族纽带之于社会的作用,并关注妇女的社会作用。
③ 译者注:Niketas Choniates,12—13世纪拜占庭的政府官员、历史学家、神学家。其著作《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是1118年到1206年间最重要的拜占庭历史资料。也是拜占庭散文体作品的主要代表。在这部作品中,“人”被描述为兼具好坏两种品质的矛盾体,成为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主动因素之一,尽管在这部作品中上帝仍是历史发展最终的主导因素,不过这部作品还是开创了拜占庭历史作品的新方向。
④ 译者注:马克西姆斯·普拉努迪斯(Maximos Planoudes, 1255—1305),13世纪拜占庭的学者和翻译家,原名曼纽尔(Manuel),生于尼科米底,曾任皇宫的手稿书记员,后成为奥克森得乌斯山(Auxentios)修院院长。1296年任拜占庭帝国外交大使出访威尼斯。其主要著作是对古代拉丁作家,如奥古斯丁、西塞罗等人作品的翻译本。另外还搜集了一些民间谚语,同时著有一部名为《印度人的伟大计算法》的算术指南。
⑤ 译者注:初级基础训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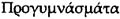 ),原意为“初级训练”,最初是指为那些要进行讲演训练的学生准备的有关修辞学的预科训练课程,包括对寓言、轶事、箴言的学习,以及对辩驳、论证等基本的演讲方法的训练。
),原意为“初级训练”,最初是指为那些要进行讲演训练的学生准备的有关修辞学的预科训练课程,包括对寓言、轶事、箴言的学习,以及对辩驳、论证等基本的演讲方法的训练。
⑥ 译者注:12世纪上半期的一部以对话集形式出现的讽刺文学作品。其作者不详,一般认为Prodromos或Kallikles为其作者,也有观点认为Michael Italikos为该作品的作者。书中主要以一个名为Timarion的人,被误认为亡魂而被带至冥府为故事主线,描写了其在冥府的所见所闻。
⑦ 译者注:10世纪拜占庭的将军。968年,皇帝尼斯弗鲁斯二世(Nikephoros Ⅱ Phokas)授予其Patrikios的称号,并任命他为黑山地区的督军,监管安条克地区。任职期间,他与太监彼得进攻安条克,并于969年末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该地区,但因其军事行为违背皇帝旨意而未获皇帝嘉奖,于是他转而支持约翰一世(John I Tzimiskes)协助其刺杀了尼斯弗鲁斯二世。瓦西里二世时期他成为安条克地区的督军(doux)。
⑧ 译者注: ,圣母玛丽亚的另一称呼,该称呼最初指古埃及女神伊西斯,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希波勒塔斯的著作中。这一称呼强调玛利亚的神性。
,圣母玛丽亚的另一称呼,该称呼最初指古埃及女神伊西斯,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希波勒塔斯的著作中。这一称呼强调玛利亚的神性。
⑨ 译者注:该教堂原是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之后,改为教堂。
⑩ 译者注:Theodores Metochites(1270-1332),拜占庭的政治家、学者和艺术的资助人。
(11) 译者注: ,一群拥有远见的圣徒,智慧而博学,常谦逊地声称自己为愚笨之人,由此得名“基督的愚人”。这类圣徒始于埃梅萨的西梅恩(Symeon of Emesa),他们反对古代城市文明的传统价值观,主张远离尘世、进行苦修。
,一群拥有远见的圣徒,智慧而博学,常谦逊地声称自己为愚笨之人,由此得名“基督的愚人”。这类圣徒始于埃梅萨的西梅恩(Symeon of Emesa),他们反对古代城市文明的传统价值观,主张远离尘世、进行苦修。
(12) 译者注:Mary of Egypt,圣徒,其生平无法考证,只有流传下来的部分传闻。据Skythopolis的西里尔记载,玛丽是耶路撒冷Anastasis教堂的歌咏者,后携带一篮蔬菜进入沙漠,并以此为食在沙漠中苦修17年。这一传说使玛丽成为沙漠圣徒的代表人物之一。
(13) 译者注: ,4世纪时塞浦路斯,Trimithous教区主教,沙漠圣徒。曾出席过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
,4世纪时塞浦路斯,Trimithous教区主教,沙漠圣徒。曾出席过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
(14) 译者注:一部6世纪神学著作集作者的笔名(亦称“伪狄奥尼索斯”)。这部著作集内容包括神秘主义神学、教会等级理论、信函等。作者称自己为圣徒保罗的门徒,其真实身份不详。作者关注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如普罗克罗斯(Proklos)等人的神秘主义学说,并将此引基督教神学中。他剔除了新柏拉图主义中自我精神的概念,用上帝来代替其中的理性,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对神学进行论述。
(15) 译者注: ,本意为“安静、寂静”,原指修道者祈祷以及沉思修道的常见方式,人们认为通过精神上的静思可达到与上帝的交汇。这种沉思的修道方式可追溯到沙漠教父时期。圣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是这种修道方式的重要传播中心。14—15世纪,这个术语也用来描述当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运动,这种用法始于1341年到1347年的内战时期。
,本意为“安静、寂静”,原指修道者祈祷以及沉思修道的常见方式,人们认为通过精神上的静思可达到与上帝的交汇。这种沉思的修道方式可追溯到沙漠教父时期。圣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是这种修道方式的重要传播中心。14—15世纪,这个术语也用来描述当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运动,这种用法始于1341年到1347年的内战时期。
(16) 译者注: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期拜占庭的教会法学家。其信函与对案件的决议是当时社会和法律历史的主要史料,反映出当时出现在主教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范围,采用的法庭辩论方法以及当时的法律知识水平。
(17) 译者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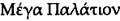 ,位于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与海岸护城墙之间的皇宫,始建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至阿列克修斯一世统治之前一直是皇帝的居所。阿列克修斯一世将皇宫移至布拉克奈宫后,大宫殿仍然是皇帝的官方居所。
,位于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与海岸护城墙之间的皇宫,始建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至阿列克修斯一世统治之前一直是皇帝的居所。阿列克修斯一世将皇宫移至布拉克奈宫后,大宫殿仍然是皇帝的官方居所。
(18) 译者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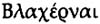 ,原指君士坦丁堡西北角的一处拥有泉水的地方。450年皇后Pulcheria在此建造了一座圣母玛利亚圣堂。利奥一世时期,增建了尊放圣骨的环型圣堂。嗣后,教堂区不断扩大。公元500年在教堂区南部的高地上建立了皇帝的行宫,行宫与教堂区毗邻,通过天桥相连。阿列克修斯一世时期,布拉舍奈宫成为皇帝的日常居所。
,原指君士坦丁堡西北角的一处拥有泉水的地方。450年皇后Pulcheria在此建造了一座圣母玛利亚圣堂。利奥一世时期,增建了尊放圣骨的环型圣堂。嗣后,教堂区不断扩大。公元500年在教堂区南部的高地上建立了皇帝的行宫,行宫与教堂区毗邻,通过天桥相连。阿列克修斯一世时期,布拉舍奈宫成为皇帝的日常居所。
(19) 译者注:教会法学家,1130—1140年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卒于1195年之后。曾任安条克主教,是皇权的忠实支持者。
(20) 译者注:12世纪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教会法学家和神学家。1118年进入圣Glykeria修道院。其著作Epitome historion包括了从创世纪至1118年的历史。
(21) 译者注:爱琴海东南部莱斯博斯岛上的主要城市,也用于指代全岛。
(22) 译者注:这是拜占庭马其顿朝宫廷斗争的一幕闹剧。狄奥法诺原是皇帝罗曼努斯二世的妻子,在罗曼努斯死后担任其子瓦西里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的摄政。当尼斯弗鲁斯·福卡斯篡位之后,狄奥法诺再次稳坐皇后宝座。但她仍然想独掌大权,遂勾结约翰·齐米西斯搞宫廷政变。她的阴谋没有得逞,约翰上台后惩罚了狄奥法诺,迎娶了狄奥法诺前夫罗曼努斯的妹妹为妻。文中所提到的这首讽刺诗就是描述这段不成功的宫廷政变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9期
【原文出处】《古代文明》(长春)2008年3期第74~82页
【作者简介】朱迪·海琳,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
| 【内容提要】 | 本文是2006年伦敦第21届世界拜占庭大会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从公开、自觉的夸示,世俗生活模式的展示和教俗势力所禁止的习俗表现等3个方面阐释了拜占庭帝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展示”(display)自己的方式,并指出,21世纪拜占庭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探寻拜占庭文明对其周边世界的影响,将其“展示”于天下。 |
一、具有自觉意识的公开展示
如果我们从拜占庭“展示”中最具自觉意识的方面开始,会发现其中一些是有道理的,而另一些则是荒谬的,不过它们都是拜占庭世界的组成部分。许多的展示是以拜占庭高度发达的教育体制为基础的,这种教育体制的内容包括七门人文学科的古典课程。这些课程在1000年中一直是帝国所有高深知识的基础。当拜占庭的知识分子面对那些深植于古典世界的知识时,这种承袭于希腊罗马实践的教育体制给予了他们强大的自信。本人以为,有一点值得强调,一种认为古典知识极具价值的深刻理念,促使同样的教育体制不断地鼓舞着大约35代的学者。这一教育(体制)囊括了从诗歌写作到肢体损伤包扎术、从哲学到兵法、古代戏剧、法律与正义的原则以及兽医学、天文学、数学和历史学在内的各种知识领域。
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体制,是因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详细地记叙了他们的学习经历和卓越的技艺。我们可以对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数量进行具体地个案研究,他们可能是在任何一段时期(300年)进入这一群体的人,我们可以得知他们是多么微小的一个阶层。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获悉,有多少古希腊原始文本得到复制,并能够追寻到一些已遗失文本曾经存在的痕迹。但是这点只能提醒我们,已经遗失的拜占庭历史证据有多大数量。例如,我们都知道一个10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教师,他的书信宴飨着现代拜占庭学者,揭示了有关其嗜好的信息,这些存留至今的信函表明了他的教学方法和成就,可我们却无法得知其姓名。而既然能有一个我们不知其名的教师,就必定存在另外十个教师,但他们的书信没有被收集到,或许他们的学生也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此外,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学者与他人通信时,① 通信的对方领会其心意,也会以同样高雅的古希腊方式回信。由于太多文本的轶失,我们不能恢复他们之间通信的历史原貌,不过这类通信的确存在。
例如:一些在斯图迪乌修道院的圣狄奥多勒(St Theodore of the Stoudios)② 在世期间一直与其通信的上层社会的女性,因在该修道院被驱散至不同流放地期间对修院的资助而受到感谢。狄奥多勒的致谢信函得以妥善收藏,但是其通信对象的那部分信件却遗失殆尽。如果修女卡西娅与那个同狄奥多勒通信的卡西娅确为同一人,那么尽管她的一些隽语和赞美诗幸运地存有副本,但是她的大量书信却毫无记录。仅从书信学方面看来,更多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想要这样称呼他们的话——进行着一种特殊形式的书面交流,许多初级教士和世俗官员接收到来自诸如迈克尔·塞勒斯这样的大人物的信件时,会以同样的阿提卡希腊语回信,他们通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这种语言。
稍晚的时候,出现了方言版的文本,这些文本是专为那些认为古典希腊语难以掌握的人们准备的。(这种现象)表明读者群需要读一种比《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History of Niketas Choniates)③ 更通俗易懂的版本。在拜占庭,人们的读写能力似乎很高——至少到13世纪为止,一直高于西欧很多。这不仅以基督教经典文本和教会文献为依据。但凡接受过些许教育的人都知道荷马的诗歌,他们或许还牢记着古典文学作品。对于提及古希腊作家——特别是诗人和戏剧作家——的文献,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使用它们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了整理。正如我们所知,有知识的地方就会有展示的形式。
对异教文学的深刻理解和对异教古代神祇、哲人、英雄和反派人物的认识,激发拜占庭人去研究在整个基督教时期伫立于拜占庭城市中的雕像。这种理解也鼓舞着8世纪君士坦丁堡的“街市哲人”步出家门,颂读并誊写那些依旧可见的铭文。即便他们误解了这些铭文,援引伪典来求证铭文的渊源,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与现已遗失的历史遗迹相关的信息。同样的理解也鼓舞着13世纪的马克西莫斯·普兰诺德斯(Maximos Planoudes)④ 创作了一篇祈祷辞,乞求上帝在末日审判时免除对柏拉图(Plato)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惩罚,因为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只是由于生活在基督启示之前的时代才所知不善的。
拜占庭展示其教育传统的明显方式是对修辞学的应用:这在讲演辞、书信、布道辞、历史书籍和司法判决中都有所体现。如是,这种方式就会对它所表达的信息有所影响,不过不是影响全部的信息。许多只完成了初级基础训练⑤ 的学生仍然通晓一些修辞学,他们能够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那些未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属于无数默默无闻的即将成为拜占庭知识分子的群体——就像那些为这个文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国家提供服务的人一样。格里摩那的留特布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第二次出使君士坦丁堡时的记录,记载了一次未达成协议、结果惨淡的外交出使,从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瞥见这些人的基本工作:拜占庭皇帝提醒大使留特布兰德,即奥托一世(Otto I)的上述使节发誓不会做使帝国愤怒的举动——拜占庭政府已经对此记录在案,并且可以向留特布兰德展示这个记录。拜占庭帝国认为拥有高度发达的记录保管体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的这种体制在中世纪无可匹敌。不过,尽管与官方记录相关的印章曾记录了许多官员和书吏的姓名与职位,但是由他们发布的文件以及他们的档案系统却没有留存下来。于我们而言,拜占庭皇帝的这个提醒是一个有益的训诫,它提醒我们不要遗忘维持帝国行政运作的受过教育的历代文职官员。
宫廷和教堂是大多数华丽矫饰的仪式发生的场景,行省长官、高级官员、主教和修道院长则以此为典范在各地效仿。通过宫廷礼仪、典礼程式、教会的主要节日以及人生各年龄段的标识性仪式(个人的生命周期由出生洗礼、婚礼或修道誓礼、葬礼等标记),矫饰成为人为设计的、用来引人注目的一种直观的方式。对于丰富多彩的仪礼形式而言,君士坦丁堡无疑拥有最恢宏的舞台,而这些仪礼形式在行省中也一再地重复上演:当皇后伊琳娜(Irene)和她年幼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途径巴尔干的博洛亚城(Berroia)时,随行人员并非士兵而是歌舞艺人,这必然要引起当地人的瞩目,而我确信它确实达到了这一效果。当塞萨洛尼卡的督军(duke of Thessalonike)进入该城时,他也竭力设计了相似的仪礼活动。这种活动也为《蒂马里翁游记》(Timarion)⑥ 的作者所模仿。得胜的将军们在他们攻占的城市中为胜利举行足够盛大的庆祝活动——969年,迈克尔·保特哲斯(Michael Bourtzes)⑦ 和彼得(Peter,一个太监,曾是某位名叫福卡斯者的奴隶,以其前任主人的名字为名)胜利地进入安条克,6年后,约翰·齐米西斯(John Tzimiskes)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当瓦西里二世前往雅典感谢圣母⑧ (Theotokos)在抗击保加尔人入侵时的神佑时,他也必定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入城式,如同他在改建后的帕特农教堂(Parthenon)⑨ 举行的庄严华丽的祈祷式一样。在帕特农的祈祷式中,瓦西里二世授予该城大量银制器皿。
这种对丰富多彩的直观仪式活动的热情,以及对仪式活动具有引人注目的影响力的认识,在一些捐赠者建造自己的画像时以个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霍拉(Chora)修道院中,由狄奥多鲁斯·迈托克特斯(Theodoros Metochites)⑩ 资助下重建的教堂中,身着宫廷服饰的狄奥多鲁斯·迈托克特斯的画像不仅具有代表性,更彰显了他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中以同样姿势出现在画像中的捐赠人(君士坦丁大帝与查士丁尼大帝)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张显了他与阿克塔马(Achtamar)的卡吉克王(Gagik)、成百上千的其他国王、捐赠者、修士和较为少见的修女之间的联系。在镶嵌画、壁画和手稿中,这种对于个人虔诚加以展示的举动确认了个人对艺术作品的责任。拜占庭必定充满了丰富的绘画作品。在帕弗斯(Paphos附近)的安克雷斯特拉(Enkleistra)修道院,修道士尼奥菲托斯(Neophytos)无疑希望激发朝觐者的敬畏之情,为此他将自己的肖像置于天使之间,这样的姿势使朝觐者联想到他得道飞升进入天堂。这种自豪的因素以及自我展示在拜占庭是十分典型的。
另一方面,指导那些投身于独身禁欲生活的修道规则期待见习修士和修女展示他们安于贫穷的义举。特鲁兰会议的第45条规定清楚地表明,根据礼节,那些引荐年轻女子进入修道生活的人不能准许这些女子穿着丝制华服、佩戴金制饰品和珠宝。相应的,她们应当穿着朴素,当她们决定献身于上帝、致力于过禁欲与清贫的修道生活时,应当换上修道服。12世纪的狄奥多鲁·巴尔萨蒙(Theodoros Balsamon)对这一规则进行了评价,他注意到那些经常违反这条规定的人将被当地主教罚以适当的苦修。不过,即使是与世隔离和克己苦修的行为也都归于一种展示。柱头修士、基督愚人(11) (fools for Christ, saloi)以及沙漠圣徒如埃及的玛丽(12) 和斯拜里顿(13) (Spyridon),他们的苦修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展示行为。他们的肖像经常悬挂在教堂和修道院的墙上,即以绘画的方式来赞扬他们的行为。极端主义苦修的盛行——赤身生存在沙漠中、常年赤脚立于高柱之上——表明了基督徒对苦修者的崇拜,并颂扬他们的成就。
拜占庭教会的祈祷仪式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展示行为,弗拉吉米尔(Vladimir)的使节们第一次见证祈祷仪式时的记载反映了这一点。基督信仰的集体性展示行为不仅体现在教堂中,也体现在Hodigitria节(在首都每周举行一次)或Naupaktitissa地区的圣母节(Theotokos,在希腊中部地区每月举行一次)期举行的圣像游行活动中;圣母赞诗(Akathistos Hymns)的吟唱、或者军队出征前的祈福,都强化了拜占庭的一种身份意识,也强化了拜占庭人卓尔不群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属于一个比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记载更为悠远古老的世界。弗提乌斯(Photios)曾阅读过一部“5卷15本的”原始文献,这部书试图将所有的古代著作,包括波斯人、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色雷斯人和罗马人的著作与基督教信仰相联系,指出所有摘录的文献都“宣告了超自然的唯一存在的三位一体”,指出它们证实了“基督徒的神圣信仰”。然而即便是弗提乌斯也没有查证出这部7世纪作品的作者之姓名,我们却更已经遗失了他所有的作品。
拜占庭对正确释义基督教神学方面的自信,也部分地来自于对古代哲学概念和辨证方法的使用,这种概念和方法已经融入神学并增强了信仰(的影响力)。特别是由笔名为狄奥尼索斯的人(14) (Ps-Dionysios)构想、由忏悔者马克西莫斯(Maximos)发展的有关上帝神格的神秘主义认知,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进展,在基督教的外衣下巩固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分支的发展。在8世纪,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方法与圣像共同使用于宗教崇拜中,他曾强调一定的文本能够使人的心灵升华至更高尚的理解境界,他也曾强调对宗教画的凝视与沉思如何具有同样的功效。至14世纪,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成为支撑着静修派(15) (Hesychasm)的基础,以达到将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的理解升华到与上帝相同一的神学境界(theosis)。通过苦修沉思和肉体上的严苛历练,修士可能经历如变容般的启示,正如基督在塔泊尔山(Tabor)上为人所见那样。
所有这些自觉的展示行为,都在诸如加冕礼、皇室婚礼等重大庆典仪式中融为一体,1180年为阿列克修斯二世·科穆宁与法兰西的艾格尼斯一安娜所举办的婚礼庆典所示——整个庆典充斥着为向安娜致敬而创作和诵读的祝婚辞,祝婚辞中华丽的辞藻俯拾皆是,更有为宾客准备的场面宏大的娱乐节目以及大肆铺张的狩猎活动和盛宴,为她举行的接风仪式及订婚礼,场面宏大。在这些场面中,拜占庭无疑展示了它自己,它也十分相信这种展示能够使它更加引人注目。
二、世俗生活的展示
拜占庭展示的第二层更为世俗化:一个明晰的社会分层是以一种二分理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存在于自由人与奴隶、罗马人与异邦人(原文用“Barbara”,罗马人通常用这一名词指代非罗马人,过去统译为蛮族——译者注)之间。这种理论包含以下的理念,即某些人有责任去统治,而某些人则有义务服从统治。在每个拜占庭家族中,家长权是十分鲜明的。太监作为介于男性女性之间的一种必要的第三性,则是重要的社会角色,其中许多人位居要职,主管宫廷礼仪,掌握皇帝的私人生活空间,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和声望。
在拜占庭,没有人质疑男性的统治地位,他们统治着自己的家人,决定子女婚配的适当人选。尽管教会可能极力主张基督徒对奴隶要施以仁慈,但是无人质疑下等人的生存条件,“下等人”可以被严酷地殴打和惩罚。如果他们被抓获偷盗,会被砍掉一只手以示惩罚。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中,迪米特里欧斯·库马提安努斯(16) (Demetrios Chomatianos)阻止一个贵妇人砍掉一个惯偷奴隶仅存的手。受到同样处置的还有太监,他们也有可能被迫“扮演令人作呕的嗜男色者”,这种行为遭到圣愚者安德莱阿斯(Andreas)的严厉斥责。许多书面遗嘱中包含对奴隶致谢的词句,这削弱了关于社会地位、出身特权、主人与奴隶的自然秩序的观念:在主人死后,这些奴隶不仅获释得到自由,而且还被赠予土地、家具以及衣服等个人物品。但是这些个体性的仁慈行为对削弱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之间基本区分的观念功效甚微。
对界线分明的社会分层理论的认同及对家长依自己意愿处置其财产、奴隶和子女的父权的认可,仅仅在寡母为保护其子女继承之财产免受侵害的法定权力时受到微弱的抵制。这种权力使一些怀有雄心壮志的女性成为帝国的摄政,她们在其子成年后仍继续掌权。皇后伊琳娜无疑是这种与父权理论不相适宜的行为的主要实践代表,她也成为其他女性熟知并效仿的典范:忏悔者狄奥凡诺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指出,811年斯陶拉克奥斯(Staurakios)的妻子——狄奥法诺(Theophano)试图效法神佑的伊琳娜实行亲政,并得到了她奄奄一息的丈夫的支持。同样,842年的狄奥多拉(Theodora),912年的佐伊(Zoe Karbounopsina)和1118年的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e)都试图夺取帝国的统治权。1341年,萨瓦的安娜(Anna of Savoy)则成功地统治了帝国。然而我们有必要对安娜·科穆宁对其祖母安娜·达拉塞尼(Anna Dalassene)的描述进行解释,11世纪末在其子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于前线同敌人作战期间,这位妇人执掌着帝国大权。这一行为是母亲对子女的关爱与奉献精神的表现,不过它也表明在必要之时女性也被认为能够统治帝国。
这种女性权力的展示被认为违反了支撑拜占庭社会的基本等级理论。但是新近对讽喻和幽默文献的关注提醒人们,表面上不变的规则受到的潜在破坏可能比我们所预计的更为频繁。在宫廷内部以及在帝国的外在风貌中,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拜占庭皇廷从竞技场与海岸护城墙之间的大宫殿(Great Palace)(17) 迁移到位于君士坦丁堡西北角的布拉舍奈宫(Blachernai),(18) 这一举动包含了许多的变化。竞技场上的马车竞赛,曾是“面包与马戏”时代的一项重要的特色娱乐活动,当帝国国民的兴趣发生转变时,这种活动则让位于枪术比武和狂欢节庆。1204年后,帝国的节庆典礼更在新都特拉布松、尼西亚、阿塔和塞萨洛尼卡得以复演。
当拜占庭人使用着拾穗于古代箴言、神话、历史集锦的格言和知识时,表现出更不自觉的一面,这体现在对古典箴言的援引中。这些知识经常在新的摘录集中、在世俗的和教会的系列箴言录中重复出现(常为老生常谈),这使得那些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教益故事以及喻世名言经世不朽,唤起人们更无私的献身精神。在听闻尼斯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I)的诸多罪行后,狄奥凡诺斯(Theophanes)援引了古老的格言“窥一斑而见全豹”,这种援引行为与安娜·科穆宁使用一个惯常的古老观点——即“巴比伦之墙”永远是最坚固的城墙——如出一辙。
尽管拜占庭的文化水平很高,但多数的历史信息是经由口头而非文字得以流传的:大量实践领域中的技术,如筑路、修建城堡和防御工事等;医药知识和兽医学、农业、钻井、制磨等技术经由口头流传,助产妇可能从有经验的妇女处习得这一技艺,再将其传授于其他人,也许就是传授于自己的女儿。很明显,在出现乐谱及记谱方式之前,音乐方面的知识是以口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如果一首赞美诗的曲调被填入一首流行歌曲的旋律中,如同一些文学手稿所言,尽管并没有文字的记录,这种歌曲的曲调和歌词仍必定会广为流传。虽然如此,许多未受过教育的人仍然是通过聆听教堂中的诗朗诵才知晓福音故事的,或者是通过能够牢记福音的长辈们的讲述知晓的。如,从圣徒传记的记载中,我们获悉埃及的圣玛莉虽未从书本上学过旧约诗篇,但她却能够背诵;她感知到这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将其牢记于心。
三、遭到禁止的展示
最后,是展示的第三个层次。这就是遭到禁止的展示,尽管有官方的极大努力(为禁止这类展示所做的努力——译者注),这种展示仍可以通过对传统信仰的纪念和从未根除的实践行为探寻其踪迹。这里我将以有关天命、星像运程或机缘的观念(tyche)为例,在拜占庭未受过教育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承认这种“天命”的力量。当然,知识分子如普洛柯比(Prokopios)、普塞留斯(Psellos)、尼西塔斯(Niketas Cheniates)或狄奥多勒(Theodore Metochites)对天命影响的方面有自己的理解。其他不具备书本知识的人则仅仅是感知到一种需求,这是抚慰人们对无法理解之力量的恐惧的需求,或是人们试图逃避死亡而产生的需求。他们重现了一些迷信的习俗,这些习俗遭到教会的斥责,却被普通人认为具有某些价值。教会教规保存了谴责这种展示行为的文件。如692年举行的特鲁兰宗教会议第61条规定,直接反对占卜者或所谓的百夫长(centurions),或那些利用熊或其它动物解释天命、运程及宗谱来欺骗头脑简单的民众者。自称可预知未来之事、哄骗人们的巫师,追寻着虚幻仙境、向人们提供护身符,占卜师则从生辰八字或星相中卜算祸福,他们都被认为是应遭天谴的异教行为的执行者,受到政府或教会的谴责。
到12世纪狄奥多鲁·巴尔萨蒙(19) (Theodore Balsamon)评述教规时,有一种现象是十分明显的,即那些参与者(参与异教展示活动——译者注)对他们所遵循的节日礼俗所知甚少,这种现象与今天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在四旬斋前日食用烙饼的行为相似,即他们并不了解这样做的原因。他写道,“直至今日”(12世纪——译者注)一些农村居民在庆祝一月份的第一天时,不是依据罗马历的节期,而是根据月亮的圆缺。同样的,佐那拉斯(20) (Zonaras)指出农民虽然仍在举行与酒业丰收相关的酒神节祭典,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他们不知道这种倾倒酒水的庆典何以起源,甚至现在他们还保留着这一习俗。
巴尔萨蒙继续说明了第62款教规中收录的其它应受到谴责的异教节庆:初旬节(Kalends)是希腊的节日,在这月的前10天人们举行庆祝活动,行一些亵渎上帝的不敬之事(tina asemna)。在一月份,这一节日与新年庆典合二为一。Rousalia节是流行于偏远农村的一个不良习俗,其节期在复活节之后;Vota节和酒神节(Brumalia)是向绵羊、其他动物以及异教神牧神献祭的古希腊节日,在向酒神斟酒致敬时,人们也向牧神斟酒致敬;在3月份的一个盛大的希腊节日中,男人与女人跳着不合礼节的舞蹈,男人们甚至穿着女性的服装,这种性别的颠倒为圣教父们所禁止。他(巴尔萨蒙)将这种佩戴假面的行为与古代作家,如阿里斯多芬(喜剧)、欧里庇底斯(悲剧)、狄厄尼索斯(讽刺诗)及巴克卡尔(Bakchal,君士坦丁一世时期的音乐理论家)等相联系。他特别指出在早期的法律中(查士丁尼新律第123条,第64节)这些节日是被废止的,但这些禁令收效甚微。
随后他描述了那些从事戏剧性表演(ta skenika)的男女,他们穿戴着修士或隐修者的服装来嘲讽教会事务。在这些节日期间,神职人员也用各种的服饰装扮自己,佩戴面具来庆祝节日:他们扮成士兵,佩剑进入教堂,或者扮成修士或四足动物在街上游走。(在现代评论中,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假面哑剧”,不过既然今日无人理解假面哑剧的含义,它应该可以被认为与万圣节前夜相同,有面具、滑稽的帽子、服装和恶作剧或捉弄人的事)。“当我问及这是如何开始的,我得到的回答都是,这是一个久远的古代习俗(ek makras synetheias)”……某些现象的不断重复是因为在每年的同一时间人们总是这样行事,而没有提及其最初的目的和功能。
不仅农村居民的这类行为需要被纠正:在圣公证人节,受训律师戴着戏剧性假面进入广场,这种不当行为也是被禁止的。米蒂利尼(21) 的克里斯多弗(Christopher of Mytilene)也提到这一节日,巴尔萨蒙则把它与法律学生联系起来。特鲁兰会议的第71条教规禁止他们采用异教习俗,禁止他们以特殊的衣着来标明学习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禁止他们参与表演和进行所谓的杂耍表演行为。对于现今(指12世纪—译者注)仍发生在大竞技场中的预测命运的行为,克里斯多弗也认为其具有危害性,并将之归为杂耍表演。
很明显,这种被禁止的“展示”与深受人们喜爱的古老习俗相关。人们不希望放弃特别有趣的娱乐活动,如为庆祝新月的第一天新月节(noumeneia),人们在作坊或房屋前燃起篝火,并从火上跨跃过去,这成为人们寻求祥兆的一种方式。巴尔萨蒙指出这种在新月之初夕点燃篝火的疯狂习俗一直延续到大主教迈克尔三世(Michael Ⅲ)时期(1170—1178)。庆祝月亮重生是犹太教和异教的习俗,这一习俗早在“没有记忆的古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巴尔萨蒙称,承蒙上帝之恩,这种习俗现在(指12世纪——译者注)转变为一种祈祷吉祥和由教会虔诚的神职人员赐予神佑圣水的基督教礼俗。不过其它的习俗仍然保留了下来:6月23日(接近夏至日),巴尔萨蒙记录了整夜吵嚷不休的歌舞活动,这与预测福祸相关。许多人,包括男人,女人,都参加了这一仪式,仪式内容包括将一个年轻女孩关在屋内,房间里另有一些人将她装扮成新娘,然后女孩被带到海边,装入樽内,放入海中,演出一场祭祀仪式——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有助于预测天命。
教规再三地将古老的不良习俗与祈福或示祸等预言祸福的行为相联系。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即有多少被废止的行为涉及所谓预知未来的能力和抵御疾病及恶魔之眼的能力。穿着异性服装、在公众场合跳舞、大声喧哗地唱歌、佩戴戏剧化的面具化装演出以娱乐,这些行为都遭到692年教规的谴责。但是即使在12世纪,巴尔萨蒙也承认教会对这类行为的控制是失败的。即便人们已经长时间地遗忘了这些行为的初衷,不过由于它们总是不断地被重复,所以它们必定延续下来。它们成为持续不断的习俗,成为每年周而复始的生活流程中的一部分,其中一些传统已经对官方规定产生了持续的颠覆性破坏作用。拜占庭人还热衷于嘲弄当权者,如:当狄奥法诺打算下嫁约翰·齐米西斯(John Tzimiskes)时,有一首讽刺民谣传播甚广,而约翰却未能成为她期待中的第三位丈夫—皇帝。(22)
上述展示行为起源于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时期,当时基督徒试图抹去异教庆典仪式的痕迹。最初,教会不得不面对老一代人有意识地持续进行异教活动的行为,他们认为这种异教庆典十分重要。但是,随后的几代人在不了解这类庆典形成的方式、原因和时间的情况下扩展了这类庆典活动,它也就变成了一种承载了较少历史信息、“从未知时代起”就不断重复的程序。这种实践行为因长期存在而变得合理,并被纳入一种潜意识的传统中。在有意识行为与无逻辑性重复这两者之间,传统可能被集体的共同记忆所加强,这些习俗被人们口口相传持续下去,即使它们可能已经没有了实质性意义。
许多这种活动被认为是专属于那些头脑简单、易被术士和其他自称能预知未来命运者引入歧途的人,然而那些曾受过教育的、正在接受律师职业训练的年轻人也包括在热衷于这类活动的群体中。君士坦丁堡成为他们活动的中心,他们在大竞技场中进行幼稚的游行和竞赛,这种活动的目的仍然是为了预言祸福。因此这种信仰也为其它社会阶层所共有;并不局限于涉及农村生活的文献中所提及的无知农民。
四、结论
讨论上述三种“展示”之后,我希望最后谈论以下有关拼写的问题。正确的拼写无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拜占庭人的标志之一。但是当拜占庭的希腊语发展出许多听起来相同的元音时,学习拼写必定变得更加困难。到10世纪,听写已经十分困难。1930年6月发轫于英格兰的反对强化推行规范拼写方法运动的海莱勒·贝洛克(Hilaire Belloc)提醒了我这一点。海莱勒·贝洛克对推行规范拼写法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在莎士比亚时代人们对以不同方式拼写姓名看得并不重要。他还论述到掌握单词间的广泛联系比正确地拼写它们更为重要。他以单词“ink”为例,称“这个单词浓缩了欧洲与伟大的拜占庭为中心的整个历史——因为ink是只有位于君士坦丁堡皇位上的统治者在签署最威严的名字时才能使用的皇室书写液。”他承认无人能记得这一点,并指出拼写Constantinopolitan比拼写ink难得多。
在他写下这番话的76年中,关于拜占庭的观点发生了许多变化,今天,几乎无人使用蘸水钢笔和墨水进行书写。我们生活在21世纪,正因如此,第21届国际拜占庭学术会议决定展示这个遗失世界的魅力。也许,理解拜占庭文明会很困难,部分原因是在现代世界它没有直接的继承者,部分原因是许多有关其文化的原始资料已经遭到破坏。但是对狄奥多修斯港(地理位置)的鉴别,严格说是对考古学家认为它应处的地理位置的鉴别,以及对古典晚期船只龙骨、船锚、货物以及船上的货币和陶器的发掘提醒我们,丰富的历史证据就深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发掘。有了这些壮观的考古发现,我们能够填补有关“万城之女皇”早期贸易形式的知识空白,也能重构它的港口。就如同在数世纪的瓦砾残垣下总是埋藏着新的物件一样,众所周知的原始文献和艺术品也在等待我们对其进行新的解释,包括拜占庭与其周边世界的新联系:与伊斯兰、西方、巴尔干和罗斯的联系。拜占庭通过它的建筑、庆典仪式以及帝国货币方面的展示——这种展示也常作为权力与权威的象征而被效仿——将自己在时空的影响远远扩展出帝国本身。而揭开这种影响的不同层次,将它们展示给世界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译者注:本文是第21届世界拜占庭大会开幕式(2006年8月21日)上的讲演。主讲者朱迪·海琳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世界著名拜占庭学者。蒙作者特许,在此节译发表。“展示”原文为“display”,英文原意为“陈列”、“展览”、“显示”,亦有“夸示”、“炫耀”,或以肢体语言表述之意。在现代语义延伸中,指在计算机屏幕上提供信息或显示图形等。“Byzantine Display”(即“拜占庭的展示”)是21届世界拜占庭大会的主题。它有双重含义,一是以今人的视角揭示拜占庭文明的特点及其价值,二是从拜占庭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包括钱币、考古遗址、遗迹、碑铭、圣像、建筑、民俗及世俗的、教会的、法律的文献及历史文献等各种有形、无形事物,理解拜占庭时期的社会风貌及价值取向,即拜占庭人对他们自己文明的“展示”。
注释:
① 译者注:“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学者”指拜占庭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
② 译者注:St. Theodore of the stoudios(759-826),8、9世纪拜占庭著名的神学家、修道院制度改革家和圣者。出生于一个支持圣像崇拜的文职官员家庭。780年进入波西尼亚地区的Sakkoudion修道院。794年成为该院院长。795年因反对君士坦丁六世的宗教政策而被流放至塞萨洛尼卡。798年返回君士坦丁堡,重建斯图迪乌修道院。809年因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尼西弗鲁斯一世对皇帝尼西弗鲁斯一世的妥协被流放到普林斯群岛,815年因反对破坏圣像再次遭流放。821年迈克尔一世将其召回君士坦丁堡。他主张建立自主的修道院组织,抵制皇权对修道院和教会的渗透。强调修道院的戒律以及修士参与社会事务的必要性,同时还高度评价了家族纽带之于社会的作用,并关注妇女的社会作用。
③ 译者注:Niketas Choniates,12—13世纪拜占庭的政府官员、历史学家、神学家。其著作《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是1118年到1206年间最重要的拜占庭历史资料。也是拜占庭散文体作品的主要代表。在这部作品中,“人”被描述为兼具好坏两种品质的矛盾体,成为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主动因素之一,尽管在这部作品中上帝仍是历史发展最终的主导因素,不过这部作品还是开创了拜占庭历史作品的新方向。
④ 译者注:马克西姆斯·普拉努迪斯(Maximos Planoudes, 1255—1305),13世纪拜占庭的学者和翻译家,原名曼纽尔(Manuel),生于尼科米底,曾任皇宫的手稿书记员,后成为奥克森得乌斯山(Auxentios)修院院长。1296年任拜占庭帝国外交大使出访威尼斯。其主要著作是对古代拉丁作家,如奥古斯丁、西塞罗等人作品的翻译本。另外还搜集了一些民间谚语,同时著有一部名为《印度人的伟大计算法》的算术指南。
⑤ 译者注:初级基础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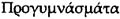 ),原意为“初级训练”,最初是指为那些要进行讲演训练的学生准备的有关修辞学的预科训练课程,包括对寓言、轶事、箴言的学习,以及对辩驳、论证等基本的演讲方法的训练。
),原意为“初级训练”,最初是指为那些要进行讲演训练的学生准备的有关修辞学的预科训练课程,包括对寓言、轶事、箴言的学习,以及对辩驳、论证等基本的演讲方法的训练。⑥ 译者注:12世纪上半期的一部以对话集形式出现的讽刺文学作品。其作者不详,一般认为Prodromos或Kallikles为其作者,也有观点认为Michael Italikos为该作品的作者。书中主要以一个名为Timarion的人,被误认为亡魂而被带至冥府为故事主线,描写了其在冥府的所见所闻。
⑦ 译者注:10世纪拜占庭的将军。968年,皇帝尼斯弗鲁斯二世(Nikephoros Ⅱ Phokas)授予其Patrikios的称号,并任命他为黑山地区的督军,监管安条克地区。任职期间,他与太监彼得进攻安条克,并于969年末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该地区,但因其军事行为违背皇帝旨意而未获皇帝嘉奖,于是他转而支持约翰一世(John I Tzimiskes)协助其刺杀了尼斯弗鲁斯二世。瓦西里二世时期他成为安条克地区的督军(doux)。
⑧ 译者注:
 ,圣母玛丽亚的另一称呼,该称呼最初指古埃及女神伊西斯,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希波勒塔斯的著作中。这一称呼强调玛利亚的神性。
,圣母玛丽亚的另一称呼,该称呼最初指古埃及女神伊西斯,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希波勒塔斯的著作中。这一称呼强调玛利亚的神性。⑨ 译者注:该教堂原是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之后,改为教堂。
⑩ 译者注:Theodores Metochites(1270-1332),拜占庭的政治家、学者和艺术的资助人。
(11) 译者注:
 ,一群拥有远见的圣徒,智慧而博学,常谦逊地声称自己为愚笨之人,由此得名“基督的愚人”。这类圣徒始于埃梅萨的西梅恩(Symeon of Emesa),他们反对古代城市文明的传统价值观,主张远离尘世、进行苦修。
,一群拥有远见的圣徒,智慧而博学,常谦逊地声称自己为愚笨之人,由此得名“基督的愚人”。这类圣徒始于埃梅萨的西梅恩(Symeon of Emesa),他们反对古代城市文明的传统价值观,主张远离尘世、进行苦修。(12) 译者注:Mary of Egypt,圣徒,其生平无法考证,只有流传下来的部分传闻。据Skythopolis的西里尔记载,玛丽是耶路撒冷Anastasis教堂的歌咏者,后携带一篮蔬菜进入沙漠,并以此为食在沙漠中苦修17年。这一传说使玛丽成为沙漠圣徒的代表人物之一。
(13) 译者注:
 ,4世纪时塞浦路斯,Trimithous教区主教,沙漠圣徒。曾出席过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
,4世纪时塞浦路斯,Trimithous教区主教,沙漠圣徒。曾出席过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14) 译者注:一部6世纪神学著作集作者的笔名(亦称“伪狄奥尼索斯”)。这部著作集内容包括神秘主义神学、教会等级理论、信函等。作者称自己为圣徒保罗的门徒,其真实身份不详。作者关注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如普罗克罗斯(Proklos)等人的神秘主义学说,并将此引基督教神学中。他剔除了新柏拉图主义中自我精神的概念,用上帝来代替其中的理性,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对神学进行论述。
(15) 译者注:
 ,本意为“安静、寂静”,原指修道者祈祷以及沉思修道的常见方式,人们认为通过精神上的静思可达到与上帝的交汇。这种沉思的修道方式可追溯到沙漠教父时期。圣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是这种修道方式的重要传播中心。14—15世纪,这个术语也用来描述当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运动,这种用法始于1341年到1347年的内战时期。
,本意为“安静、寂静”,原指修道者祈祷以及沉思修道的常见方式,人们认为通过精神上的静思可达到与上帝的交汇。这种沉思的修道方式可追溯到沙漠教父时期。圣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是这种修道方式的重要传播中心。14—15世纪,这个术语也用来描述当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运动,这种用法始于1341年到1347年的内战时期。(16) 译者注: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期拜占庭的教会法学家。其信函与对案件的决议是当时社会和法律历史的主要史料,反映出当时出现在主教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范围,采用的法庭辩论方法以及当时的法律知识水平。
(17) 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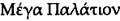 ,位于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与海岸护城墙之间的皇宫,始建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至阿列克修斯一世统治之前一直是皇帝的居所。阿列克修斯一世将皇宫移至布拉克奈宫后,大宫殿仍然是皇帝的官方居所。
,位于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与海岸护城墙之间的皇宫,始建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至阿列克修斯一世统治之前一直是皇帝的居所。阿列克修斯一世将皇宫移至布拉克奈宫后,大宫殿仍然是皇帝的官方居所。(18) 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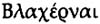 ,原指君士坦丁堡西北角的一处拥有泉水的地方。450年皇后Pulcheria在此建造了一座圣母玛利亚圣堂。利奥一世时期,增建了尊放圣骨的环型圣堂。嗣后,教堂区不断扩大。公元500年在教堂区南部的高地上建立了皇帝的行宫,行宫与教堂区毗邻,通过天桥相连。阿列克修斯一世时期,布拉舍奈宫成为皇帝的日常居所。
,原指君士坦丁堡西北角的一处拥有泉水的地方。450年皇后Pulcheria在此建造了一座圣母玛利亚圣堂。利奥一世时期,增建了尊放圣骨的环型圣堂。嗣后,教堂区不断扩大。公元500年在教堂区南部的高地上建立了皇帝的行宫,行宫与教堂区毗邻,通过天桥相连。阿列克修斯一世时期,布拉舍奈宫成为皇帝的日常居所。(19) 译者注:教会法学家,1130—1140年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卒于1195年之后。曾任安条克主教,是皇权的忠实支持者。
(20) 译者注:12世纪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教会法学家和神学家。1118年进入圣Glykeria修道院。其著作Epitome historion包括了从创世纪至1118年的历史。
(21) 译者注:爱琴海东南部莱斯博斯岛上的主要城市,也用于指代全岛。
(22) 译者注:这是拜占庭马其顿朝宫廷斗争的一幕闹剧。狄奥法诺原是皇帝罗曼努斯二世的妻子,在罗曼努斯死后担任其子瓦西里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的摄政。当尼斯弗鲁斯·福卡斯篡位之后,狄奥法诺再次稳坐皇后宝座。但她仍然想独掌大权,遂勾结约翰·齐米西斯搞宫廷政变。她的阴谋没有得逞,约翰上台后惩罚了狄奥法诺,迎娶了狄奥法诺前夫罗曼努斯的妹妹为妻。文中所提到的这首讽刺诗就是描述这段不成功的宫廷政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