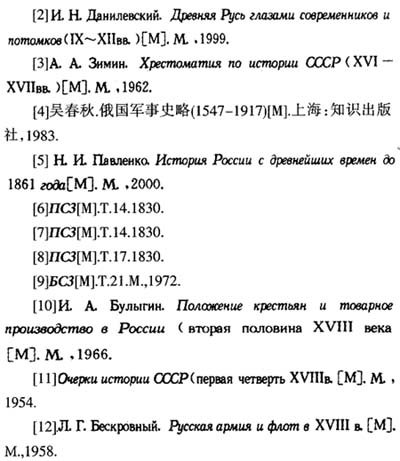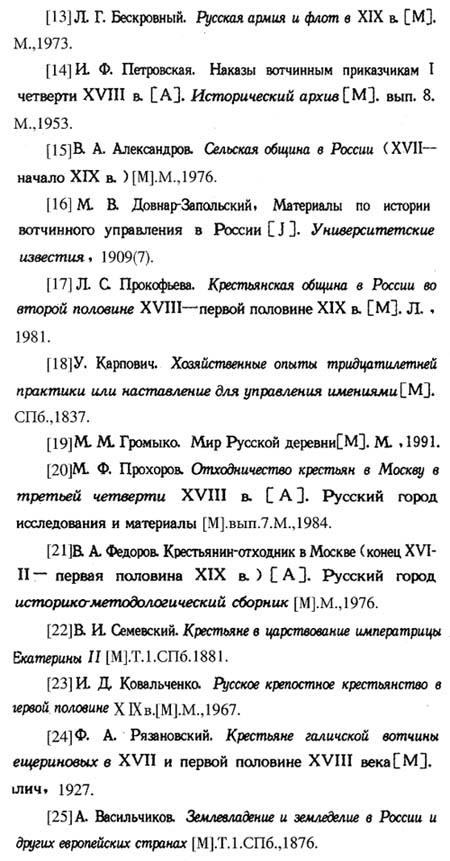| 明清史 |
论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的兵役义务
罗爱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11期第69~75,81页
【作者简介】罗爱林,历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广西 桂林 541001
【关 键 词】俄国/农村公社/农民/兵役义务/农奴制
[中图分类号]K5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11-0069-07
俄国的兵役义务肇始于18世纪初,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等级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从彼得一世改革起,到1874年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止,服兵役只是纳税等级的义务。随着贵族、教士、商人被豁免兵役,兵役事实上成为农民的专属义务。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保障兵役义务的实施。为国家选派新兵是村社的一项重要职责。研究这一时期俄国村社在农民兵役义务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俄国兵役制度、村社职能以及农奴制度特点的认识。
一 等级义务兵役制的确立
兵役作为一种国家义务,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确定下来。在此之前,俄国“没有一名真正的士兵”,“没有一支受过作战训练的军队”,[1](p25,26)当兵打仗是贵族等级的特权。
基辅罗斯时期,国家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王公亲兵队。王公亲兵队由志愿人员组成,人数一般在200~400人。[2](p106)亲兵与王公是一种契约关系,亲兵可自由加入或退出亲兵队。王公则将部分战利品和贡物分发给亲兵作报酬。从兵役制度的角度看,这是雇佣兵制度(募兵制)的萌芽。
莫斯科公国延续了这种兵役制度,所不同的是亲兵演变为服役贵族,实物报酬被封地所取代。随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封地制的发展,已获得大量封地的贵族开始逃避服役。1556年,伊凡四世颁布《军役法》,规定无论是领地波雅尔还是封地贵族,“每100切特维基良地须提供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3](p124)。为了护卫京城,伊凡四世还开始建立一支使用火器的射击军。射击军士兵多从手工业者、商人中招募而来,服役期间由国家付给军饷、军服和食物。他们可以带家属,战时执行军事任务,平时则经营自己的工商业。[4](p11)
贵族军队存在着诸多弊端:平时经营地产,怠于军事训练;战时纪律松弛,行动懒散,缺乏战斗力。因此,从17世纪起,贵族军队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新制骑兵团和步兵团成为军队的主要类型。这种新制军团起初采用募兵制,由国家提供薪水,每年秋季集训1个月,之后分散回家。但从17世纪40年代起,政府开始不定期地在农民中强制性征召“差丁”(даточный)作为军队的补员。所谓的“差丁”,指的是被政府强行征人军队的农奴。他们服役不是为了获得报酬,只是被迫履行无偿义务。俄国兵役制度开始由募兵制逐渐向义务兵役制(征兵制)过渡。
彼得一世建立起近代化的正规陆海军,并最终将兵役制度变为纳税居民义务兵役制。1699年11月17日,在对瑞典战争前夕,彼得一世下令强制征召3.2万名“差丁”入伍。随着对瑞典战争的进行,旧兵役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兵员严重匮乏,制约着战争的深入和持久。有鉴于此,1705年2月彼得一世颁布敕令,将不定期的补员征兵改为常规征兵,所征新兵称做“pekpym”。①从此,服兵役成为俄国纳税等级义不容辞的国家义务。俄国正式过渡到义务兵役制。
义务兵役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纳税等级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从1705年彼得一世颁布敕令起,到1874年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止,服兵役只是纳税等级的义务。
随着贵族、教士、商人被豁免兵役,兵役义务后来主要落在农民身上,成为农民阶级的专属义务。“1762年以前,贵族是赋税等级,就是说与其他等级一样,要承担义务。”[5](p307)但是,贵族等级逐渐享有特权,并最终从兵役义务中脱身出来:1736年贵族服役的年限缩短到25年,1740年贵族被允许在服役和公职之间作出选择,1762年颁布的《贵族自由诏书》正式免除贵族的兵役义务。18世纪30年代,教士和商人被赋予可以花钱雇人去当兵的权利;紧接着,兵工厂的匠人亦获得此项特权;到19世纪初,商人和僧侣不再承担任何军事义务。至此,等级义务兵役制事实上变成农民义务兵役制。
等级义务兵役制实施之初,只是在俄罗斯居民当中招收新兵,从18世纪下半期起开始推广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
在新兵役制推行初期,国家只规定征召新兵的年龄条件和家庭条件,年龄被限制在15~20岁,仅征募单身汉。[6](p291~292)后来,对新兵的家庭状况不作考虑,仅规定新兵的年龄和身高,如1757年的征兵通令要求新兵的年龄从20岁到35岁,身高不低于2俄尺4俄寸即1.60米;[7](p840~841)1766年,新兵年龄下限降低到17岁,其他所有条件照旧,并在以后得到坚持。[8](p1000)
1724年第1次人口普查结束前,以户为单位征兵,大约每20户征1名新兵。[9](p617)这次人口普查结束后转为根据男性人口数进行摊派。依征兵总数不同,每次摊派的比例不一。最初每500个男性人口征收1名新兵,18世纪80年代后则依次增加到每250、200、100个征1名新兵。[10](p185)到1831年,普通征兵时每千人征5~7名新兵,加强征兵的时候增加到7~10名,而特别征兵时则超过10名;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甚至达到每千人征50~70名。[9](p617)
服役年限被多次缩减。最初,兵役义务是终身的。1793年,服役期限改为25年。1834年开始变相缩短服役年限:只要服役满20年,剩下的5年就可以离职休假。亚历山大二世接着又将服役年限压缩到15年,并在1855~1872年间分三次改变服役方式:从服役12年后休假3年、服役10年后休假5年直至变为服役7年后休假8年。有意思的是,这种缩短服役期限的政策遭到了地主的强烈抵制。因为缩短服役期限势必需要有更多的农民作后备替补,地主当然不愿意损失自己的农奴,失去劳动人手;此外,地主也害怕退伍回乡的士兵在家乡为非作歹,增加管理难度。
据统计,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头25年间,除了非定期的征召民兵外,总共进行了90次征兵。随着不断对外扩张,征召进军队的新兵人数日趋增多。18世纪头25年征兵53次,征募的新兵超过28.4万人,占第1次人口普查材料中男性人口总数的3.6%多;[11](p347)1726~1760年征募了79.5万新兵,1767~1799年的新兵数是125.2万,都各占第3次人口普查(1762年)和第5次人口普查(1795年)材料中男性人口总数的7%;[12](p23~37、294~297)19世纪头25年,征募了200万新兵,占1833年第8次人口普查中男性人口总数的8%。[13](p74)兵役成为农民最繁重的国家义务。
二 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
在封建晚期,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发布征兵命令,提出征兵额度,规定征兵条件以及服役年限等。服兵役属于所有纳税等级的应尽义务。但就农民来说,却非其个人义务,而是领地义务。换言之,国家将兵役名额分解到各领地,然后由领地来履行兵役义务。国家只关注于领地按时、足额提供新兵,而不管这些新兵是以什么方式挑选出来的。
国家将挑选新兵的权力下放给领地,出于三方面的考虑:在法律层面上,承担兵役义务的农民属于领主的私有财产,他们去服兵役客观上损害了领主的经济利益,这就需要得到后者的理解和支持;从行政方面说,封建晚期俄国农村没有国家行政机构,乡、村一级村社属于农民的自治组织,②国家行政机构与农民自治组织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领地管理机构是国家意志到达农村的唯一渠道;在具体操作上,国家将挑选新兵的权力下放给领地,既使自己置身于繁琐的征兵事务之外、不至处于矛盾中心,又维护了领主的威望。
可是领主并不愿意直接插手征兵事务,而是效仿政府的做法,让村社具体负责新兵的选派工作,③即选兵权属于村社,只为自己保留确定征兵原则、监督征兵过程、批准米尔决议书的权利。早在1718年,领主Д.А.舍佩廖夫就明确了村社的选兵权:“选择谁去当兵应当由农民在米尔会议上决定。”[14](p231)领主А.Б.库拉金也公开表示,征兵活动“由米尔考虑”[15](p261~262)。这样一来,农奴主将本该自己负责的兵役义务转嫁给村社。从这方面说,兵役义务与其说是领地义务,还不如说是村社义务。为国家挑选和派送新兵成为村社一项重要职责。
毫无疑问,这种层层下放、缺乏统一征兵标准的政策,客观上造成全国选兵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尽管不同的村社在选兵的具体操作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经过考察我们发现,他们在选兵制度方面大体上均经历了“按单身男子→按大家庭→普遍按户→按人头”原则的演变过程。
18世纪初,许多村社按照国家选派单身男子去当兵的原则派送新兵。列日涅沃村社在18世纪40~50年代就是完全依靠犯罪嫌疑人、单身汉、欠税人、不务正业的浪荡人来保证新兵选派任务的。[15](p247)这一原则在某些村社甚至坚持到18世纪下半期。不能夸大奉行这种原则的村社的数量和该规则存续的时间,因为该原则是建立在兵役规模比较小的基础上的。随着对新兵数量需求的不断增多,按照这种原则显然无法完成征兵任务。于是,绝大多数村社在18世纪中叶将兵役义务推行到有家眷的农民身上。
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参照纳税人头的选兵原则使得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复杂化。在由许多村庄、村社构成的大组合村社里,米尔会议首先将全部村庄分成若干村庄小组,这些村庄小组根据现有的人头数来彼此分摊分配给全村社的新兵数;然后,在村庄小组内通过抓阄确定各村庄、村社选派新兵和为他们配备军需品的顺序;紧接着,在村庄、村社内部,那些有家眷的农民通过抓阄产生出服兵役的顺序。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有家眷的农民实际上指的是有多个纳税人头的大家庭,至于究竟有几个纳税人头的家庭必须参加兵役抓阄、排队,各个村社的规定却很不一致。在皮斯佐沃村社,1771年前规定只从拥有不少于3个劳力的家庭中选送新兵[15](p253);在И.И.舒瓦洛夫的领地上,有3~4个儿子的农民有义务提供1名兵役,有2个儿子的农民有义务提供半个兵役,其他农民家庭则要交纳兵役费[16](p228,229)。
根据家庭中男性人口的多少,村社通常将农户负担兵役义务的顺序列为几个梯队:男性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被列做第1序列。在舍列梅捷夫家族的领地上,多于3个儿子(不包括养子和女婿)的家庭被列为第1类,有3个儿子的家庭被列为第2类,有2个或1个儿子的家庭被列做第3类。兵役顺序从第1类家庭的父亲开始,当这一轮排队结束后,接着的排队从第2类家庭的父亲开始,当第2轮排队结束后,第3轮排队又从第3类家庭开始。[17](p152)这种按家庭、只从大家庭选派新兵的制度是村社平均主义传统的产物,它无疑地保存了劳力少的家庭,促进了村社内部农民家庭劳动潜力的平均化,却加重了大家庭的负担。因此,为了摆脱兵役义务,许多家庭就纷纷采取分家的方式来逃避。这样,按大家庭分配新兵的做法走进了死胡同。
在依靠大家庭履行兵役义务的做法遭到大家庭的反对后,一些村社接着推行普遍按户的选兵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不仅大家庭,而且两人家庭同样需要负担兵役。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家庭——不考虑他们的赋税和人头状况——均参与抓阄。在对兵役义务按户排序时,一般以20年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个农户在提供兵役的时候,被免除义务税20年;如果士兵战死疆场,那么对这个农户来说结束排队的期限就被延长,新的排队从他去世算起20年后才开始;如果分家,而新兵在分家之前被家庭派出,那么结束排队的20年期限对两个家庭均有效;作为“受处罚的农民”被送去当兵的家庭不享受此种排队优惠;赎免兵役义务的家庭,排队的期限从缴纳兵役费之日起20年或10年后——购买整个兵役提供全部20年的优惠,购买半个兵役提供10年优惠。[15](p256)同样,一个家庭赎买兵役义务只对一个循环周期有效,在分家的情况下,只为家长保留赎买兵役义务的权利,晚辈则参加当前这一轮循环顺序的抓阄,而不管他们已经缴纳了多少赎买费。在具体实践中,农奴主为了保持农民的赋税能力和减轻负担,通常不主张从两人家庭中选派新兵,而由他们用货币赎买兵役。可是这种看似优惠的政策却给小家庭农民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在基亚索夫卡村社,两人家庭在1821~1824年间应缴纳兵役赎买费68315卢布,而实际上只缴纳了7499卢布,尚欠交60816卢布。[15](p256)很显然,这种状况削弱了小家庭农民的赋税能力,加重了村社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④是领主和村社都不愿看到的。为避免这种后果,许多村社不得不取消小家庭的兵役义务。可是农民们利用了这一漏洞,争相分家,“通过此举逃避兵役排队”[18](p274)。
在这种两难情况下,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发生进一步的演变,代之以每个家庭的全部男性人口都必须承担兵役义务即男性普遍兵役制。存在着用货币抵补摊到男性家庭成员身上的兵役义务份额或提供实体人两种途径。在后一种情况下,离家去服兵役的家庭成员不仅抵消了自己的兵役义务份额,而且还承担了家庭其他成员的份额。
村社内部选派新兵按照排队。如上所述,村社首先将那些有过错、疏于耕作、欠缴税款、光棍单身的农民送去当兵,然后再把剩下的兵役名额向全村社摊派。谁去当兵,根据抓阄来确定。为了体现村社公正性原则,按照规定,所投放的阄必须与全村社本轮排队应承担兵役义务的家庭或人头数相等。抓到兵役阄的被派去当兵。
必须指出,在按家庭和男性人口排队征兵的方式下,村社只是将兵役义务分摊到家庭,至于最后派谁去服役则由家长决定。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其地位得到家庭所有成员、村社甚至政府的认可”[19](p171)。家长往往利用自己的宗法制权威在家庭派送新兵方面以权谋私,将兵役义务转嫁到其他旁系亲属身上。在1787年波戈列尔基村社派送的150个新兵中,只有12个家长和他们的10个儿子,其余均为家庭中的所谓旁系亲属——72个家长的胞兄弟、5个家长的堂兄弟、37个家长的亲叔叔、1个堂叔叔、7个侄儿和1个前妻的儿子。[15](p287)即便是在只有一对夫妇的亲兄弟家庭中,担当家长的长兄为了能留下自己的儿子,常把落到家庭的兵役义务转嫁给弟弟或者叔叔。
三 商品货币关系对兵役义务的影响
18世纪中叶起,农民外出打工、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数逐年增加,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村社内部社会分化加剧。这在中部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莫斯科县和雅罗斯拉夫尔省为例,前者离开村社到城市务工的农民1764年为4331人,1765年为5 263人,1766年为6824人,1767年为9515人,1768年为12779人,1769年达到13026人;后者18世纪60年代初为外出农民发放身份证2万张(占全省男性人口的9%),1765年2.7万,[20](p153~155)18世纪末外出人数增至5.5万~7.5万(23%),19世纪50年代更是高达105887人(26%)。[21](p166.167)
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兵役制度造成强烈冲击,部分改变着农民履行兵役义务的方式。从18世纪中叶起,个别村社开始允许被摊到兵役任务的农民家庭通过用货币购买来抵补新兵名额。为鼓励农民赎买兵役义务,村社甚至还推出不同的优惠措施。1758年,在谢尔巴托夫家族的领地上,农民家长如果购买半个新兵,其家庭可以获得全免1年代役租和劳役的优惠,下一年也只需承担代役租和劳役的一半份额;如果农民家庭独自缴纳1名新兵的价钱,那么就全免其2年的代役租,另2年只缴纳代役租的一半,4年不承担任何劳役。此外,在前一种情况下,农民家庭被免除今后的3次招兵排序;在后一种情况下,农民家庭被免除参与今后7次的征兵。[15](p249)这种赎免兵役的制度呈扩大化、合法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许多农民愈益愿意花钱赎买兵役,他们“不是用实体人去承担兵役义务,而是购买新兵”[22](p306)。在波戈列尔基村社,据1787年的兵役清单,纯粹用钱来赎买摊到自己身上的兵役份额的有111个家庭,还有10个家庭同时派送实体人和花钱赎买兵役份额,120个家庭只用实体人履行兵役义务;而在此之前,派送实体人的家庭有150个,花钱赎买兵役的却只有55个。[15](p260)通常,愿意赎买兵役义务的农民必须向村长提出书面申请,在申请书中农民应具体地说明抵买兵役的份额及用途(为自己还是为孩子),并对缴费的顺序和缴费的期限作出保证。在外地打工的农民更乐意用货币方式承担兵役义务。为了解决外出务工农民赎买兵役的问题,村社通过领主设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领地办事处向这类农民办理赎买兵役的手续。
人口和土地是农奴主谋取财富的基本来源。因而,出于留住劳动人手的考虑,农奴主一般鼓励农民用货币赎买兵役义务,苏沃洛夫“甚至完全禁止自己的领地派实体人去当兵”[22](p306)。兵役买卖现象也为农奴主加强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创造了条件。农奴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从中获利:一是鼓动不愿提供实体人服役的家庭交纳兵役赎买费,并将其据为己有,然后强行将那些欠税、行为不检点的农民送去服役。这种赎买费数额巨大。谢尔巴托大家族沃斯克列先斯科耶领地和罗曼诺沃一鲍里索格列布斯基领地上的农民,为免除兵役义务在18世纪80年代到1827年间交纳赎买费101988卢布,舍列梅捷夫家族莫洛多图德领地的农民在1800~1855年间也为此交纳了101134卢布。[23](p285)二是出售自己的农奴代替别的村社去当兵。18世纪50年代,某地主因出售100个农奴去当兵而获利1.6万卢布。[22](P119)
村社从赋税的角度亦鼓励农民赎买兵役义务。作为领主与农民的中间人,村社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替领主向农民征收赋税地租,并对其成员的税费和欠税承担责任。为保持本村社总体赋税能力,村社自然不愿意失去最能贡献赋税的成年男性劳力尤其是富裕农民。毫无疑问,赎买兵役义务是村社解决兵役义务与赋税能力两难问题的最佳途径。为了避免本村社农民去当兵,个别村社甚至采取“合伙出资”的形式到外村社雇佣农民代替本村社去当兵。[24](p39)这种送“雇佣者”去当兵的做法得到了国家的默许。
用货币赎买兵役义务的方式也为国家增加兵役名额借此大肆敛财提供了方便,故而国家每年向村社推销所谓的“兵役证”。村社则为了本村社农民的利益,避免兵役证涨价,常常提前预先购买一定量的兵役证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再将兵役证出售给村社农民。根据阿里斯杰耶夫村社和西多洛沃村社的情况可以具体地判断出购买兵役证和赎买兵役义务的规模。在1793~1809年的16年间,阿里斯杰耶夫村社计有345个农户,他们花费19688卢布购买了32张兵役证,这些兵役证可以抵买128个农民的兵役义务;⑤在有412个农户(1424个男性人头)的西多洛沃,村社在1798~1809年间征收了37039卢布,共购买兵役证60张,可以抵买240个人的兵役义务。[15](p266)到19世纪初,购买兵役证已成为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23](p285)
兵役买卖的普遍流行使兵役义务事实上变成村社内部的货币税,而只有农村中经济实力强大的农民才有能力交纳这种高昂的货币税。据著名史学家科瓦利琴科研究,一张可以免除兵役义务20~25年的全价兵役证,在19世纪上半期价值2000卢布。[23](p285)很显然,赎买兵役义务属于富裕农民的特权,贫穷农民面对高额费用只能打消这种念头,不得不提供实体人去当兵。赎免兵役制度的出现,是农村居民财产分化的表现,是村社内部农民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标志,它证明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开始从实体人充实军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可见,随着农民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从18世纪中叶起村社内部这种糅合了货币赎买成分的兵役选派制度更多地显现出社会分化的特征:有钱人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赎买兵役义务,逃脱事实上的兵役负担,而没有能力赎买兵役义务的中等和贫穷农民则只好去当兵:“不好的即最贫穷的农民的孩子死在医院里或战场上……而最好的农民家庭、最认真和最听话顺从的农民留在庄园里,被自己好心肠的老爷保护了起来。”[25](p465~466)
四 兵役义务的社会功能
在保障军队兵源的同时,封建晚期的兵役义务客观上还发挥着别样的社会功能。
前面谈到领主(农奴主/地主)不直接插手征兵事务、选兵权属于村社,这并不意味着领主在兵役问题上放任不管。恰恰相反,兵役义务是领主进行农奴制统治的重要方式,是领主和村社惩罚“不顺从”农民、“纯洁”农村社会成分、“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手段。
俄国农奴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领主通常不直接与农民打交道,而是通过向村社发布领地指示、借助于村社对农民实行统治,村社成为领主意志的执行者。从这方面说,村社是领主维护农奴制度的工具。但另一方面,村社在传统上是农民的自治机构,扮演着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在领主和农民两者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村社一般选择站在领主一边。许多形式上由村社推行的举措实际上是领主意志的体现。
兵役义务始终贯穿着领主的意志。尽管各村社在选兵制度方面没有划一性,但是不论在何时、不管在哪个村社,首先必须遵循的是领主所制定的原则:优先送那些应受处罚的农民去当兵。1774年,领主С.К.纳雷什金亲自下令无需排队抓阄,首先将那些“形迹可疑的人、酒鬼、懒汉和游手好闲之徒送去当兵”,若有不适合服役者,亦以兵役名义将其流放。[15](p274)1824年,领主Д.Н.舍列梅捷夫给莫洛多图德村社的管理人员舒茨基写信,要求“将好打架的、有恶劣行为的人送去当兵,哪怕是不轮到他们”[17](p152)。至于“恶劣行为”的标准,则完全由农奴主确定。农奴主常以此为由将不合心意的叛逆人士送去当兵,逐出领地。在奥尔洛夫家族的叶洛霍沃领地,1798~1803年间派送新兵25个,其中受处罚者不少于11人。[15](p275)
兵役义务带给农民更多的是精神失落。村社是农民的整个世界,是农民的生活依靠。被派出服役,就意味着将永远离开村社这个集体,为大家所抛弃。这对于自小“紧抱着村社不放,甚至不敢想象没有村社自己能否生存”[26](p64)的俄国农民来说,不仅是肉体的别离,更是心灵的折磨、精神的惩罚。
所以,对农民而言,兵役与其说是国家义务,不如说是农奴主驯服农民的工具。
兵役义务的严酷性令农民对其望而生畏。为了逃避兵役负担,有些农民甚至不惜自残,他们“损伤眼睛,砍断手指,(故意)危害其他成员”[17](p155)。1789年,农民П.达尼洛夫故意砍断自己的脚趾;1795年,农民П.阿列克谢耶夫跺掉左手食指。[10](p186)
村社严厉处罚那些逃避兵役义务的人:有一般过失的农民被送往别的领地去做苦力或在本村社做份外的公益工作;对于那些以逃跑的方式躲避兵役义务的农民,村社采取拆毁房子、搬走粮食、赶走牲畜等方式加以惩处,被捉回的人往往遭到鞭笞,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11](p348)
在派送受处罚的农民去服役的问题上,领主的利益与村社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于领主来说,在自己的领地上维持农奴制统治是首要任务,兵役义务是达到这一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对于村社来说,这些人赋税能力低下,忤逆村社“一致性”原则,成为村社的累赘,将他们送去当兵,既能满足兵役要求,又可清除社会不安定因素。
领主和村社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政府军事部门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尽管这类新兵是被当做受处罚送来服役,但也并非是刑事犯,因为犯有杀人、纵火、抢劫等重罪的刑事犯早有国家进行审判和处治。他们自信,在军队严酷纪律的约束下,这些人不会对军队构成特别的威胁。1812年卫国战争结束后,在兵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军事部门甚至主动向地主和村社提出将那些被认为是“不听话的、不安分守己的、在村社内容不得人的”民兵留在军队里。[15](p277)
除了农奴制的社会功能外,兵役义务还是村社实行社会平均化的重要途径,是村社平均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经济形态下的生产主要是土地经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地租剥削,通过以份地的形式将士地交给农民使用而后向他们征收赋税来实现。村社扮演着地主与农民之间中间人的角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事实上都由村社来完成。分摊赋税、征收赋税、送交赋税构成村社的赋税职能。所以,马克思称村社是“下金蛋的母鸡”[27](p440)。村社的任务不仅在于分摊并征收赋税,而且对其成员的税费和欠税负有完全的责任。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村社内的总体赋税能力,村社在选派新兵的时候也将经济上贫困、很少赋税潜力、缺乏劳动能力的农民列为优先考虑的对象。1788年莫洛多图德乡米尔会议作出决定:“送71个或疏于耕作、或不缴纳赋税、或是有犯罪嫌疑、或是光棍穷人的农民去当兵。”[17](p152)同年,尼科里斯科耶村社送7个人去当兵,其中40~45岁的就有5人。[15](p279)这样,村社利用兵役义务,首先将不安分守己的农民和贫穷农民送去当兵,逐出村社。紧接着,如前所述,在进行兵役义务排序时,村社优先安排多子家庭服兵役,削弱其依靠人力资源致富的潜力,然后再向富裕农民收取兵役赎金。
那些“逃脱”了兵役义务的农民其实并不轻松,他们必须负担新兵的装备和薪水,犒劳新兵亲属,给接兵官员的行贿费及礼物。彼得一世规定,选派新兵者有义务保障新兵的便服,给他们提供一年的薪水和给养。这些规定一直保持下来。博戈斯洛夫斯基村社1797年为派送1个新兵而向全村社征收了44卢布60戈比,平均每个成年人负担20戈比,其中16卢布用于新兵的服装和鞋子,22卢布用作给接兵司令部的医生和中尉的“礼品”,剩下的给新兵用在路上花销。1798年该村社为送3个新兵又征收了102卢布58戈比。[10](186)在舍列梅捷夫家族的领地上,1781年按每一特列特尼克(征税单位——作者注)为新兵征收1卢布货币费、1俄升黑麦、半俄升燕麦粉。[17](p155)
村社在征兵的过程中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推动村社内部农民生活水平的平均化,从而既增强赋税能力,又避免因贫富差距悬殊而危及村社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兵役义务很快便超出了纯军事范畴,被赋予更多的社会经济色彩,兵役制度也演变为一种独特的农村社会制度,贯穿于整个农奴制农村社会生活。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充分展示了村社的二重性特征:既履行帮助农奴主压迫和剥削农民(农奴制)的功能,也肩负着通过平均主义传统保护农民的职责。透过封建晚期俄国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我们清晰地看到,村社所固有的二重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社会各方的利益要求,为国家、农奴主、农民所需要和依靠,由此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开俄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谜团——村社制度以及农奴制度为什么能在俄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兵役制度也向世人证明农奴主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随着农民卷入市场经济,兵役来源日渐枯竭,从最初的所有纳税等级参与选派演化为农民阶级的专属义务,而农民中的富裕阶层也逐渐从兵役义务中脱身而出,兵源的不断萎缩使这种兵役制度走进了死胡同,所以新的兵役制度——普遍义务兵役制也就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应运而生了。
注释:
①源自法语recruter,即“被征召的新兵”。因这些新兵来自纳税等级,国内有学者因此称之为“税兵”,将这种兵役制度称为“税兵制”。
②国有村社和皇室村社直到1838年才获得法人权,而地主村社则迟至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才逐渐成为基层行政机构。
③在封建晚期,农奴主通常以领地为单位保留或创建农村公社。这样,领地与村社是同一的:对农奴主来说是领地,对农民来说则是村社。
④按照连环保原则,村社其他成员有义务分摊本村社农民的欠税。
⑤一张兵役证通常可以免除4个兵役义务。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11期第69~75,81页
【作者简介】罗爱林,历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广西 桂林 541001
| 【内容提要】 | 18世纪初,俄国确立等级义务兵役制,农民的兵役义务由此产生。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实施。村社在选派新兵时力求遵循平均主义原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开始从实体人充实军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这是农村社会分化的标志。兵役义务不仅是地主进行农奴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农奴主和村社惩罚“不顺从”农民、“纯洁”农村社会成分、“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手段。 |
俄国的兵役义务肇始于18世纪初,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等级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从彼得一世改革起,到1874年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止,服兵役只是纳税等级的义务。随着贵族、教士、商人被豁免兵役,兵役事实上成为农民的专属义务。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保障兵役义务的实施。为国家选派新兵是村社的一项重要职责。研究这一时期俄国村社在农民兵役义务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俄国兵役制度、村社职能以及农奴制度特点的认识。
一 等级义务兵役制的确立
兵役作为一种国家义务,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确定下来。在此之前,俄国“没有一名真正的士兵”,“没有一支受过作战训练的军队”,[1](p25,26)当兵打仗是贵族等级的特权。
基辅罗斯时期,国家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王公亲兵队。王公亲兵队由志愿人员组成,人数一般在200~400人。[2](p106)亲兵与王公是一种契约关系,亲兵可自由加入或退出亲兵队。王公则将部分战利品和贡物分发给亲兵作报酬。从兵役制度的角度看,这是雇佣兵制度(募兵制)的萌芽。
莫斯科公国延续了这种兵役制度,所不同的是亲兵演变为服役贵族,实物报酬被封地所取代。随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封地制的发展,已获得大量封地的贵族开始逃避服役。1556年,伊凡四世颁布《军役法》,规定无论是领地波雅尔还是封地贵族,“每100切特维基良地须提供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3](p124)。为了护卫京城,伊凡四世还开始建立一支使用火器的射击军。射击军士兵多从手工业者、商人中招募而来,服役期间由国家付给军饷、军服和食物。他们可以带家属,战时执行军事任务,平时则经营自己的工商业。[4](p11)
贵族军队存在着诸多弊端:平时经营地产,怠于军事训练;战时纪律松弛,行动懒散,缺乏战斗力。因此,从17世纪起,贵族军队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新制骑兵团和步兵团成为军队的主要类型。这种新制军团起初采用募兵制,由国家提供薪水,每年秋季集训1个月,之后分散回家。但从17世纪40年代起,政府开始不定期地在农民中强制性征召“差丁”(даточный)作为军队的补员。所谓的“差丁”,指的是被政府强行征人军队的农奴。他们服役不是为了获得报酬,只是被迫履行无偿义务。俄国兵役制度开始由募兵制逐渐向义务兵役制(征兵制)过渡。
彼得一世建立起近代化的正规陆海军,并最终将兵役制度变为纳税居民义务兵役制。1699年11月17日,在对瑞典战争前夕,彼得一世下令强制征召3.2万名“差丁”入伍。随着对瑞典战争的进行,旧兵役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兵员严重匮乏,制约着战争的深入和持久。有鉴于此,1705年2月彼得一世颁布敕令,将不定期的补员征兵改为常规征兵,所征新兵称做“pekpym”。①从此,服兵役成为俄国纳税等级义不容辞的国家义务。俄国正式过渡到义务兵役制。
义务兵役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纳税等级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从1705年彼得一世颁布敕令起,到1874年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止,服兵役只是纳税等级的义务。
随着贵族、教士、商人被豁免兵役,兵役义务后来主要落在农民身上,成为农民阶级的专属义务。“1762年以前,贵族是赋税等级,就是说与其他等级一样,要承担义务。”[5](p307)但是,贵族等级逐渐享有特权,并最终从兵役义务中脱身出来:1736年贵族服役的年限缩短到25年,1740年贵族被允许在服役和公职之间作出选择,1762年颁布的《贵族自由诏书》正式免除贵族的兵役义务。18世纪30年代,教士和商人被赋予可以花钱雇人去当兵的权利;紧接着,兵工厂的匠人亦获得此项特权;到19世纪初,商人和僧侣不再承担任何军事义务。至此,等级义务兵役制事实上变成农民义务兵役制。
等级义务兵役制实施之初,只是在俄罗斯居民当中招收新兵,从18世纪下半期起开始推广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
在新兵役制推行初期,国家只规定征召新兵的年龄条件和家庭条件,年龄被限制在15~20岁,仅征募单身汉。[6](p291~292)后来,对新兵的家庭状况不作考虑,仅规定新兵的年龄和身高,如1757年的征兵通令要求新兵的年龄从20岁到35岁,身高不低于2俄尺4俄寸即1.60米;[7](p840~841)1766年,新兵年龄下限降低到17岁,其他所有条件照旧,并在以后得到坚持。[8](p1000)
1724年第1次人口普查结束前,以户为单位征兵,大约每20户征1名新兵。[9](p617)这次人口普查结束后转为根据男性人口数进行摊派。依征兵总数不同,每次摊派的比例不一。最初每500个男性人口征收1名新兵,18世纪80年代后则依次增加到每250、200、100个征1名新兵。[10](p185)到1831年,普通征兵时每千人征5~7名新兵,加强征兵的时候增加到7~10名,而特别征兵时则超过10名;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甚至达到每千人征50~70名。[9](p617)
服役年限被多次缩减。最初,兵役义务是终身的。1793年,服役期限改为25年。1834年开始变相缩短服役年限:只要服役满20年,剩下的5年就可以离职休假。亚历山大二世接着又将服役年限压缩到15年,并在1855~1872年间分三次改变服役方式:从服役12年后休假3年、服役10年后休假5年直至变为服役7年后休假8年。有意思的是,这种缩短服役期限的政策遭到了地主的强烈抵制。因为缩短服役期限势必需要有更多的农民作后备替补,地主当然不愿意损失自己的农奴,失去劳动人手;此外,地主也害怕退伍回乡的士兵在家乡为非作歹,增加管理难度。
据统计,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头25年间,除了非定期的征召民兵外,总共进行了90次征兵。随着不断对外扩张,征召进军队的新兵人数日趋增多。18世纪头25年征兵53次,征募的新兵超过28.4万人,占第1次人口普查材料中男性人口总数的3.6%多;[11](p347)1726~1760年征募了79.5万新兵,1767~1799年的新兵数是125.2万,都各占第3次人口普查(1762年)和第5次人口普查(1795年)材料中男性人口总数的7%;[12](p23~37、294~297)19世纪头25年,征募了200万新兵,占1833年第8次人口普查中男性人口总数的8%。[13](p74)兵役成为农民最繁重的国家义务。
二 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
在封建晚期,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发布征兵命令,提出征兵额度,规定征兵条件以及服役年限等。服兵役属于所有纳税等级的应尽义务。但就农民来说,却非其个人义务,而是领地义务。换言之,国家将兵役名额分解到各领地,然后由领地来履行兵役义务。国家只关注于领地按时、足额提供新兵,而不管这些新兵是以什么方式挑选出来的。
国家将挑选新兵的权力下放给领地,出于三方面的考虑:在法律层面上,承担兵役义务的农民属于领主的私有财产,他们去服兵役客观上损害了领主的经济利益,这就需要得到后者的理解和支持;从行政方面说,封建晚期俄国农村没有国家行政机构,乡、村一级村社属于农民的自治组织,②国家行政机构与农民自治组织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领地管理机构是国家意志到达农村的唯一渠道;在具体操作上,国家将挑选新兵的权力下放给领地,既使自己置身于繁琐的征兵事务之外、不至处于矛盾中心,又维护了领主的威望。
可是领主并不愿意直接插手征兵事务,而是效仿政府的做法,让村社具体负责新兵的选派工作,③即选兵权属于村社,只为自己保留确定征兵原则、监督征兵过程、批准米尔决议书的权利。早在1718年,领主Д.А.舍佩廖夫就明确了村社的选兵权:“选择谁去当兵应当由农民在米尔会议上决定。”[14](p231)领主А.Б.库拉金也公开表示,征兵活动“由米尔考虑”[15](p261~262)。这样一来,农奴主将本该自己负责的兵役义务转嫁给村社。从这方面说,兵役义务与其说是领地义务,还不如说是村社义务。为国家挑选和派送新兵成为村社一项重要职责。
毫无疑问,这种层层下放、缺乏统一征兵标准的政策,客观上造成全国选兵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尽管不同的村社在选兵的具体操作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经过考察我们发现,他们在选兵制度方面大体上均经历了“按单身男子→按大家庭→普遍按户→按人头”原则的演变过程。
18世纪初,许多村社按照国家选派单身男子去当兵的原则派送新兵。列日涅沃村社在18世纪40~50年代就是完全依靠犯罪嫌疑人、单身汉、欠税人、不务正业的浪荡人来保证新兵选派任务的。[15](p247)这一原则在某些村社甚至坚持到18世纪下半期。不能夸大奉行这种原则的村社的数量和该规则存续的时间,因为该原则是建立在兵役规模比较小的基础上的。随着对新兵数量需求的不断增多,按照这种原则显然无法完成征兵任务。于是,绝大多数村社在18世纪中叶将兵役义务推行到有家眷的农民身上。
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参照纳税人头的选兵原则使得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复杂化。在由许多村庄、村社构成的大组合村社里,米尔会议首先将全部村庄分成若干村庄小组,这些村庄小组根据现有的人头数来彼此分摊分配给全村社的新兵数;然后,在村庄小组内通过抓阄确定各村庄、村社选派新兵和为他们配备军需品的顺序;紧接着,在村庄、村社内部,那些有家眷的农民通过抓阄产生出服兵役的顺序。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有家眷的农民实际上指的是有多个纳税人头的大家庭,至于究竟有几个纳税人头的家庭必须参加兵役抓阄、排队,各个村社的规定却很不一致。在皮斯佐沃村社,1771年前规定只从拥有不少于3个劳力的家庭中选送新兵[15](p253);在И.И.舒瓦洛夫的领地上,有3~4个儿子的农民有义务提供1名兵役,有2个儿子的农民有义务提供半个兵役,其他农民家庭则要交纳兵役费[16](p228,229)。
根据家庭中男性人口的多少,村社通常将农户负担兵役义务的顺序列为几个梯队:男性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被列做第1序列。在舍列梅捷夫家族的领地上,多于3个儿子(不包括养子和女婿)的家庭被列为第1类,有3个儿子的家庭被列为第2类,有2个或1个儿子的家庭被列做第3类。兵役顺序从第1类家庭的父亲开始,当这一轮排队结束后,接着的排队从第2类家庭的父亲开始,当第2轮排队结束后,第3轮排队又从第3类家庭开始。[17](p152)这种按家庭、只从大家庭选派新兵的制度是村社平均主义传统的产物,它无疑地保存了劳力少的家庭,促进了村社内部农民家庭劳动潜力的平均化,却加重了大家庭的负担。因此,为了摆脱兵役义务,许多家庭就纷纷采取分家的方式来逃避。这样,按大家庭分配新兵的做法走进了死胡同。
在依靠大家庭履行兵役义务的做法遭到大家庭的反对后,一些村社接着推行普遍按户的选兵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不仅大家庭,而且两人家庭同样需要负担兵役。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家庭——不考虑他们的赋税和人头状况——均参与抓阄。在对兵役义务按户排序时,一般以20年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个农户在提供兵役的时候,被免除义务税20年;如果士兵战死疆场,那么对这个农户来说结束排队的期限就被延长,新的排队从他去世算起20年后才开始;如果分家,而新兵在分家之前被家庭派出,那么结束排队的20年期限对两个家庭均有效;作为“受处罚的农民”被送去当兵的家庭不享受此种排队优惠;赎免兵役义务的家庭,排队的期限从缴纳兵役费之日起20年或10年后——购买整个兵役提供全部20年的优惠,购买半个兵役提供10年优惠。[15](p256)同样,一个家庭赎买兵役义务只对一个循环周期有效,在分家的情况下,只为家长保留赎买兵役义务的权利,晚辈则参加当前这一轮循环顺序的抓阄,而不管他们已经缴纳了多少赎买费。在具体实践中,农奴主为了保持农民的赋税能力和减轻负担,通常不主张从两人家庭中选派新兵,而由他们用货币赎买兵役。可是这种看似优惠的政策却给小家庭农民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在基亚索夫卡村社,两人家庭在1821~1824年间应缴纳兵役赎买费68315卢布,而实际上只缴纳了7499卢布,尚欠交60816卢布。[15](p256)很显然,这种状况削弱了小家庭农民的赋税能力,加重了村社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④是领主和村社都不愿看到的。为避免这种后果,许多村社不得不取消小家庭的兵役义务。可是农民们利用了这一漏洞,争相分家,“通过此举逃避兵役排队”[18](p274)。
在这种两难情况下,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发生进一步的演变,代之以每个家庭的全部男性人口都必须承担兵役义务即男性普遍兵役制。存在着用货币抵补摊到男性家庭成员身上的兵役义务份额或提供实体人两种途径。在后一种情况下,离家去服兵役的家庭成员不仅抵消了自己的兵役义务份额,而且还承担了家庭其他成员的份额。
村社内部选派新兵按照排队。如上所述,村社首先将那些有过错、疏于耕作、欠缴税款、光棍单身的农民送去当兵,然后再把剩下的兵役名额向全村社摊派。谁去当兵,根据抓阄来确定。为了体现村社公正性原则,按照规定,所投放的阄必须与全村社本轮排队应承担兵役义务的家庭或人头数相等。抓到兵役阄的被派去当兵。
必须指出,在按家庭和男性人口排队征兵的方式下,村社只是将兵役义务分摊到家庭,至于最后派谁去服役则由家长决定。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其地位得到家庭所有成员、村社甚至政府的认可”[19](p171)。家长往往利用自己的宗法制权威在家庭派送新兵方面以权谋私,将兵役义务转嫁到其他旁系亲属身上。在1787年波戈列尔基村社派送的150个新兵中,只有12个家长和他们的10个儿子,其余均为家庭中的所谓旁系亲属——72个家长的胞兄弟、5个家长的堂兄弟、37个家长的亲叔叔、1个堂叔叔、7个侄儿和1个前妻的儿子。[15](p287)即便是在只有一对夫妇的亲兄弟家庭中,担当家长的长兄为了能留下自己的儿子,常把落到家庭的兵役义务转嫁给弟弟或者叔叔。
三 商品货币关系对兵役义务的影响
18世纪中叶起,农民外出打工、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数逐年增加,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村社内部社会分化加剧。这在中部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莫斯科县和雅罗斯拉夫尔省为例,前者离开村社到城市务工的农民1764年为4331人,1765年为5 263人,1766年为6824人,1767年为9515人,1768年为12779人,1769年达到13026人;后者18世纪60年代初为外出农民发放身份证2万张(占全省男性人口的9%),1765年2.7万,[20](p153~155)18世纪末外出人数增至5.5万~7.5万(23%),19世纪50年代更是高达105887人(26%)。[21](p166.167)
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兵役制度造成强烈冲击,部分改变着农民履行兵役义务的方式。从18世纪中叶起,个别村社开始允许被摊到兵役任务的农民家庭通过用货币购买来抵补新兵名额。为鼓励农民赎买兵役义务,村社甚至还推出不同的优惠措施。1758年,在谢尔巴托夫家族的领地上,农民家长如果购买半个新兵,其家庭可以获得全免1年代役租和劳役的优惠,下一年也只需承担代役租和劳役的一半份额;如果农民家庭独自缴纳1名新兵的价钱,那么就全免其2年的代役租,另2年只缴纳代役租的一半,4年不承担任何劳役。此外,在前一种情况下,农民家庭被免除今后的3次招兵排序;在后一种情况下,农民家庭被免除参与今后7次的征兵。[15](p249)这种赎免兵役的制度呈扩大化、合法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许多农民愈益愿意花钱赎买兵役,他们“不是用实体人去承担兵役义务,而是购买新兵”[22](p306)。在波戈列尔基村社,据1787年的兵役清单,纯粹用钱来赎买摊到自己身上的兵役份额的有111个家庭,还有10个家庭同时派送实体人和花钱赎买兵役份额,120个家庭只用实体人履行兵役义务;而在此之前,派送实体人的家庭有150个,花钱赎买兵役的却只有55个。[15](p260)通常,愿意赎买兵役义务的农民必须向村长提出书面申请,在申请书中农民应具体地说明抵买兵役的份额及用途(为自己还是为孩子),并对缴费的顺序和缴费的期限作出保证。在外地打工的农民更乐意用货币方式承担兵役义务。为了解决外出务工农民赎买兵役的问题,村社通过领主设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领地办事处向这类农民办理赎买兵役的手续。
人口和土地是农奴主谋取财富的基本来源。因而,出于留住劳动人手的考虑,农奴主一般鼓励农民用货币赎买兵役义务,苏沃洛夫“甚至完全禁止自己的领地派实体人去当兵”[22](p306)。兵役买卖现象也为农奴主加强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创造了条件。农奴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从中获利:一是鼓动不愿提供实体人服役的家庭交纳兵役赎买费,并将其据为己有,然后强行将那些欠税、行为不检点的农民送去服役。这种赎买费数额巨大。谢尔巴托大家族沃斯克列先斯科耶领地和罗曼诺沃一鲍里索格列布斯基领地上的农民,为免除兵役义务在18世纪80年代到1827年间交纳赎买费101988卢布,舍列梅捷夫家族莫洛多图德领地的农民在1800~1855年间也为此交纳了101134卢布。[23](p285)二是出售自己的农奴代替别的村社去当兵。18世纪50年代,某地主因出售100个农奴去当兵而获利1.6万卢布。[22](P119)
村社从赋税的角度亦鼓励农民赎买兵役义务。作为领主与农民的中间人,村社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替领主向农民征收赋税地租,并对其成员的税费和欠税承担责任。为保持本村社总体赋税能力,村社自然不愿意失去最能贡献赋税的成年男性劳力尤其是富裕农民。毫无疑问,赎买兵役义务是村社解决兵役义务与赋税能力两难问题的最佳途径。为了避免本村社农民去当兵,个别村社甚至采取“合伙出资”的形式到外村社雇佣农民代替本村社去当兵。[24](p39)这种送“雇佣者”去当兵的做法得到了国家的默许。
用货币赎买兵役义务的方式也为国家增加兵役名额借此大肆敛财提供了方便,故而国家每年向村社推销所谓的“兵役证”。村社则为了本村社农民的利益,避免兵役证涨价,常常提前预先购买一定量的兵役证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再将兵役证出售给村社农民。根据阿里斯杰耶夫村社和西多洛沃村社的情况可以具体地判断出购买兵役证和赎买兵役义务的规模。在1793~1809年的16年间,阿里斯杰耶夫村社计有345个农户,他们花费19688卢布购买了32张兵役证,这些兵役证可以抵买128个农民的兵役义务;⑤在有412个农户(1424个男性人头)的西多洛沃,村社在1798~1809年间征收了37039卢布,共购买兵役证60张,可以抵买240个人的兵役义务。[15](p266)到19世纪初,购买兵役证已成为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23](p285)
兵役买卖的普遍流行使兵役义务事实上变成村社内部的货币税,而只有农村中经济实力强大的农民才有能力交纳这种高昂的货币税。据著名史学家科瓦利琴科研究,一张可以免除兵役义务20~25年的全价兵役证,在19世纪上半期价值2000卢布。[23](p285)很显然,赎买兵役义务属于富裕农民的特权,贫穷农民面对高额费用只能打消这种念头,不得不提供实体人去当兵。赎免兵役制度的出现,是农村居民财产分化的表现,是村社内部农民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标志,它证明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开始从实体人充实军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可见,随着农民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从18世纪中叶起村社内部这种糅合了货币赎买成分的兵役选派制度更多地显现出社会分化的特征:有钱人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赎买兵役义务,逃脱事实上的兵役负担,而没有能力赎买兵役义务的中等和贫穷农民则只好去当兵:“不好的即最贫穷的农民的孩子死在医院里或战场上……而最好的农民家庭、最认真和最听话顺从的农民留在庄园里,被自己好心肠的老爷保护了起来。”[25](p465~466)
四 兵役义务的社会功能
在保障军队兵源的同时,封建晚期的兵役义务客观上还发挥着别样的社会功能。
前面谈到领主(农奴主/地主)不直接插手征兵事务、选兵权属于村社,这并不意味着领主在兵役问题上放任不管。恰恰相反,兵役义务是领主进行农奴制统治的重要方式,是领主和村社惩罚“不顺从”农民、“纯洁”农村社会成分、“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手段。
俄国农奴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领主通常不直接与农民打交道,而是通过向村社发布领地指示、借助于村社对农民实行统治,村社成为领主意志的执行者。从这方面说,村社是领主维护农奴制度的工具。但另一方面,村社在传统上是农民的自治机构,扮演着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在领主和农民两者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村社一般选择站在领主一边。许多形式上由村社推行的举措实际上是领主意志的体现。
兵役义务始终贯穿着领主的意志。尽管各村社在选兵制度方面没有划一性,但是不论在何时、不管在哪个村社,首先必须遵循的是领主所制定的原则:优先送那些应受处罚的农民去当兵。1774年,领主С.К.纳雷什金亲自下令无需排队抓阄,首先将那些“形迹可疑的人、酒鬼、懒汉和游手好闲之徒送去当兵”,若有不适合服役者,亦以兵役名义将其流放。[15](p274)1824年,领主Д.Н.舍列梅捷夫给莫洛多图德村社的管理人员舒茨基写信,要求“将好打架的、有恶劣行为的人送去当兵,哪怕是不轮到他们”[17](p152)。至于“恶劣行为”的标准,则完全由农奴主确定。农奴主常以此为由将不合心意的叛逆人士送去当兵,逐出领地。在奥尔洛夫家族的叶洛霍沃领地,1798~1803年间派送新兵25个,其中受处罚者不少于11人。[15](p275)
兵役义务带给农民更多的是精神失落。村社是农民的整个世界,是农民的生活依靠。被派出服役,就意味着将永远离开村社这个集体,为大家所抛弃。这对于自小“紧抱着村社不放,甚至不敢想象没有村社自己能否生存”[26](p64)的俄国农民来说,不仅是肉体的别离,更是心灵的折磨、精神的惩罚。
所以,对农民而言,兵役与其说是国家义务,不如说是农奴主驯服农民的工具。
兵役义务的严酷性令农民对其望而生畏。为了逃避兵役负担,有些农民甚至不惜自残,他们“损伤眼睛,砍断手指,(故意)危害其他成员”[17](p155)。1789年,农民П.达尼洛夫故意砍断自己的脚趾;1795年,农民П.阿列克谢耶夫跺掉左手食指。[10](p186)
村社严厉处罚那些逃避兵役义务的人:有一般过失的农民被送往别的领地去做苦力或在本村社做份外的公益工作;对于那些以逃跑的方式躲避兵役义务的农民,村社采取拆毁房子、搬走粮食、赶走牲畜等方式加以惩处,被捉回的人往往遭到鞭笞,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11](p348)
在派送受处罚的农民去服役的问题上,领主的利益与村社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于领主来说,在自己的领地上维持农奴制统治是首要任务,兵役义务是达到这一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对于村社来说,这些人赋税能力低下,忤逆村社“一致性”原则,成为村社的累赘,将他们送去当兵,既能满足兵役要求,又可清除社会不安定因素。
领主和村社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政府军事部门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尽管这类新兵是被当做受处罚送来服役,但也并非是刑事犯,因为犯有杀人、纵火、抢劫等重罪的刑事犯早有国家进行审判和处治。他们自信,在军队严酷纪律的约束下,这些人不会对军队构成特别的威胁。1812年卫国战争结束后,在兵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军事部门甚至主动向地主和村社提出将那些被认为是“不听话的、不安分守己的、在村社内容不得人的”民兵留在军队里。[15](p277)
除了农奴制的社会功能外,兵役义务还是村社实行社会平均化的重要途径,是村社平均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经济形态下的生产主要是土地经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地租剥削,通过以份地的形式将士地交给农民使用而后向他们征收赋税来实现。村社扮演着地主与农民之间中间人的角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事实上都由村社来完成。分摊赋税、征收赋税、送交赋税构成村社的赋税职能。所以,马克思称村社是“下金蛋的母鸡”[27](p440)。村社的任务不仅在于分摊并征收赋税,而且对其成员的税费和欠税负有完全的责任。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村社内的总体赋税能力,村社在选派新兵的时候也将经济上贫困、很少赋税潜力、缺乏劳动能力的农民列为优先考虑的对象。1788年莫洛多图德乡米尔会议作出决定:“送71个或疏于耕作、或不缴纳赋税、或是有犯罪嫌疑、或是光棍穷人的农民去当兵。”[17](p152)同年,尼科里斯科耶村社送7个人去当兵,其中40~45岁的就有5人。[15](p279)这样,村社利用兵役义务,首先将不安分守己的农民和贫穷农民送去当兵,逐出村社。紧接着,如前所述,在进行兵役义务排序时,村社优先安排多子家庭服兵役,削弱其依靠人力资源致富的潜力,然后再向富裕农民收取兵役赎金。
那些“逃脱”了兵役义务的农民其实并不轻松,他们必须负担新兵的装备和薪水,犒劳新兵亲属,给接兵官员的行贿费及礼物。彼得一世规定,选派新兵者有义务保障新兵的便服,给他们提供一年的薪水和给养。这些规定一直保持下来。博戈斯洛夫斯基村社1797年为派送1个新兵而向全村社征收了44卢布60戈比,平均每个成年人负担20戈比,其中16卢布用于新兵的服装和鞋子,22卢布用作给接兵司令部的医生和中尉的“礼品”,剩下的给新兵用在路上花销。1798年该村社为送3个新兵又征收了102卢布58戈比。[10](186)在舍列梅捷夫家族的领地上,1781年按每一特列特尼克(征税单位——作者注)为新兵征收1卢布货币费、1俄升黑麦、半俄升燕麦粉。[17](p155)
村社在征兵的过程中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推动村社内部农民生活水平的平均化,从而既增强赋税能力,又避免因贫富差距悬殊而危及村社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兵役义务很快便超出了纯军事范畴,被赋予更多的社会经济色彩,兵役制度也演变为一种独特的农村社会制度,贯穿于整个农奴制农村社会生活。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充分展示了村社的二重性特征:既履行帮助农奴主压迫和剥削农民(农奴制)的功能,也肩负着通过平均主义传统保护农民的职责。透过封建晚期俄国村社内部的选兵制度,我们清晰地看到,村社所固有的二重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社会各方的利益要求,为国家、农奴主、农民所需要和依靠,由此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开俄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谜团——村社制度以及农奴制度为什么能在俄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兵役制度也向世人证明农奴主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随着农民卷入市场经济,兵役来源日渐枯竭,从最初的所有纳税等级参与选派演化为农民阶级的专属义务,而农民中的富裕阶层也逐渐从兵役义务中脱身而出,兵源的不断萎缩使这种兵役制度走进了死胡同,所以新的兵役制度——普遍义务兵役制也就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应运而生了。
注释:
①源自法语recruter,即“被征召的新兵”。因这些新兵来自纳税等级,国内有学者因此称之为“税兵”,将这种兵役制度称为“税兵制”。
②国有村社和皇室村社直到1838年才获得法人权,而地主村社则迟至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才逐渐成为基层行政机构。
③在封建晚期,农奴主通常以领地为单位保留或创建农村公社。这样,领地与村社是同一的:对农奴主来说是领地,对农民来说则是村社。
④按照连环保原则,村社其他成员有义务分摊本村社农民的欠税。
⑤一张兵役证通常可以免除4个兵役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