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
——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
张建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8期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06年2期第32~38页
【作者简介】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关 键 词】欧亚主义/俄罗斯/苏联时代
中图分类号:K512;D032(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2—0032—07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冷战结束之际在他的新著《透视新世界》① 中写道:“过去的日子,世界发生了海滩滚滑车式的急转突变,从突然看到希望到幻想破灭,接着又是欣喜不已。”[1](P4)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留给欧洲人的记忆是痛苦和深刻的,欧洲人对“欧洲复兴”和“欧洲重建”的期盼心情是积极的,但又是复杂的。② 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将欧洲一体化推向新阶段。2003年5月,素有学怨的德、 法两大思想家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联袂著文《论欧洲的复兴》,向欧洲各国发出在“欧洲认同”(Europaeische Identitaet)基础上“超越欧洲中心主义”,“重新定位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的呼吁[2]。
俄罗斯复兴与欧洲复兴息息相关,但两者之间却充满了吊诡。就在西欧政治家和学者热切期盼欧洲复兴之际,在欧洲东端的俄罗斯(苏联)却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着孤寡之形象。不论冷战前夜丘吉尔的“欧洲合众国”梦想,还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核心欧洲”(Kerneuropa)构想,均不包括昨天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因为在欧美政治家和学者眼中,苏联完全是异类的“红色帝国”或“邪恶帝国”,今日的俄罗斯也不幸变成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特例,成为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3](P22)。困扰俄罗斯数个世纪的“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сфинкс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再现了。③ 与此同时,一个似曾相识的名词——“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开始频繁跃然新闻媒体之上和学者笔下,甚至是政治家谈话中。“欧亚主义”能不能复兴俄罗斯?这是一个让俄罗斯思想文化界既兴奋又迷茫的问题,它一下子把俄国—苏联—俄罗斯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吸引政治家和学者们思考。
一、复兴危机与问题的提出
自1991年底起,刚刚获得独立的俄罗斯即开始了它的“国家复兴”进程。它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它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4](P8—9)。毫无疑问,在告别了社会主义之后,俄罗斯选择了“纯粹”的西方式道路,即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经济上的纯市场经济、外交上的向西方一边倒、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俄罗斯复兴的核心即是“重返欧洲”,搭上“欧洲复兴的快车”,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叶利钦语)[5]。但是这个全方位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异常波折和时艰命蹇。
在政治转型方面:1990年10月12日,俄罗斯宪法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宪法草案,宣布在俄罗斯建立三权分立式的联邦共和国,规定“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俄罗斯议会、总统、宪法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它们根据分权原则独立地履行自己的职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总统是联邦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然而,“超级总统”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府”“院”权力之争旷日持久愈加严重,最终酿成1993年10月两者直接的武装对抗。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是当年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中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自由民主党”地位陡升,1995年12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大选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影响突进,震荡了脆弱的政党政治。
在经济复兴方面:1992年初开始的休克疗法试图以一步到位的形式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实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战略。但实施结果,使政府对市场失去了控制,投机资本肆虐,市场秩序极端混乱,生产急剧下滑,物价暴涨,政府财政赤字剧升,货币信贷体系濒临崩溃。从1992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连续四年居高不下,超过四位数字,1992年高达2610%,此后开始逐年下降,1993年为940%,1994年为320%,1995年仍然为131%。据俄经济学家统计, 1995年与1990年相比,消费品价格上涨了1700多倍[6](P374)。恶性通货膨胀大大阻碍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价格的飞涨使市场机制远远不能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力量,高通货膨胀率则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倾向,打击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助长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使整个经济生活陷入混乱之中。1993年8 月政府颁布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俄罗斯经济1993—1995年工作计划》,宣布调整政策,叶利钦也在1995年宣布:“今后不再实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5]
在外交政策方面:初期俄罗斯奉行了对西方和美国“一边倒”的做法。1992年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俄罗斯不仅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成是伙伴,而且看成是盟国。”[5] 外长科济列夫宣布俄罗斯将奉行与西方“完全伙伴化的方针,与西方一体化”。然而一年多的外交实践使俄罗斯领导人明白,以上的想法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叶利钦在1993年初访问韩国时提出了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外交政策。同年4 月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新构想》中强调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别,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进一步强化大国外交意识,加速发展全方位外交局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与前苏联拥有传统关系国家的关系,建立西方的莫斯科—柏林—巴黎,东方的莫斯科—新德里—北京轴心关系。1995年后,北约东扩加剧俄美矛盾。叶利钦总统警告,“如果北约东扩,一个与之军事对抗的军事联盟可能再次出现”,“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战争状态。”[5] 这表明,俄罗斯“重返欧洲”的进程严重受阻。
在国家复兴和社会转型全面受挫之后,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反思。“俄罗斯路标在何方?”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ЕвропеизмАтлатизм)在1993年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许多学者试图从文化、宗教、语言甚至族缘、血缘方面寻找俄罗斯与西欧的共同点。被誉为俄罗斯国学大师的利哈乔夫院士认为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东方国家,“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那维亚起决定性的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那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7](P21),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идосавия)。④ 曾担任过政府总理的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所长盖达尔认为,“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俄罗斯是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接触西方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走上西方道路的国家,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几乎跟上的状态中”[8](PP.52—53)。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强调:“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和文明的论点看,俄罗斯人是欧洲民族。”俄罗斯与西方“将尽一切努力来倡导共同的民主价值观”[5]。俄驻美大使卢金干脆称“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思潮”为“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国际主义”,以区别于苏联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9](P409)。
然而,几年来西方模式实践的失败宣告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道路的破产,也使这种思潮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思想文化界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当代哲学家梅茹耶夫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谓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10] 值得思索的是,19世纪著名的西方派代表、 轰动一时的《哲学书简》的作者恰达耶夫在160年前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11](P42)
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随之上升,并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向俄罗斯科学院提出了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确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идея)。副总统鲁茨科依也表示:“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罗斯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12] 欧亚主义变成了街谈巷议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异乎寻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欧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凡是有关文化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会议和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欧亚主义的。在俄罗斯科学院之下设有一个“欧亚研究中心”,莫斯科成立了“欧亚主义”出版社,“欧亚主义”杂志得以创刊。在俄国政治家和学者亚历山大·杜金的领导下,2001年“欧亚主义”全俄社会政治运动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2002年改名为“欧亚党”,并获准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另外还建有自己的网站(http://www.evrazia.org)。 著名电影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永远是欧亚国家,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道路的话,我想,这就是自己的发展道路——欧亚主义的道路。”“今天在俄国土地上,欧亚主义的伟大思想是可以实现的。”[13] 为区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侨民中兴起的欧亚主义,90年代后盛行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被冠之以“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的名称。
二、欧亚主义的历史溯源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与“新欧亚主义”之争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的历史延续,以此为出发点的两条道路实际上是公元10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摇摆不定的“路标选择”历史的延续。美国当代史学家、全球史学奠基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评论:“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14](P374)
自然地理上的俄国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促成了位于欧洲和亚洲大陆核心位置的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俄罗斯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汇合带(或称结合部)特征。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精神特点对于俄罗斯文化传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即是开拓土地和殖民的历史,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民族向整个东欧平原散布开来:从波罗的海到白海到黑海、高加索山脉、里海和乌拉尔河,甚至深入高加索,里海和乌拉尔以南、以东的地方。俄罗斯部族在政治上几乎全部联合在一个政权之下:小俄罗斯、白俄罗斯、诺沃罗西亚一个接一个地归并入大俄罗斯,组成了全俄罗斯帝国”[15](P28),成为一个地跨欧亚、幅员228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面积为174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16](P142)。
纵观10世纪以来俄国历史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即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
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蒙古鞑靼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欧化”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他所支持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方式的,但他同样支持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予其人身自由权利,但不放心的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农村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迈开步伐,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是一夫当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超级集权统治。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一条现代化新路,然而就在苏联社会主义“凯歌行进”和成就巨大的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发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仍然苦斗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西方式”与“东方式”道路的吊诡悖论之中。
俄国发展模式的摇摆导致社会的分裂。18世纪初,彼得一世大力推行欧化改革,试图以“野蛮”方式制服俄国的“野蛮”(马克思语)[17](P620)。其长远效应是推动俄国历史发展,其近期效应是促进了俄罗斯民族觉醒以及导致社会大分裂。准确地说,使俄罗斯社会分裂为相互对抗的“本土(почва)”俄罗斯和“文明(цивилизация)”俄罗斯两部分。对抗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分裂性不可避免地将选择道路问题摆在国家面前。如果选择‘本土’化道路,就意味着采取伊凡四世时代启动的东方类型道路。如果选择‘文明’化道路,就意识着拒绝基辅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接受欧洲传统。俄国几乎用了300年来解决这个难题。”⑤
18世纪80年代,持本土派立场的俄国著名学者冯维津提出了著名的“东方与西方”和“俄国与西方”的命题,他的观点是“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18](P89—92)。由此,引发俄国知识分子两个多世纪的深入思考。俄国知识阶层在19世纪30—50年代展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即是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即赫尔岑所称“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最终划分出西方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与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ъство)两大营垒。西方派主张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故步于自己的传统,俄国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三次革命洗礼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布尔什维克的执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反苏势力的溃败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再次分裂,形成了“苏维埃俄罗斯”(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和由移居国外的200余万俄罗斯人组成的“侨民俄罗斯”(Эмигрантская Россия)。⑥ 侨民知识分子仍然在思考着著名的“赫尔岑命题”, 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悲剧使欧亚主义在废墟中显露出来。20年代初形成了“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⑦ 思潮和“欧亚主义派”(Евразийцы)。 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斯拉夫主义思想,强调从俄罗斯文化传统和独特地理环境中寻找“赫尔岑命题”的答案,试图为俄国发展指出道路。
1921年,在俄侨聚居的索菲亚出版了《走向东方》(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文集,标志着欧亚主义思潮的诞生。⑧ 作者之一萨维茨基认为,“在从前在地理上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的旧大陆的土地上,它成为划分的第三个、中间的大陆——‘欧亚’,欧亚主义的名字由此而来”;“俄罗斯就其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而言,它既不是纯亚洲式的,也不是纯欧洲式的。”[19](P100) 俄罗斯命中注定要充当沟通两块大陆和两种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的角色。他在一首诗中形象地表示:“我们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种族是特殊的。我们是完整的东西方,我们是其高峰的旅行者。”[20](P146) 作者之一阿列克谢耶夫是欧亚主义国家思想的主要表述者。他考察了自古以来俄罗斯人所追求的“真理国家”的五种模式,即东正教的君主制思想、独裁思想、哥萨克自由逃民的思想、非正统教派的国家思想、约瑟夫派的国家思想。他主张从俄罗斯古代村社体制和民间谚语等民族传统中寻找借鉴,建立重在保障公民精神发展的欧亚国家。苏俄红色领袖托洛茨基也曾就此发表看法,“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2](P255)
欧亚主义者强烈反对欧化,认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亦称“欧亚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欧亚世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是非欧非亚的欧亚人,其文化也是非欧非亚的欧亚文化;俄罗斯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寻找和坚持自己的道路。作家特鲁别茨科依公爵强调珍视和重建俄罗斯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作坚决斗争,以对抗强势的罗马—日耳曼文化的侵略。
欧亚主义者非常关注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对新经济政策持谨慎的合作态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完全不适合俄国的国情,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苏维埃政权已改弦更张,表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死了”[22](P15),“欧亚主义要竭尽全力渗透这一新的体制, 假借新政权之手建立自己的新国家”[23](P177)。西方的道路走不通,俄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欧亚主义道路。而且欧亚主义派与布尔什维克在一些思想上不谋而合,如强调思想意识在国家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主张联邦主义原则,主张不屈服西方的压力走自己的道路等。
到20年代末,欧亚派试图变理论为实践,建立欧亚党,但这个尝试没有成功。30年代中叶,欧亚派逐渐发生分裂,这个阵营分化成两部分:一部分支持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国家建设方案,另一部分反对。1937年,欧亚派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欧亚主义思想并没有因欧亚派的消亡而消失,它不仅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而且还渗透到了苏联国内,列夫·古米廖夫(1912—1992)就是苏联国内最为著名的欧亚主义者之一,他表示:“当别人称我欧亚人时,因为某些原因我不拒绝这个称呼。第一,这是强大历史潮流,如果我被吸引到这里,它将给我以荣誉。第二,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个流派的著作。第三,我实际上同意欧亚主义者基本的历史方法论的结论。”他的结论是如果俄罗斯能够被拯救的话,那么只有通过欧亚主义的道路[24]。
三、欧亚主义: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
在苏联时代,尽管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基本绝迹,但是从欧亚主义角度思考治国安邦的方略却成为苏联领导人的一种出发点。美国学者米兰·霍纳认为欧亚主义无意识地帮助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成为苏维埃思想的宣传者[25](P57—63)。从列宁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从古老的地缘政治观念考虑苏联安全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在1946年说过:“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对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26](P484) 以此为出发点, 苏联在解放东欧后,帮助各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并且将其发展为冷战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勃列日涅夫则以“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来维持这个大家庭的存在。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评价:“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27](P119—120)
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许多知识分子试图从俄国文化传统、农业国家、农民村社等典型的欧亚主义视角解开十月革命性质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之谜。他们普遍认为,尽管列宁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引入俄国,指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从性质上讲,十月革命仅仅是俄国特色的革命,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夫认为:“村社这一古老的传统是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在我看来,它是1917年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这种传统对俄国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深刻得多,它不仅影响到民族传统,而且影响到道德、政治文化和一切智力活动的特点。”“几十年来,苏联史学一直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1917年吸引了大多数俄国人,因此十月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然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不可能在以农民为主的、非西方化的俄国传播开来”,因此“与其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不如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列宁主义的产物。”[28]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知识分子革命,是一场基于俄国文化传统的政治革命,是一次试图在西方道路和东方道路中寻找第三条道路——欧亚主义道路的政治实验。
新欧亚主义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持有“较友善”的批评意见,但是对当前进行的“全盘西化”式改革则持彻底否定态度。就是在俄罗斯政府和全社会急于“重返欧洲”和“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思潮占绝对支配地位时,一些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学者对此展开了批判,揭露当政的总理盖达尔、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所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理论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不切实际,并且预言“西方化道路”必然失败。当代欧亚主义学者、俄侨哲学家留克斯在1992年底批评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同时也点出了新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新俄罗斯的西方主义者和他们19世纪的前辈一样,把俄罗斯看成是落后的东方国家。认为西方模式是俄罗斯或早或晚必须接受的模式。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派的观点是完全的乌托邦,他们认为俄罗斯永远不会变成欧洲国家,因为它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结构与西方大相径庭,照搬西方模式终究要失败的。”[28] 哲学家巴纳林在1993 年表示:“现在当权的是西方派人士,他们认为民主的需要高于俄罗斯的需要,而且民主的胜利应该是以牺牲俄罗斯需要为前提的。他们把人民视为民主道路上的障碍,是保守力量。这些人是要把他们主张的西方文化强加在俄罗斯头上。这必然导致人民和知识分子、人民和政权、帝国霸权主义和地区自治主义之间的对立。”[29](P156—157)
新俄罗斯继承了沙皇俄国和苏联大部分的政治版图,也继承了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也不得不继承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下的欧亚主义的诱惑和困惑。1993年后,较为系统的新欧亚主义思潮已经形成,并且上升为俄罗斯社会和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思潮。巴纳林认为欧亚主义就是“在生活和建设的统一原则下联合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的、非西方的特殊的文明类型”,欧亚主义“是特殊的文明共同体思想,它创造性地吸收和反映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的一切积极因素”[30]。俄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也主张俄罗斯要避免成为“世界又一轮重新瓜分的中心”,就必须牢牢掌握“欧亚大陆深处跳动的地缘政治的世界心脏”,“控制整个地缘政治利益范围(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成员国和阿富汗)”[31](P187—188)。 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杜金总结了新老欧亚主义的基本点和相互联系,他认为:“这种新欧亚主义建立在萨维茨基、维尔纳茨基和特鲁别茨科依公爵,甚至还包括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家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思想基础之上,历史上的欧亚主义者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欧亚主义在现代形势的迫切和更加积极的作用。帝国大陆范围的民族理论大纲中同时将自由主义西方派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俄罗斯被看成是地缘政治‘大版图’的中地轴线,它的民族使命等同于帝国的构建。在社会政治条件下,这种思想一致倾向于欧亚社会主义(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циализм),认为自由经济是大西洋阵营的特殊标志。俄国历史的苏维埃时期被看成是路标转换后的前景,是作为传统的、俄罗斯的、民族的追求全球扩张和旨在反大西洋主义的欧亚主义的普世精神的现代化模式。由此表现了新欧亚主义这种理论的‘亲共产主义’趋势。”[9](P157) 于是,在“赫尔岑命题”和欧亚主义观点上,旧俄罗斯、苏联和新俄罗斯实现了历史性的相遇。然而,从欧亚主义视角来观察俄国、苏联和新俄罗斯复兴道路,我们能够发现其共性所在: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的历史命运之外,还必须注意三者间的差异性和歧路。
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一般都极力赞美彼得一世改革前莫斯科罗斯时代的淳朴民风和田园诗般生活,甚至责难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32]。而新欧亚主义者既坚持俄罗斯文化传统,同时又强调尊重现代文明,他们认为在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里,只有俄罗斯才能将“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巴纳林认为:“在新时期里,处于中心位置的不是经济人,而是把精神、文化和生态需要摆在第一位的后经济人。向这一时期转化的保证,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后经济人与还没有西方化的前经济人的联盟。……我们的全部精神传统,正是当今时期的迫切需要,导致前经济人与后经济人的相遇最早发生在俄罗斯,而俄罗斯因此也就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成为全球转折的倡导者之一。”[33](P390)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但工业文明与技术文明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原因在于西方文化本身无法推进现代化继续发展,以及进入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化阶段。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对现代文明的亲和性。因为,“俄罗斯社会意识中迄今还留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传统价值,尽管它不适合工业文明的要求,但更适合后工业文明的要求。从而使俄罗斯社会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为容易。俄罗斯摆脱现有的历史处境的出路在于实现晚发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俄罗斯踏上一条无与伦比的新路。”[34]
新欧亚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相比较大的区别之处。斯拉夫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在较多情况下扮演了政府的反对派的角色,而新欧亚主义者则强调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维护当前政府的权威。他们在沙皇政府教育大臣乌瓦罗夫1832年提出的“官方国民性”(Официалъ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ъ)三原则(“东正教、 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感,将其发展成为“新国民性”三原则(“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 “人民主权”(Народны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和“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изм),这种立场很自然地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普京执政后,延续了欧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他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这一点。”[5] 他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把实用主义、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政府的主要任务,认为国内目标高于国际目标。在内政方面,普京政府主张实行“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并根据苏联70年经济建设和俄罗斯90年代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изм)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既没有继续叶利钦时期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也没有回到原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轨道,而是强调在不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下逐步改革,强调遵循温和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由国家调控的自由社会经济体系。在外交方面,普京把“东西方并重”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各个层次的平衡外交。把俄罗斯定位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集中力量关注自身周边地区的安全,不再追求与自身国力不相适应的、不切实际的大国地位,近期目标在于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一个巨大的“稳定的弧形(圆形)安全带”。2002年4月,普京又宣布俄罗斯的目标是融入欧洲主流经济。
作为在野反对派的俄联邦共产党支持欧亚主义,并且把“国家主义”(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ъ)写入1995年1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中,作为俄共所倡导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份纲领宣布:“俄共必须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完整,恢复革新的苏维埃各族人民的联盟,确保俄罗斯民族的统一”,“俄共提出的任务是加强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保护俄罗斯的国家民族利益和今天的反对殖民奴役制度以及反对反革命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人民政权形式有机结合起来。”[35](P30) 该党纲宣布:“作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争取各族人民友谊的政党,俄共将争取保持国家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民族和睦。”[35](P32)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进化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给予该民族各方面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因为民族文化传统一经形成,便同时被赋予顽强的再生性,其影响将在该民族的进化过程中一再地发挥出来,一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在适宜的时机还会以某种方式迁移和滋生,这即是文化传统强烈的滞后作用。透过文化传统的历史空隙,一叶可以知百年俄国春秋,可以知苏联兴衰成败,一孔可以窥俄罗斯发展取向。
娴熟欧洲历史和欧洲政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6](P585) 从前天的俄国历史、昨天的苏联历史、今天的俄罗斯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文化传统,包括欧亚主义传统的作用,它如影随形般地影响着俄罗斯(包括苏联)的社会进程,并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明天的俄罗斯发展取向。最后,还应该提到自称“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列夫·古米廖夫,他生活在苏联时代,既不属于欧亚主义者,也不是新欧亚主义,但正是由于他的思想活动才完成了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历史会通。他在去世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知道一点,并愿意悄悄地告诉您,俄罗斯如果想要得救的话,就必须成为欧亚大陆强国,事实上,只有欧亚主义能够救俄罗斯。”[37](P31) 这句话,不正是我们理解欧亚主义和俄罗斯复兴的重要的着眼点吗?
注释:
① 若按原书名翻译为《捕获瞬间:美国在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中面临的挑战》(Seize the Moment: America's Challenge in a One Superpower World. Simon & Schuster Inc.1991),意义则更为准确和深远。
② 17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制订了第一个欧洲联邦计划。18世纪以来,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神父、启蒙思想家卢梭、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德国哲学家康德都先后提出过“欧洲联邦”设想。1923年,奥地利贵族理查德·考登霍夫—加勒基发表《泛欧洲》一书,并发起组织“泛欧联盟”, 以此反对苏维埃俄国。1929年9月,法国总理兼外长白里安在国际联盟提出“欧洲联邦”建议,同年5月法国政府向欧洲26国政府提交“关于组织欧洲联盟体系”备忘录(白里安计划)。1947年,已下野的丘吉尔在“欧洲统一大会”上再次向各国发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呼吁。
③ 即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提出的问题:俄国向何处去,东方还是西方?因此称“赫尔岑命题”(проблема Герцена)。
④ 即斯堪的那维亚(Сканденавия)加上斯拉夫(Славяне)。
⑤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在改革前的农村和新俄罗斯中产生的不是我国历史两个相邻的时期,而是两个相互敌对的风格和生活倾向,这种风格和倾向导致俄国社会的分化,并导致彼此间斗争,取代了他们本应和睦地与自己的共同的生活困难处境的斗争。”参见Семенникова Л.И.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Курсив”1996.C.156.
⑥ 关于俄国侨民人数、政治态度和社会团体的内容, 参见张建华等《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历史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249—269页。
⑦ “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是欧洲(Европа)和亚洲(Азия)两个词的合成词。
⑧ 文集收录比钦里的《旧阶层历史中的东方与西方》,特鲁别茨科依的《论真实的和虚假的民族主义》、《俄罗斯问题》、《论土兰因素和俄国文化》、《我们和他人》、《普遍欧亚民族主义》,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两个世界》、《草原和定居》、《主人和经济》,阿列克谢耶夫的《欧亚派与国家》和卡尔萨文的《政治基础》等12篇文章。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8期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06年2期第32~38页
【作者简介】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关 键 词】欧亚主义/俄罗斯/苏联时代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冷战结束之际在他的新著《透视新世界》① 中写道:“过去的日子,世界发生了海滩滚滑车式的急转突变,从突然看到希望到幻想破灭,接着又是欣喜不已。”[1](P4)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留给欧洲人的记忆是痛苦和深刻的,欧洲人对“欧洲复兴”和“欧洲重建”的期盼心情是积极的,但又是复杂的。② 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将欧洲一体化推向新阶段。2003年5月,素有学怨的德、 法两大思想家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联袂著文《论欧洲的复兴》,向欧洲各国发出在“欧洲认同”(Europaeische Identitaet)基础上“超越欧洲中心主义”,“重新定位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的呼吁[2]。
俄罗斯复兴与欧洲复兴息息相关,但两者之间却充满了吊诡。就在西欧政治家和学者热切期盼欧洲复兴之际,在欧洲东端的俄罗斯(苏联)却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着孤寡之形象。不论冷战前夜丘吉尔的“欧洲合众国”梦想,还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核心欧洲”(Kerneuropa)构想,均不包括昨天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因为在欧美政治家和学者眼中,苏联完全是异类的“红色帝国”或“邪恶帝国”,今日的俄罗斯也不幸变成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特例,成为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3](P22)。困扰俄罗斯数个世纪的“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сфинкс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再现了。③ 与此同时,一个似曾相识的名词——“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开始频繁跃然新闻媒体之上和学者笔下,甚至是政治家谈话中。“欧亚主义”能不能复兴俄罗斯?这是一个让俄罗斯思想文化界既兴奋又迷茫的问题,它一下子把俄国—苏联—俄罗斯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吸引政治家和学者们思考。
一、复兴危机与问题的提出
自1991年底起,刚刚获得独立的俄罗斯即开始了它的“国家复兴”进程。它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它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4](P8—9)。毫无疑问,在告别了社会主义之后,俄罗斯选择了“纯粹”的西方式道路,即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经济上的纯市场经济、外交上的向西方一边倒、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俄罗斯复兴的核心即是“重返欧洲”,搭上“欧洲复兴的快车”,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叶利钦语)[5]。但是这个全方位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异常波折和时艰命蹇。
在政治转型方面:1990年10月12日,俄罗斯宪法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宪法草案,宣布在俄罗斯建立三权分立式的联邦共和国,规定“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俄罗斯议会、总统、宪法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它们根据分权原则独立地履行自己的职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总统是联邦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然而,“超级总统”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府”“院”权力之争旷日持久愈加严重,最终酿成1993年10月两者直接的武装对抗。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是当年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中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自由民主党”地位陡升,1995年12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大选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影响突进,震荡了脆弱的政党政治。
在经济复兴方面:1992年初开始的休克疗法试图以一步到位的形式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实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战略。但实施结果,使政府对市场失去了控制,投机资本肆虐,市场秩序极端混乱,生产急剧下滑,物价暴涨,政府财政赤字剧升,货币信贷体系濒临崩溃。从1992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连续四年居高不下,超过四位数字,1992年高达2610%,此后开始逐年下降,1993年为940%,1994年为320%,1995年仍然为131%。据俄经济学家统计, 1995年与1990年相比,消费品价格上涨了1700多倍[6](P374)。恶性通货膨胀大大阻碍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价格的飞涨使市场机制远远不能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力量,高通货膨胀率则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倾向,打击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助长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使整个经济生活陷入混乱之中。1993年8 月政府颁布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俄罗斯经济1993—1995年工作计划》,宣布调整政策,叶利钦也在1995年宣布:“今后不再实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5]
在外交政策方面:初期俄罗斯奉行了对西方和美国“一边倒”的做法。1992年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俄罗斯不仅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成是伙伴,而且看成是盟国。”[5] 外长科济列夫宣布俄罗斯将奉行与西方“完全伙伴化的方针,与西方一体化”。然而一年多的外交实践使俄罗斯领导人明白,以上的想法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叶利钦在1993年初访问韩国时提出了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外交政策。同年4 月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新构想》中强调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别,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进一步强化大国外交意识,加速发展全方位外交局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与前苏联拥有传统关系国家的关系,建立西方的莫斯科—柏林—巴黎,东方的莫斯科—新德里—北京轴心关系。1995年后,北约东扩加剧俄美矛盾。叶利钦总统警告,“如果北约东扩,一个与之军事对抗的军事联盟可能再次出现”,“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战争状态。”[5] 这表明,俄罗斯“重返欧洲”的进程严重受阻。
在国家复兴和社会转型全面受挫之后,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反思。“俄罗斯路标在何方?”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ЕвропеизмАтлатизм)在1993年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许多学者试图从文化、宗教、语言甚至族缘、血缘方面寻找俄罗斯与西欧的共同点。被誉为俄罗斯国学大师的利哈乔夫院士认为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东方国家,“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那维亚起决定性的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那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7](P21),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идосавия)。④ 曾担任过政府总理的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所长盖达尔认为,“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俄罗斯是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接触西方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走上西方道路的国家,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几乎跟上的状态中”[8](PP.52—53)。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强调:“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和文明的论点看,俄罗斯人是欧洲民族。”俄罗斯与西方“将尽一切努力来倡导共同的民主价值观”[5]。俄驻美大使卢金干脆称“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思潮”为“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国际主义”,以区别于苏联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9](P409)。
然而,几年来西方模式实践的失败宣告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道路的破产,也使这种思潮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思想文化界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当代哲学家梅茹耶夫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谓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10] 值得思索的是,19世纪著名的西方派代表、 轰动一时的《哲学书简》的作者恰达耶夫在160年前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11](P42)
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随之上升,并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向俄罗斯科学院提出了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确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идея)。副总统鲁茨科依也表示:“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罗斯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12] 欧亚主义变成了街谈巷议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异乎寻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欧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凡是有关文化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会议和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欧亚主义的。在俄罗斯科学院之下设有一个“欧亚研究中心”,莫斯科成立了“欧亚主义”出版社,“欧亚主义”杂志得以创刊。在俄国政治家和学者亚历山大·杜金的领导下,2001年“欧亚主义”全俄社会政治运动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2002年改名为“欧亚党”,并获准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另外还建有自己的网站(http://www.evrazia.org)。 著名电影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永远是欧亚国家,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道路的话,我想,这就是自己的发展道路——欧亚主义的道路。”“今天在俄国土地上,欧亚主义的伟大思想是可以实现的。”[13] 为区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侨民中兴起的欧亚主义,90年代后盛行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被冠之以“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的名称。
二、欧亚主义的历史溯源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与“新欧亚主义”之争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的历史延续,以此为出发点的两条道路实际上是公元10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摇摆不定的“路标选择”历史的延续。美国当代史学家、全球史学奠基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评论:“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14](P374)
自然地理上的俄国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促成了位于欧洲和亚洲大陆核心位置的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俄罗斯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汇合带(或称结合部)特征。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精神特点对于俄罗斯文化传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即是开拓土地和殖民的历史,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民族向整个东欧平原散布开来:从波罗的海到白海到黑海、高加索山脉、里海和乌拉尔河,甚至深入高加索,里海和乌拉尔以南、以东的地方。俄罗斯部族在政治上几乎全部联合在一个政权之下:小俄罗斯、白俄罗斯、诺沃罗西亚一个接一个地归并入大俄罗斯,组成了全俄罗斯帝国”[15](P28),成为一个地跨欧亚、幅员228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面积为174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16](P142)。
纵观10世纪以来俄国历史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即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
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蒙古鞑靼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欧化”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他所支持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方式的,但他同样支持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予其人身自由权利,但不放心的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农村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迈开步伐,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是一夫当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超级集权统治。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一条现代化新路,然而就在苏联社会主义“凯歌行进”和成就巨大的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发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仍然苦斗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西方式”与“东方式”道路的吊诡悖论之中。
俄国发展模式的摇摆导致社会的分裂。18世纪初,彼得一世大力推行欧化改革,试图以“野蛮”方式制服俄国的“野蛮”(马克思语)[17](P620)。其长远效应是推动俄国历史发展,其近期效应是促进了俄罗斯民族觉醒以及导致社会大分裂。准确地说,使俄罗斯社会分裂为相互对抗的“本土(почва)”俄罗斯和“文明(цивилизация)”俄罗斯两部分。对抗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分裂性不可避免地将选择道路问题摆在国家面前。如果选择‘本土’化道路,就意味着采取伊凡四世时代启动的东方类型道路。如果选择‘文明’化道路,就意识着拒绝基辅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接受欧洲传统。俄国几乎用了300年来解决这个难题。”⑤
18世纪80年代,持本土派立场的俄国著名学者冯维津提出了著名的“东方与西方”和“俄国与西方”的命题,他的观点是“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18](P89—92)。由此,引发俄国知识分子两个多世纪的深入思考。俄国知识阶层在19世纪30—50年代展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即是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即赫尔岑所称“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最终划分出西方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与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ъство)两大营垒。西方派主张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故步于自己的传统,俄国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三次革命洗礼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布尔什维克的执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反苏势力的溃败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再次分裂,形成了“苏维埃俄罗斯”(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和由移居国外的200余万俄罗斯人组成的“侨民俄罗斯”(Эмигрантская Россия)。⑥ 侨民知识分子仍然在思考着著名的“赫尔岑命题”, 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悲剧使欧亚主义在废墟中显露出来。20年代初形成了“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⑦ 思潮和“欧亚主义派”(Евразийцы)。 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斯拉夫主义思想,强调从俄罗斯文化传统和独特地理环境中寻找“赫尔岑命题”的答案,试图为俄国发展指出道路。
1921年,在俄侨聚居的索菲亚出版了《走向东方》(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文集,标志着欧亚主义思潮的诞生。⑧ 作者之一萨维茨基认为,“在从前在地理上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的旧大陆的土地上,它成为划分的第三个、中间的大陆——‘欧亚’,欧亚主义的名字由此而来”;“俄罗斯就其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而言,它既不是纯亚洲式的,也不是纯欧洲式的。”[19](P100) 俄罗斯命中注定要充当沟通两块大陆和两种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的角色。他在一首诗中形象地表示:“我们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种族是特殊的。我们是完整的东西方,我们是其高峰的旅行者。”[20](P146) 作者之一阿列克谢耶夫是欧亚主义国家思想的主要表述者。他考察了自古以来俄罗斯人所追求的“真理国家”的五种模式,即东正教的君主制思想、独裁思想、哥萨克自由逃民的思想、非正统教派的国家思想、约瑟夫派的国家思想。他主张从俄罗斯古代村社体制和民间谚语等民族传统中寻找借鉴,建立重在保障公民精神发展的欧亚国家。苏俄红色领袖托洛茨基也曾就此发表看法,“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2](P255)
欧亚主义者强烈反对欧化,认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亦称“欧亚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欧亚世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是非欧非亚的欧亚人,其文化也是非欧非亚的欧亚文化;俄罗斯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寻找和坚持自己的道路。作家特鲁别茨科依公爵强调珍视和重建俄罗斯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作坚决斗争,以对抗强势的罗马—日耳曼文化的侵略。
欧亚主义者非常关注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对新经济政策持谨慎的合作态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完全不适合俄国的国情,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苏维埃政权已改弦更张,表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死了”[22](P15),“欧亚主义要竭尽全力渗透这一新的体制, 假借新政权之手建立自己的新国家”[23](P177)。西方的道路走不通,俄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欧亚主义道路。而且欧亚主义派与布尔什维克在一些思想上不谋而合,如强调思想意识在国家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主张联邦主义原则,主张不屈服西方的压力走自己的道路等。
到20年代末,欧亚派试图变理论为实践,建立欧亚党,但这个尝试没有成功。30年代中叶,欧亚派逐渐发生分裂,这个阵营分化成两部分:一部分支持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国家建设方案,另一部分反对。1937年,欧亚派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欧亚主义思想并没有因欧亚派的消亡而消失,它不仅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而且还渗透到了苏联国内,列夫·古米廖夫(1912—1992)就是苏联国内最为著名的欧亚主义者之一,他表示:“当别人称我欧亚人时,因为某些原因我不拒绝这个称呼。第一,这是强大历史潮流,如果我被吸引到这里,它将给我以荣誉。第二,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个流派的著作。第三,我实际上同意欧亚主义者基本的历史方法论的结论。”他的结论是如果俄罗斯能够被拯救的话,那么只有通过欧亚主义的道路[24]。
三、欧亚主义: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
在苏联时代,尽管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基本绝迹,但是从欧亚主义角度思考治国安邦的方略却成为苏联领导人的一种出发点。美国学者米兰·霍纳认为欧亚主义无意识地帮助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成为苏维埃思想的宣传者[25](P57—63)。从列宁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从古老的地缘政治观念考虑苏联安全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在1946年说过:“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对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26](P484) 以此为出发点, 苏联在解放东欧后,帮助各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并且将其发展为冷战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勃列日涅夫则以“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来维持这个大家庭的存在。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评价:“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27](P119—120)
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许多知识分子试图从俄国文化传统、农业国家、农民村社等典型的欧亚主义视角解开十月革命性质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之谜。他们普遍认为,尽管列宁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引入俄国,指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从性质上讲,十月革命仅仅是俄国特色的革命,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夫认为:“村社这一古老的传统是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在我看来,它是1917年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这种传统对俄国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深刻得多,它不仅影响到民族传统,而且影响到道德、政治文化和一切智力活动的特点。”“几十年来,苏联史学一直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1917年吸引了大多数俄国人,因此十月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然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不可能在以农民为主的、非西方化的俄国传播开来”,因此“与其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不如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列宁主义的产物。”[28]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知识分子革命,是一场基于俄国文化传统的政治革命,是一次试图在西方道路和东方道路中寻找第三条道路——欧亚主义道路的政治实验。
新欧亚主义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持有“较友善”的批评意见,但是对当前进行的“全盘西化”式改革则持彻底否定态度。就是在俄罗斯政府和全社会急于“重返欧洲”和“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思潮占绝对支配地位时,一些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学者对此展开了批判,揭露当政的总理盖达尔、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所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理论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不切实际,并且预言“西方化道路”必然失败。当代欧亚主义学者、俄侨哲学家留克斯在1992年底批评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同时也点出了新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新俄罗斯的西方主义者和他们19世纪的前辈一样,把俄罗斯看成是落后的东方国家。认为西方模式是俄罗斯或早或晚必须接受的模式。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派的观点是完全的乌托邦,他们认为俄罗斯永远不会变成欧洲国家,因为它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结构与西方大相径庭,照搬西方模式终究要失败的。”[28] 哲学家巴纳林在1993 年表示:“现在当权的是西方派人士,他们认为民主的需要高于俄罗斯的需要,而且民主的胜利应该是以牺牲俄罗斯需要为前提的。他们把人民视为民主道路上的障碍,是保守力量。这些人是要把他们主张的西方文化强加在俄罗斯头上。这必然导致人民和知识分子、人民和政权、帝国霸权主义和地区自治主义之间的对立。”[29](P156—157)
新俄罗斯继承了沙皇俄国和苏联大部分的政治版图,也继承了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也不得不继承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下的欧亚主义的诱惑和困惑。1993年后,较为系统的新欧亚主义思潮已经形成,并且上升为俄罗斯社会和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思潮。巴纳林认为欧亚主义就是“在生活和建设的统一原则下联合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的、非西方的特殊的文明类型”,欧亚主义“是特殊的文明共同体思想,它创造性地吸收和反映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的一切积极因素”[30]。俄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也主张俄罗斯要避免成为“世界又一轮重新瓜分的中心”,就必须牢牢掌握“欧亚大陆深处跳动的地缘政治的世界心脏”,“控制整个地缘政治利益范围(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成员国和阿富汗)”[31](P187—188)。 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杜金总结了新老欧亚主义的基本点和相互联系,他认为:“这种新欧亚主义建立在萨维茨基、维尔纳茨基和特鲁别茨科依公爵,甚至还包括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家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思想基础之上,历史上的欧亚主义者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欧亚主义在现代形势的迫切和更加积极的作用。帝国大陆范围的民族理论大纲中同时将自由主义西方派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俄罗斯被看成是地缘政治‘大版图’的中地轴线,它的民族使命等同于帝国的构建。在社会政治条件下,这种思想一致倾向于欧亚社会主义(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циализм),认为自由经济是大西洋阵营的特殊标志。俄国历史的苏维埃时期被看成是路标转换后的前景,是作为传统的、俄罗斯的、民族的追求全球扩张和旨在反大西洋主义的欧亚主义的普世精神的现代化模式。由此表现了新欧亚主义这种理论的‘亲共产主义’趋势。”[9](P157) 于是,在“赫尔岑命题”和欧亚主义观点上,旧俄罗斯、苏联和新俄罗斯实现了历史性的相遇。然而,从欧亚主义视角来观察俄国、苏联和新俄罗斯复兴道路,我们能够发现其共性所在: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的历史命运之外,还必须注意三者间的差异性和歧路。
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一般都极力赞美彼得一世改革前莫斯科罗斯时代的淳朴民风和田园诗般生活,甚至责难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32]。而新欧亚主义者既坚持俄罗斯文化传统,同时又强调尊重现代文明,他们认为在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里,只有俄罗斯才能将“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巴纳林认为:“在新时期里,处于中心位置的不是经济人,而是把精神、文化和生态需要摆在第一位的后经济人。向这一时期转化的保证,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后经济人与还没有西方化的前经济人的联盟。……我们的全部精神传统,正是当今时期的迫切需要,导致前经济人与后经济人的相遇最早发生在俄罗斯,而俄罗斯因此也就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成为全球转折的倡导者之一。”[33](P390)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但工业文明与技术文明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原因在于西方文化本身无法推进现代化继续发展,以及进入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化阶段。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对现代文明的亲和性。因为,“俄罗斯社会意识中迄今还留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传统价值,尽管它不适合工业文明的要求,但更适合后工业文明的要求。从而使俄罗斯社会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为容易。俄罗斯摆脱现有的历史处境的出路在于实现晚发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俄罗斯踏上一条无与伦比的新路。”[34]
新欧亚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相比较大的区别之处。斯拉夫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在较多情况下扮演了政府的反对派的角色,而新欧亚主义者则强调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维护当前政府的权威。他们在沙皇政府教育大臣乌瓦罗夫1832年提出的“官方国民性”(Официалъ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ъ)三原则(“东正教、 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感,将其发展成为“新国民性”三原则(“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 “人民主权”(Народны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和“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изм),这种立场很自然地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普京执政后,延续了欧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他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这一点。”[5] 他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把实用主义、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政府的主要任务,认为国内目标高于国际目标。在内政方面,普京政府主张实行“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并根据苏联70年经济建设和俄罗斯90年代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изм)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既没有继续叶利钦时期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也没有回到原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轨道,而是强调在不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下逐步改革,强调遵循温和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由国家调控的自由社会经济体系。在外交方面,普京把“东西方并重”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各个层次的平衡外交。把俄罗斯定位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集中力量关注自身周边地区的安全,不再追求与自身国力不相适应的、不切实际的大国地位,近期目标在于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一个巨大的“稳定的弧形(圆形)安全带”。2002年4月,普京又宣布俄罗斯的目标是融入欧洲主流经济。
作为在野反对派的俄联邦共产党支持欧亚主义,并且把“国家主义”(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ъ)写入1995年1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中,作为俄共所倡导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份纲领宣布:“俄共必须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完整,恢复革新的苏维埃各族人民的联盟,确保俄罗斯民族的统一”,“俄共提出的任务是加强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保护俄罗斯的国家民族利益和今天的反对殖民奴役制度以及反对反革命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人民政权形式有机结合起来。”[35](P30) 该党纲宣布:“作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争取各族人民友谊的政党,俄共将争取保持国家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民族和睦。”[35](P32)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进化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给予该民族各方面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因为民族文化传统一经形成,便同时被赋予顽强的再生性,其影响将在该民族的进化过程中一再地发挥出来,一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在适宜的时机还会以某种方式迁移和滋生,这即是文化传统强烈的滞后作用。透过文化传统的历史空隙,一叶可以知百年俄国春秋,可以知苏联兴衰成败,一孔可以窥俄罗斯发展取向。
娴熟欧洲历史和欧洲政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6](P585) 从前天的俄国历史、昨天的苏联历史、今天的俄罗斯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文化传统,包括欧亚主义传统的作用,它如影随形般地影响着俄罗斯(包括苏联)的社会进程,并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明天的俄罗斯发展取向。最后,还应该提到自称“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列夫·古米廖夫,他生活在苏联时代,既不属于欧亚主义者,也不是新欧亚主义,但正是由于他的思想活动才完成了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历史会通。他在去世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知道一点,并愿意悄悄地告诉您,俄罗斯如果想要得救的话,就必须成为欧亚大陆强国,事实上,只有欧亚主义能够救俄罗斯。”[37](P31) 这句话,不正是我们理解欧亚主义和俄罗斯复兴的重要的着眼点吗?
注释:
① 若按原书名翻译为《捕获瞬间:美国在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中面临的挑战》(Seize the Moment: America's Challenge in a One Superpower World. Simon & Schuster Inc.1991),意义则更为准确和深远。
② 17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制订了第一个欧洲联邦计划。18世纪以来,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神父、启蒙思想家卢梭、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德国哲学家康德都先后提出过“欧洲联邦”设想。1923年,奥地利贵族理查德·考登霍夫—加勒基发表《泛欧洲》一书,并发起组织“泛欧联盟”, 以此反对苏维埃俄国。1929年9月,法国总理兼外长白里安在国际联盟提出“欧洲联邦”建议,同年5月法国政府向欧洲26国政府提交“关于组织欧洲联盟体系”备忘录(白里安计划)。1947年,已下野的丘吉尔在“欧洲统一大会”上再次向各国发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呼吁。
③ 即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提出的问题:俄国向何处去,东方还是西方?因此称“赫尔岑命题”(проблема Герцена)。
④ 即斯堪的那维亚(Сканденавия)加上斯拉夫(Славяне)。
⑤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在改革前的农村和新俄罗斯中产生的不是我国历史两个相邻的时期,而是两个相互敌对的风格和生活倾向,这种风格和倾向导致俄国社会的分化,并导致彼此间斗争,取代了他们本应和睦地与自己的共同的生活困难处境的斗争。”参见Семенникова Л.И.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Курсив”1996.C.156.
⑥ 关于俄国侨民人数、政治态度和社会团体的内容, 参见张建华等《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历史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249—269页。
⑦ “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是欧洲(Европа)和亚洲(Азия)两个词的合成词。
⑧ 文集收录比钦里的《旧阶层历史中的东方与西方》,特鲁别茨科依的《论真实的和虚假的民族主义》、《俄罗斯问题》、《论土兰因素和俄国文化》、《我们和他人》、《普遍欧亚民族主义》,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两个世界》、《草原和定居》、《主人和经济》,阿列克谢耶夫的《欧亚派与国家》和卡尔萨文的《政治基础》等12篇文章。

|
 [M].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Евразийство”,1995.
[M].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Евразийство”,1995.
 [M].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Арксогея”,1997.
[M].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Арксогея”,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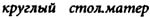 [J].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6,(6).
[J].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6,(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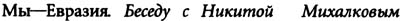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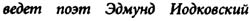 [J].Континент,1992,(70).
[J].Континент,199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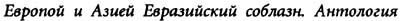 [C].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Наука”, 1993.
[C].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Наука”, 199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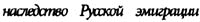 1917—1940[C].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Наука”,1994.
1917—1940[C].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Наука”,199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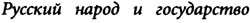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Аграф”,2000.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Аграф”,2000. [J]. Нашсовременик, 1991,(1);ГУМИЛЕВ Л.Зам еmкu
[J]. Нашсовременик, 1991,(1);ГУМИЛЕВ Л.Зам еmкu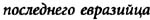 [J].Наше наследне,1991,(3).
[J].Наше наследне,1991,(3).
 [J].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ъ,1992,(15).
[J].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ъ,1992,(1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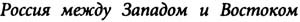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Московск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Фонд”,1993.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Московск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Фонд”,199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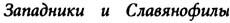 [J].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ъ,1993,(3).
[J].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ъ,19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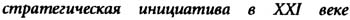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Логос”,1998.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Логос”,199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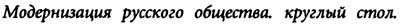 mamep[J].Вестник Росс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и,1993,(3).
mamep[J].Вестник Росс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и,1993,(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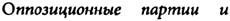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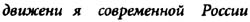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Информпечатъ”,1998.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Информпечатъ”,1998.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Экопрос”,1993.^
[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Экопрос”,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