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小川关治郎和《一个军法务官日记》
程兆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4年01期第92~105页
【作者简介】程兆奇,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关 键 词】小川关治郎日记/第十军/日军军风纪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1-0092-14
日本战败后和东京审判前两次焚毁大量文书档案,给复原相关历史带来了困难。这不 仅是致力于究明战时日军暴行的日本学者的感叹,持否定日军暴行的论者也如是观。如 持温和否定观点的松本健一(丽泽大学教授)说:因为尚存的“关于日本军南京战役的正 式记录太少,使得蹈袭中国主张——没有具体统计和资料支撑的三十万人说——的洞先 生(指洞富雄,已故日本大屠杀派第一人——引者)的二十万人说得以登场和独步。”( 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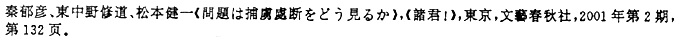 )。这也是本人近年为回应日本虚构派而搜寻日方文献时的突出体会 。所以去年末去东京访书,当看到出版已两年的日军第十军(攻占南京和江南的主力部 队之一)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时,不仅意外,也颇悔自己搜寻不细(因日记出版后 曾多次去找书)。
)。这也是本人近年为回应日本虚构派而搜寻日方文献时的突出体会 。所以去年末去东京访书,当看到出版已两年的日军第十军(攻占南京和江南的主力部 队之一)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时,不仅意外,也颇悔自己搜寻不细(因日记出版后 曾多次去找书)。
小川日记珍藏到今日,长期不为人所知,连与他晚年一同生活的女儿都感到“吃惊” 、“完全没有记忆”(注: )。日记起自1937年10月12日“第七号军(即第 十军)动员令下达”,讫于1938年2月21日小川随中支那方面军(注:国内多将中支那方 面军译为“华中方面军”,因考虑到日本所称“中支”与我国的“华中”无论在传统所 指自然地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指行政区划上都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而中支那 方面军的活动范围也始终未逾今天通常所指的华东以外,所以本文一仍日本旧称。国内 译名避免“支那”是因为以为“支那”是蔑称,如《“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中译本 第一页第一条注释称:“支那为日本对战前中国的蔑称。《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仍 沿用了这一称呼,表明了笔者的反华立场。为了客观反映该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译者 未加任何改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原著无“大”字,“南京屠杀”加引号 ,因为日本虚构派不承认“屠杀”,故称屠杀必加引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 “内部发行”版,第1页。)日本今天仍坚持以“支那”称中国者,一定是右翼,但援用 历史名称,如“中支那方面军”时,则不论左、右翼都不加改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 将一行坐船离沪,其中11月7日小川在金山登陆后所记均为中国见闻,对认识第十军在 华数月的活动,尤其是日军“军风纪”,有重要价值。因为小川为当时日军最资深的军 法官,他的个人经历与本文主题有一定关系,所以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勾勒小川其 人,下篇举证说明此书之价值。下篇为本文重点。
)。日记起自1937年10月12日“第七号军(即第 十军)动员令下达”,讫于1938年2月21日小川随中支那方面军(注:国内多将中支那方 面军译为“华中方面军”,因考虑到日本所称“中支”与我国的“华中”无论在传统所 指自然地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指行政区划上都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而中支那 方面军的活动范围也始终未逾今天通常所指的华东以外,所以本文一仍日本旧称。国内 译名避免“支那”是因为以为“支那”是蔑称,如《“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中译本 第一页第一条注释称:“支那为日本对战前中国的蔑称。《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仍 沿用了这一称呼,表明了笔者的反华立场。为了客观反映该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译者 未加任何改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原著无“大”字,“南京屠杀”加引号 ,因为日本虚构派不承认“屠杀”,故称屠杀必加引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 “内部发行”版,第1页。)日本今天仍坚持以“支那”称中国者,一定是右翼,但援用 历史名称,如“中支那方面军”时,则不论左、右翼都不加改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 将一行坐船离沪,其中11月7日小川在金山登陆后所记均为中国见闻,对认识第十军在 华数月的活动,尤其是日军“军风纪”,有重要价值。因为小川为当时日军最资深的军 法官,他的个人经历与本文主题有一定关系,所以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勾勒小川其 人,下篇举证说明此书之价值。下篇为本文重点。
上篇:日军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其人
小川关治郎,1875年(明治八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海东郡木折村(现海部郡美和町大字 木折字宫越五)。1898年进入明治法律学校(现明治大学),1904年被司法省任命为见习 检察官,1906年为预备法官,1907年被陆军省任命为第十六师团法务部员。以后转任多 职。1937年10月第十军组建时任法务部长,次年1月迁属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3月晋为 高等官一等(军事高等官最高级别,相当于中将),同月致仕。战后曾任民事调停委员等 职,卒于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小川在大正末期和昭和前期参加过许多重大案件审判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甘粕事件”(又称“大杉事件”)、“相泽事件”和“2·26事件 ”的审判。这三起“事件”的共同点是肇事者都是极右翼军人(注:“右翼”只是笼统 说法。“相泽事件”和“2·26事件”中的“皇道派”军人一方面视天皇为“万世一神 ”,主张“在天皇陛下统御下,举国一体,完成八纮一宇”,实际是进一步推动日本的军国化,这可以说是右翼;一方面痛恨贫富悬殊和上层社会的腐化,致力于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元老重臣、财阀军阀,以改造社会,这又难以用通常所说的右翼来概 括。),在当时极端民族主义的时潮中,这些案犯反而成了得时誉的“英雄”(注:时至 今日日本仍有人如此看。如七十年代日本以“2·26事件”为题材拍摄的《动乱》,便 完全站在肇事军人的立场上,将皇道派描绘成救国救民不惜舍身的志士。影片还穿插了 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由日本极负人望的高仓健、吉永小百合主演,悲恸凄绝,不能不 让日本观众一洒同情之泪。),所以这类逆风审判对审判者多少都是一个考验。
“甘粕事件”发生于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6日,当晚东京宪兵队涉谷分队长兼麴町 分队长甘粕正彦大尉率人杀害社会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妻和大杉年幼的外甥。虽 然案发后甘粕自供杀害大杉只是“个人行为”,但案发时能动用宪兵队的两辆汽车,杀 害地点又在宪兵队本部,尸体也隐藏于宪兵队之内,加上甘粕的宪兵分队长身份,这些 迹象都不能不让人感到“个人”身后的组织背景。而这正是军方所要推脱和掩饰的。所 以作为军法官的小川在审判中的严厉追究,不仅显得不合时宜,也打乱了军方的意图。 因此第一次开庭后,小川便因“辩护方要求避忌”被军方撤换。辩护方称小川与被害人 是“同乡兼远亲”。这一子虚乌有的理由瞒不过任何人,所以时人讽刺说:小川是“大 杉君的妹妹的先生的哥哥的妻子的妹夫的表兄弟的寄养家的孙子”(注: ) 。在军方的意志下,甘粕仅被判刑十年,而且仅仅三年即提前出狱,后来成了日本在海 外占领地最重要的宣传机构“满映”的理事长。
) 。在军方的意志下,甘粕仅被判刑十年,而且仅仅三年即提前出狱,后来成了日本在海 外占领地最重要的宣传机构“满映”的理事长。
“相泽事件”是“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刺杀“统制派”中坚人物陆军省军务局 长永田铁山少将的事件,事发于1935年8月12日,其背后涉及了日本陆军内部复杂的派 系斗争。此事也成了次年2月26日军事政变的预演。“2·26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 大的政变,许多重臣被杀,给日本政、军界造成了巨大震荡。此事今天在日本仍家喻户 晓。小川参加了两案审理,对直接肇事者的审判无须多述,值得注意的是对被疑为“2 ·26事件”幕后黑手的真崎甚三郎大将的审判。真崎曾任陆军教育总监,教育总监的基 准军衔为大将,与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相同,位份很高。前一年7月15日转为闲职军事 参议官,这是导致“相泽事件”的直接起因。(真崎去职和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元帅的 坚主关系最大,但皇道派认为是统制派作梗。)真崎早在大正末出长士官学校时已开始 在青年军官中收揽人心,直至事变前仍与皇道派频有交往,所以事变后也以涉案者收审 。真崎对事变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至今扑朔迷离。真崎在临终前一年曾有一自述,为自 己撇清,称:
我并没有世间所想象的与“2·26事件”的关系,毋宁说,到事件突发为止,对这一无 谋的计划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对我来说,听到那天早晨突发事件的报道,犹如晴天霹雳 。然而这一布置周密的突发事件背后是真崎的宣传,不仅世间,宫中也确信不疑。
对他(指真崎——引者)历时一年三个月的军法会议,彻底调查,什么事也没有。
如果有一点关系的话,我决不能得救。今天没有复述全部调查的必要,但因为青年军 官如此拥戴真崎,当时的当局因此深疑被拥戴的真崎多少有所牵连。这个调查费时约半 年,直至世界法制史上所未有的推迟执行死刑,将三人作为证人,想通过延长时间来取 得有关真崎的证据,然而,没有的东西是怎么样都不会出现的。(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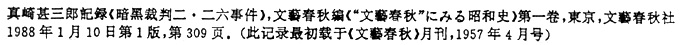 )
)
虽说此事至今仍是一个疑团,但真崎所谓如有关系“决不能得救”却有悖事实。因为 近年已有证据证明,真崎“无罪释放”实出日本军方的政治考虑。据晚近发现的松木直 亮大将的日记,松木和矶村年大将、小川关治郎军法官三位真崎案的法官,对案件持三 种态度。松木认为真崎有“野心”和“策谋”;小川认为不仅是“野心”和“策谋”, 在事发时真崎还有“对反乱者好意的言动”(此点若成立,即可定真崎“利敌罪”);矶 村则认为真崎没有“野心”和“策谋”。三人各执己见,尤其是矶村和小川的对立,发 展到了不欢而散的地步。最终矶村以疾病为由提出辞呈,导致“异例”的军法会议解散 (37年9月3日日记)。最后由陆军省法务局长大山文雄等出面“说服”小川,又“将公判 审理改为多数决定”(9月14日日记),复由陆军当局对小川所拟判决书进行删削,才使 真崎得以免罪释放。(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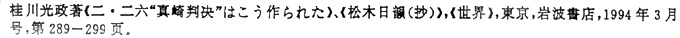 )对此,小川直至晚年仍未释然。(注:小川去 世前为小川作过一次诊断的医师增山隆雄说,在这唯一一次的接触中,小川说“真崎真 是个坏蛋”,因此让他“不能忘怀”。(
)对此,小川直至晚年仍未释然。(注:小川去 世前为小川作过一次诊断的医师增山隆雄说,在这唯一一次的接触中,小川说“真崎真 是个坏蛋”,因此让他“不能忘怀”。( 附录,第226页)对初次见面者这样说 ,可见此事在小川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附录,第226页)对初次见面者这样说 ,可见此事在小川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此类案件的是非曲折,无须由我们来裁断,小川在真崎案中的立场确实也有“道德” 的因素在(小川向其女儿说过真崎不仅毫无担当,而且卑怯无耻,所以极其鄙视其人格) ,但从主要方面说小川还是一个严格依律行事的军法官。作为第十军法务部长,不论小 川在日军中是不是特例,说明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日军军法官和小川日记都会有一定的 帮助。
下篇:《一个军法务官日记》的史料价值
战时日军各部队都有日志,其中法务部日志是反映日军暴行——包括杀人、放火、抢 劫、强奸的最重要文献。这不仅因为它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因为日军军法会议对日军暴 行的认定总是十分“矜持”,决不肯让自己平添嫌疑,所以这种肇事方的“不打自招” ,反映的虽然只是事实下限,但作为证据却最为坚实,最不可动摇。所以,也是赖小川 得以保留的侵华日军仅存的第十军法务部日志(1937年10月12日—38年2月23日,下简为 “日志甲”)和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38年1月4日—31日,下简为“日志乙”)意 义确实非同一般。有关于此,我在拙文《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已 有详论(注:在我的有限阅读中,中、日两国学者对日志和日记迄今都未加援用。拙文 将刊于北京《近代史研究》。)。最近复将记、志加以比勘,发现虽然所记内容颇有重 复、时间几乎一致(日记仅比日志甲少了一天),小川日记仍有重要的补苴罅漏的价值。 以下摭拾数例以为证明。
一,从日记所记周继棠等被处决案可见日军对中、日两方受审者的量刑极不公平,也 可疑今刊日志已遭删节
日志乙在1月27日“发送法务局长书类”中有一条“审判请求之件报告”,括注中有“ 周△△六名”一语。因日志乙既无“犯罪事实概要”(两志所记各案均有此项)和判文, 志末所附“处理事件概要通报”亦无相关记载,而日志甲也没有丝毫踪迹可循,遂使此 事成了一个悬疑。我曾留意当时各种记录,终未得解,一直觉得是个遗憾。不意小川日 记却在多处留下了记录。1月28日记周等六人审判、处决情况如下:
午前9时审判周继棠等六名违反军律事件。其中首领周继棠作为第二区队长,原来为流 氓,即无赖、侠客,以前所辖有五百人,一见即较他人沉稳。约1时审理结束,立即准 备执行。5时执行。自己作为检察官出席审判,又作为执行指挥让宪兵执行。犯人在审 判时对自己不利之点极力否认,但在执行时却没有任何恶态。进入刑场时极其沉着,毫 无畏惧,一言不发。没有任何障碍便结束了。(中略)犯人姓名(原注:数字为年龄):周 继棠(34)、方家全(28)、杨光珺(21)、徐祥庆(17)、张满棍(23)、顾传云(30)、陈坤林(29)。(注: ,第170—171页。)
,第170—171页。)
周继棠等所犯“罪行”,此日日记未记。从24日、26日日记看,周等被断罪当是以游 击队之名。24日记:
整日调查周继棠等六名违反军律事件文件。由不良青年纠合的别动队,依所谓游击战 术,以搅乱日本军后方为目的,在上海战役时进行了频繁活动。南京陷落后几乎都向广 东方向避遁(原文如此——引者),仅有少量残党仍进行地下活动。大部分为无赖(原注 :流氓),加入毋宁是生活困难所迫。
26日记:
作成周继棠等六名违反军律事件论告要旨。结论为:“被告等多数相结为党,属于对 帝国军加以危害的不逞集团。他们的行为不仅对帝国军队的危害甚大,对帝国所期待的 东洋和平亦是阻碍。因此,无庸置疑,绝对应扑灭此等极恶分子。故以严厉制裁,全部 应给以最重的处罚。”(注: ,第163—164、167—168页。)
,第163—164、167—168页。)
此案审理过程的详情,如被告究竟具体犯了什么“罪”,为自己做了怎样的辩护,处 罚根据的是什么条文,今天已无从知晓。但通过上引可以看到:军律会议(注:“军律 会议”受理占领地军民案件,与“军法会议”实为一套人马。)在开审前已决定“给以 最重的处罚”,审判不过是个走过场的形式;而且从开庭到判决,从判决到执行,仅仅 一日,这个形式走得也很不象样。日本不少人每每说日军对中国军民的处决(指战场以 外)都经过军律会议的审判,言下之意都有“合法”根据,周案告诉我们,这种“审判 ”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不仅如此,如果比较至今仍为不少日本人强调的经过军法会议 处罚的日军案件(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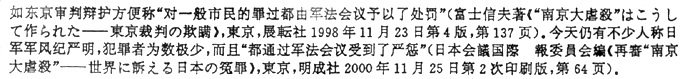 ),在徒有其名之上,更可以看到这种审判没有丝毫 公正可言。
),在徒有其名之上,更可以看到这种审判没有丝毫 公正可言。
在第十军和中支军军法会议所受理的所有日军烧杀抢掠强奸等案件中,处罚最重者仅 为惩役四年(注:另有六年一例、五年两例为“以兵器胁迫长官”和“敌前逃亡、毁弃 军用品”等“反噬”案件。),许多蓄意杀人、强奸都被免于起诉。如后备山炮兵第一 中队一等兵辻某(因虑“名誉”,志、记出版时当事人姓名都仅留一字,下同)杀人案 :
被告人在嘉兴宿营中,昭和12年(1937年)11月29日午后约5时,因支那酒泥醉,在强烈 的敌忾心驱使下,生出憎恶,以所携带刺刀杀害三名通行中的支那人(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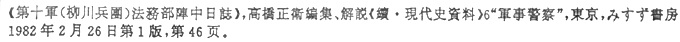 )。
)。
此处“犯罪事实概要”中所谓“泥醉”和“敌忾心”其实是为宽大——日军军法会议 判决中的惯用套语叫做“情可悯谅”——留下伏笔。今天日本也许仍会有人以为“泥醉 ”是“理由”,但一,依历版陆军刑法,杀人所当都应是死刑、无期惩役刑和长期惩役 刑;二,杀三人应较杀一人更重;三,即使退一万步说,“情可悯谅”也有底线,重刑 不能减为轻刑,更不能免刑。然而,辻某无端杀害三人,最后却仍被军法会议以所谓 “三○一条告知”免于起诉。
再如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上等兵外某强奸案:
被告人昭和12年11月27日昼,赴枫泾镇征发粮秣之际,沿途看到支那女子(十五岁), 试图逃跑,生出恶心,逮住强奸(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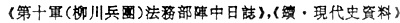 6,第47页。)。
6,第47页。)。
外某“公务”在身,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谓恣肆之极,结果也被军法会议以“三 ○一条告知”开释,免于起诉。
不仅量刑的轻重完全不当,对嫌犯的调查也惟恐失之于“偏”。如后备上等兵植某杀 人,本有确据,仍由军医部早尾 雄中尉(金泽医科大学教授)进行“精神”鉴定 。鉴定科目多达七类近三十项,如所谓“指南力”“领受力”“记铭力”(特指记忆新 事物力)“记忆力”“知识”“批判力”“妄想及幻觉”“观念联系”“胁迫观念”“ 感情”“意志”等等。植某的鉴定结论也十分烦琐,大约是饮酒过量,致“第一意识不 醒以前,受到第二意识(原注:极其原始的)发动的运动意识支配,因此误认事实,做出 不适合的行为”云云(注:
雄中尉(金泽医科大学教授)进行“精神”鉴定 。鉴定科目多达七类近三十项,如所谓“指南力”“领受力”“记铭力”(特指记忆新 事物力)“记忆力”“知识”“批判力”“妄想及幻觉”“观念联系”“胁迫观念”“ 感情”“意志”等等。植某的鉴定结论也十分烦琐,大约是饮酒过量,致“第一意识不 醒以前,受到第二意识(原注:极其原始的)发动的运动意识支配,因此误认事实,做出 不适合的行为”云云(注: ,第178页。)。如此繁复的检查,大概没有什么人 可得“正常”的结果。所以与其说是鉴定,不如说是为嫌犯开脱寻找理由。如此的调查 ,与对待周某等中国人的“斩立决”,真是有如天壤之别。
,第178页。)。如此繁复的检查,大概没有什么人 可得“正常”的结果。所以与其说是鉴定,不如说是为嫌犯开脱寻找理由。如此的调查 ,与对待周某等中国人的“斩立决”,真是有如天壤之别。
周继棠等人的具体案情不得而知,但没有造成日军人员财产损失则几乎可以肯定(如李 新民、陆丹书等投掷土制手榴弹案,日军未受伤害,仍有详细记录,若对日军造成危害 ,不会没有记录)。所以对周继棠等的严苛和对辻某等的轻纵,说明日军军律会议虽有 审判的外衣,实质则只是镇压;即使不论“法”本身的问题,审判也只是与公正全然无 关的枉法。
这样的“审判”以战后的价值是没有袒护余地的,因此我疑日志不见周案详情,是出 版方或小川本人有意隐瞒,做了手脚。因为一,就一次枪毙六人而言,周案在中支军( 第十军亦如此)军法会议(包括军律会议)所有案件中为最重大刑案(注:仅就判决结果说 。就案情说,则第十军后备步兵第四大队少尉吉某等一次无端枪杀二十六名金山平民为 最大罪案,但此案肇事者全部被免于起诉。),日志绝无不加记载的任何理由。二,以 记、志所载各案相比较,日记有而日志无者,只有周继棠、陆丹书两案,其中在日志乙 范围内(1月31日讫)的仅有周案。三,日记1月28日所记限于周案审判和处决,28日军法 (军律)会议似应没有其他活动,是以日志乙此日全缺,当为删除周案后已无它事可留; 换言之,以周案以外的其他记载未能保留作为否定日志乙缺28日事出它故的理由并不存 在。四,陆丹书之处决在2月6日,逾出日志乙讫日,本可不论,但日志乙附有讫日之后 的判决书,如晚于陆案判决的上海派遣军野战衣粮厂一等兵福某监守自盗案(与陆案同 日调查,10日判决),所以日志不见陆案痕迹,理由当与周案一样,是为了遮掩,因此 不载陆案也可以作为不载周案理由的又一证据。(李新民案得以保存,因为李被判死刑 后越狱逃脱。)凡此应可证明,为了掩盖军律会议对中国人的不当重判,今刊日志经过 了删节。
二,从日记与日志的异文可见日志对事实的损益和日记的重要价值
日记在内容上与日志多有重合,但因是私下记录,较少利益考虑,不象日志那样严守 分寸,多有可以补充日志的真消息。在此谨举三例为证。
第十军作战部队11月5日登陆后,占领金山城等地基本没有遇到抵抗,但仍不断进行烧 杀抢掠。(战斗艰难、伤亡惨重激发出的报复心是造成日军暴行的原因之一,现在已成 普遍看法(注:这一看法在日本由来已久,不少当事人也供认不讳,如第六十五联队第 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位下士官称:“真是很惨重,都是‘为国’而战死的。希望把进攻 南京看作是这场激战(上海战役)的延长。俘虏来投降,便轻易地释放的气氛完全没有。 是受到那样伤害的战友的仇啊。这样的心情,我想让那时战斗的中国士兵们明白。假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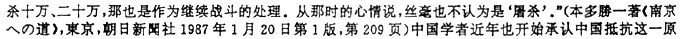 因,如称:“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也加剧了日本侵略军 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后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 保卫战的进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孙宅 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页)不过,此处所指 “抵抗”与日本所指不尽相同,日本指的是淞沪战役,而非“南京保卫战”。就当时实 际而言,日军进攻南京受到的抵抗远不及上海激烈,如上海打了近三个月,而南京不足 一周,日军的伤亡也仅是上海的数十分之一。如果将南京的“英勇抵抗”作为“基本原 因之一”,不免会留下一个疑问:日军的“暴行”为什么不是在上海更“残忍、疯狂” 。),而第十军在中国数月,没有遇到激烈抵抗,也没有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那样的 重大伤亡,除了与上海派遣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占南京,以后几乎已无战事,如占领杭 州时不费一枪一弹的“无血入城”。所以第十军的表现更能反映常态下的日军性格。) 第十军法务部7、8两日在金山登陆,次日(9日)日志甲记:
因,如称:“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也加剧了日本侵略军 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后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 保卫战的进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孙宅 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页)不过,此处所指 “抵抗”与日本所指不尽相同,日本指的是淞沪战役,而非“南京保卫战”。就当时实 际而言,日军进攻南京受到的抵抗远不及上海激烈,如上海打了近三个月,而南京不足 一周,日军的伤亡也仅是上海的数十分之一。如果将南京的“英勇抵抗”作为“基本原 因之一”,不免会留下一个疑问:日军的“暴行”为什么不是在上海更“残忍、疯狂” 。),而第十军在中国数月,没有遇到激烈抵抗,也没有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那样的 重大伤亡,除了与上海派遣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占南京,以后几乎已无战事,如占领杭 州时不费一枪一弹的“无血入城”。所以第十军的表现更能反映常态下的日军性格。) 第十军法务部7、8两日在金山登陆,次日(9日)日志甲记:
午后3时军宪兵队长上砂中佐就金山卫城(今金山卫镇——引者)附近掠夺暴行等军纪弛 缓的情况与小川部长联系。(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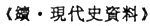 6,第29页。)
6,第29页。)
小川日记同日记:
午后据视察了金山卫城的宪兵队长上砂说,同城附近掠夺十分严重,无益的杀伤惨不 忍睹。(注: ,第18页。)
,第18页。)
不仅日记的“十分严重”在程度上显然更甚,“无益的杀伤惨不忍睹”也为日志失载 。而此处所引是小川本人得到的报告,所记自当更为可信。上引本来算不上重大区别, 可以不论,但近年日本虚构派在否认日军暴行中,常常抓住史文中的这种差别大做文章 。比如事发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的石射猪太郎曾在《外交官的一生》中说:
跟随我军回到南京的福井领事的电信报告和随即上海领事发来的书面报告,让人慨叹 。因为进入南京的日本军有对中国人掠夺、强奸、放火、屠杀的情报。(注:石射猪太 郎著 太平出版社1974年4月15日第4次印刷版,第267页。)
太平出版社1974年4月15日第4次印刷版,第267页。)
这条回忆一直被作为日本高层在南京暴行事发第一时间已经知情的证据。但因石射在 东京审判回答伊藤清律师有关石射庭证(第3287号)中说到“残暴”(Atrocities)的具体 所指时,没有提及“屠杀”二字(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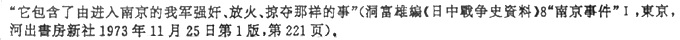 ),虚构派便抓住这一枝节的出入, 视为重大差别,声称当时实无“屠杀”(注:
),虚构派便抓住这一枝节的出入, 视为重大差别,声称当时实无“屠杀”(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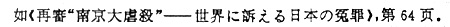 )。近又有人以石射日记未记“屠 杀”(注:
)。近又有人以石射日记未记“屠 杀”(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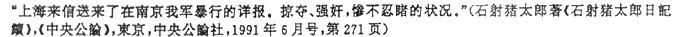 ),“证明”“原来没有‘屠杀’”(注:
),“证明”“原来没有‘屠杀’”(注: 社2002年9月 16日第1版,第179页。)。有关此事辨析,拙文(注:《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 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169—208页。)已详,此处不另。在这样的两方 相争的背景下,小川所记和日志的看似平常的差别,实有重要的意义。以上为第一例。
社2002年9月 16日第1版,第179页。)。有关此事辨析,拙文(注:《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 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169—208页。)已详,此处不另。在这样的两方 相争的背景下,小川所记和日志的看似平常的差别,实有重要的意义。以上为第一例。
例二。日志甲10日记:
村落并无荒废之迹,但村落内约十处房屋被烧毁,此为敌之兵燹所致。(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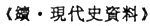 6,第30页。)
6,第30页。)
日记10日记:
午后在附近视察,火灾之迹各处散见,或云是便衣队放火后逃跑,或云是日本军的行 为,真伪不明,相当惨烈。(注: ,第19页。)
,第19页。)
“并无”和“各处散见”不同;“或云”虽不确定,比日志的断言,却是较可信的态 度。以后日记更有“真伪不明”事项得到澄清的记录,下将略及。
例三。日志甲11月18日记录军司令部会议中说到军风纪糟糕时,有“为了肃正军纪即 使有牺牲者也不得不”(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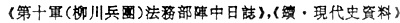 6,第37页。)之语。(“牺牲”二字并非故作危言 ,因为日军的骄兵悍将自恃卖命打仗有“功”,以为可享胡作非为的特权,并不把宪兵 放在眼里。)这确可说是“决心”的表现,但当天会议谈及此事时其实并不仅于此,小 川在当日日记中保留了日志“忽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内容与“牺牲”同条 而列之于前:
6,第37页。)之语。(“牺牲”二字并非故作危言 ,因为日军的骄兵悍将自恃卖命打仗有“功”,以为可享胡作非为的特权,并不把宪兵 放在眼里。)这确可说是“决心”的表现,但当天会议谈及此事时其实并不仅于此,小 川在当日日记中保留了日志“忽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内容与“牺牲”同条 而列之于前:
第一线部队另当别论,后方部队应保持军纪。(注: ,第46页。)
,第46页。)
这实在是不能遗漏的大关键,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日本左右两翼论及日军中央对军风 纪的告诫(12月28日),不论是以之证明日军对军风纪问题的“重视”,还是以之证明日 军军风纪问题的严重,所指都是12月末南京暴行发生、日本军政高层受到外界压力之后 。因此,我在此想慎重提出一个推断:虽然我们不能将小川所记“另当别论”简单地看 作鼓励犯罪,简单地与豁免权划等号,但在12月末之前,第十军——上海派遣军也可以 推想——对“第一线部队”应该有过“保持”军风纪可以缓行的明确表示。也就是说, 南京的骇人听闻的暴行,除了日军骄兵悍将“个人”的因素,日军“组织”也有推脱不 了的责任,这应该是一条有力的旁证。
上举日志对事实的损益之例,当非日军记录中的特例。如果这一推断不误,则日军事 发时留下的文献,就反映日军暴行而言,已经打了折扣。
三,从日记更正金山城劫掠之真凶可见事发时日方的记载确有偏见
小川日记之所以和日志比较仍别有自具的价值,和小川的客观态度也有很大关系。这 从下举之例中可以看出。11月15日日记中记:
在[金山]市内(今朱泾镇——引者)巡回,市的大部分成了废墟,这当是人为造成的。 偶尔看到烬余的房子,东西被劫后的散乱,难以名状。如大书店和药房,进去一看,其 内部的气派可以和三省堂(东京最大的书店之一——引者)匹敌,但不论是药还是书都破 损散乱了。其他所残存的店铺也无不如此。此等暴戾狼藉,当非日本兵所为。推测起来 不是支那败残兵的所为么?听说支那禁止将任何东西留给日本兵,如退却全部破坏烧毁 才逃跑,因此不论肝肤(原注:原文如此)尽可能的全部破坏烧毁。(注: ,第3 6页。)
,第3 6页。)
小川这样推断,也许是误信传言,也许是对日军军纪估计过高,这也是不明真相的日 本人最容易接受的看法。这种偏见,即使有中国证人证明,往往也难以改变。所以小川 稍后告诉我们真凶的日记(17日)显得特别可贵:
风闻日本兵暴戾狼藉,多少有些疑问。今日军医部中佐作为前□(原文如此——引者) 者,说:10日到达金山,当时如某书店,即前记可与东京三省堂匹敌的那家,毫无被害 的痕迹,后来到同店一看,如前所记实在是凄惨暴戾狼藉之极,显然这决不是支那兵的 所为,而完全是日本兵的所为。实际确如所说,让人不胜惊骇。(注: ,第45 页。)
,第45 页。)
10日后金山已是日军的天下,所以从“毫无被害的痕迹”一变而成为“凄惨”“狼藉 ”,只可能是日本兵的所为。这是一个可以举一反三的例子,当时日本的观察者,官兵 、记者、外交官等等,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日军的暴行总是宁信其无。小川日记的 特别价值就在于:它既是对所见所闻的照实而录,又是站在日军立场上的记录。所以它 所记录的“支那兵”的暴行虽不免为误传,但所记日军暴行则均应是有据的确证。
四,从日记所记日军犯罪和小川对日军犯罪的“痛恶”可证小川在东京审判时为辩护 方提供的证词为伪证
东京审判时许多参与侵华的辩护方证人都一口咬定日军在华军纪严明,没有暴行,不 仅对审判产生了影响(注:如松井石根虽然最终被判处最高量刑——绞刑的处罚,但所 罚只是消极的“不作为责任”,否认了公诉人提出的被告的“非法命令、授权、许可” 。),对以后长时间在日本学者以至民众认识上出现的“歧义”也有重要影响(注:详请 参拙文《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北京,《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 —57页;《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论著平议》之五,拙著《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 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0—354页。)。我在前面已说过,侵华日军的战时文书档案 大多已被焚毁,这是对这些“证言”证伪的最大困难(注:中、西方留下的证据,日本 相当多的人不予承认,认为它是战时“敌国”或助敌之国的宣传。如铃木明、北村稔、 东中野修道等分别“考证”出田伯烈(H.J.Timperley)、贝茨(M.S.Bates)等为中国顾问 ,中、西方的证据都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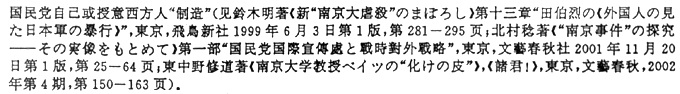 )。小川东京审判时也曾出庭,为日军作了无罪证 明。所以小川日记如能有相关记录,当可成为解明此事的一个突破口。小川在向远东军 事法庭提出的“宣誓供述书”(辩护方文书第2708号、法庭庭证第3400号)中这样说:
)。小川东京审判时也曾出庭,为日军作了无罪证 明。所以小川日记如能有相关记录,当可成为解明此事的一个突破口。小川在向远东军 事法庭提出的“宣誓供述书”(辩护方文书第2708号、法庭庭证第3400号)中这样说:
没有听说日本军的不法行为,也没有不法事件被起诉之事。日本军是作战态势,军纪 很严肃。(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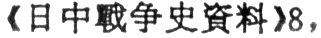 第256页。)
第256页。)
小川的两个“没有”说得很肯定。这种证言出自法务部长之口,对不明真相的日本人 有特殊的分量。幸而小川日记仍存于世,使判别这一证言的真伪,有了最可靠的根据。 以下我们就来对小川日记做一检查,查一查他当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是不 是像他自己说的什么都“没有”。
前记小川登陆次日即得上砂胜七宪兵队长报告日军掠夺和杀戮,接着小川记:“担心 引起非常的问题”(注: ,第18页。)。以后小川所见日多,在日记中也每有感 慨。因为此事不仅关系小川一人的证言,对其他辩护人辩词也有比照的意义,所以在此 不妨较详援引。11月24日日记记:
,第18页。)。以后小川所见日多,在日记中也每有感 慨。因为此事不仅关系小川一人的证言,对其他辩护人辩词也有比照的意义,所以在此 不妨较详援引。11月24日日记记:
所到之处恣意强奸,不以掠夺、放火为恶事,作为皇军,这实在是难以言表的可耻。 作为日本人,特别是应该成为日本中枢的青年男子,假使带着这样无所顾忌的心理风习 凯旋而归,对日本今后全体的思想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想到这一点,让人栗然。我想 日本政府当局应对此研究,对思想问题应加以根本的大改革。这是稍稍极端地说法。然 而如某人所说:日本兵比支那兵更残虐,这是作为日本人的我们不胜感慨的。听说支那 人将我们日本人称为猛兽,将日本兵称为兽兵,闻之使人战栗。从支那方面来看当然是 这样。作为我们,对日本兵的实际见闻不堪遗憾之例不遑枚举。(注: ,第59 页。)
,第59 页。)
小川并不以“野兽”“兽兵”为诬枉,是因为“实际见闻不堪遗憾之例不遑枚举”, 所以作为职业军法官的他只能“不胜感慨”。
11月25日记:
昨夜3时半松冈宪兵大尉不拘深夜来报告重大事件。事件为第六师团五名士兵(内伍长 一名)在约三里(一日里约当近四公里——引者)的乡间劫持十几至二十六岁女子在某处 大空宅恣意强奸。而且,劫持之际枪杀逃跑的五十五岁女子,并射伤另一女大腿部。违 反军纪,不逞之极,让人无话可说。
△(日记原符号——引者)日本政府声明,今后以支那政府为敌,不以一般国民为敌。 然而,日本兵对没有任何罪过的良民的行为不逞之极,如何看待在这样行为之下的一般 支那国民的更进一步的抗日思想呢?为了日本帝国的将来计,让人不寒而栗。
(中略)看日本兵对支那人的使役,用枪对着,完全像对待猫狗,因为是支那人,完全 不抵抗。反过来,如果和日本人易位而处,会怎么样呢?(注: ,第62—63页。 )
,第62—63页。 )
虐待军人,因战争的酷烈有时难以完全避免,但非人的对待“良民”,则再怎么退而 说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小川能将心比心,想到“易位而处”,既说明小川还有起 码的良知,更是由于日军表现“不逞之极”,使小川不能不受到震撼。
11月26日记:
从各方面的观察,不仅第一线部队,后方部队的狡狯之兵也故意落伍,进入民家干恶 事。如上记杀人、掠夺、强奸事件的被告人即是此类。结果,正直的、认真的士兵在第 一线英勇奋战,稍一疏忽即战死,狡狯的家伙恣意妄为,什么战斗也不参加,称作国贼 、反逆者、害群之马绝非过言。越发使人感慨。
(中略)他们一看到日本兵立即逃散,女子、小孩似对日本兵极其恐惧,这是日本兵所 做恶事造成的。如果什么恶事也没做,理当不会逃跑。真是使人非常遗憾。
皇军的脸面是什么呢?所谓战争,自己开始什么都不能判断,但上记支那人对日本人的 感情,日本兵素质今后对青年男子的影响,完全让人寒心。(注: ,第65—66 页。)
,第65—66 页。)
(此日日记后记法务部成员田岛隆弌调查25日日记所记强奸杀人案,谓“听现场调查 状况,其恶劣超出想象”,而特别可注意者为此案中杀死三人、杀伤三人,而日志乙所 载正式案卷和判文仅为一死一伤。)中国民众对日军“极其恐慌”,由“日本兵所做恶 事造成”,“让人寒心”,单凭此日所记就足见小川的法庭证词全未据实。
11月29日记:
有的士兵让支那人背负行李,(中略)稍有不从或显出不从的样子,就立遭处罚,让人 无话可说。途中看到士兵二人拔出剑刺击一个仰向的支那人。又一个支那人沾满鲜血, 苦痛不堪。见及于此,感到战败国国民之可怜无以复加。(注: ,第78页。)
,第78页。)
当时强征中国人随军服苦役的情况十分普遍,12月11日又记:
这些支那人拼着命背负行李,其中有相当的老人,没有比战败国良民更不幸了。这样 的场合,对我士兵稍有不从,立即处罚。万一逃跑,就在这一带立即处决。(注: ,第105页。)
,第105页。)
行文至此,忆及前些年美国日侨为战时收容向美国政府索赔(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 曾将日本侨民集中监管,这一举措是由当时的特定背景决定的。作为一个敌对国,尤其 是一个以偷袭方式使自己蒙受巨大损失的敌对国,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已毫无信用可言。 因此,疑及日本侨民,采取防范措施,不仅十分自然,也有充分理由。但事过境迁,在 一个没有硝烟的时代,你死我活的环境已为人淡忘,圈居与现代立国理念的抵触却日益 突出。于是,在美日侨向美国政府控诉战时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要求美国政府道歉 赔偿,不仅得到日本朝野的一致支持,美国也不得不作出让步,给予赔偿。),在索赔 过程中,日本电视台数度播放难民营实景,作为所谓“不人道”待遇的证据。对照小川 所述及类似记录,日军加诸中国人的苦痛比起日侨所受的“迫害”真是何止百倍!
因为第十军登陆后并未受到激烈抵抗,所以第十军所过之处留下的尸体,必有相当部 分是此类随意“处决”的受害者。从金山登陆起,几乎每到一处,小川都会遇到中国人 的尸体。如11月14日上午往张堰镇途中,“河、潭、田中到处都是尸体”“尸体不计其 数”,下午到达金山时所见尸体中居然有的“全裸”(注: ,第27、30页。)。 11月17日在金山郊外,“今日仍有支那人尸体”(注:
,第27、30页。)。 11月17日在金山郊外,“今日仍有支那人尸体”(注: ,第44页。)。11月28日 在往湖州途中,看到“累累尸体”,其中相当部分穿着平民服装。12月10日小川记:“ 途中各地所见支那人尸体,不计其数”(注:
,第44页。)。11月28日 在往湖州途中,看到“累累尸体”,其中相当部分穿着平民服装。12月10日小川记:“ 途中各地所见支那人尸体,不计其数”(注: ,第102页。)。这样大量的尸体 使小川的感觉变得麻木,诚如他在12月11日日记中所说:
,第102页。)。这样大量的尸体 使小川的感觉变得麻木,诚如他在12月11日日记中所说:
最初由李宅向金山进发途中看到支那人的尸体时,总有异常的感觉,但渐渐看到大量 的尸体,就习以为常了。此时的感觉就如在内地看到狗的遗骸一样。(注: , 第107页。)
, 第107页。)
杀人,或者说抹杀中国人的生命权,是第十军在中国的最严重犯罪,其他“军风纪” 问题,直至中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的建制撤消,行将回国之前,同样也很 严重。如2月15日日记中有:
塚本法务官到,听取南京方面事件的状况。特别是接受了天野中尉强奸事 件的详细报告。(中略)各方面强奸事件频频发生,对之如何防止是应特别研究的问题。 (注: ,第192页。)
,第192页。)
以上所见种种,都是驳斥小川在东京审判所说未闻日军犯罪的最有力证明。虽然,我 们不能将小川之例无限夸张,断言当时类似的证据都是有意作伪,但小川证词和日记的 相反记载,至少可以证明东京审判时与小川相同的那些证词不合实情。
五,从日记所记南京南门之中国军队尸体和大火可再驳日本老兵城内无尸体和火灾之 “证言”
日本旧军人团体偕行社所刊《偕行》(月刊),主要发表有关日军战史的文字,近三十 年来刊有不少参加南京战役的老兵的回忆,其中多有南京既无尸体,亦无火灾的“证言 ”。如亩本正己(日军攻克南京时为独立轻装甲车队的小队长)在《检证“拉贝日记”》 中所引伊庭益夫“没有尸体”,栗原直行“在扫荡区域内,既没有住民的人影,也没有 遗弃的尸体”(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土屋正治“在城内巡回,没有看到尸体”(注:附 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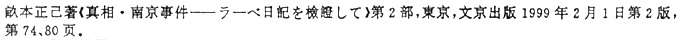 )等等。近年积极策动状告东史郎的森英生(日军攻占南京时为步兵第二十联 队第三中队中队长)说:
)等等。近年积极策动状告东史郎的森英生(日军攻占南京时为步兵第二十联 队第三中队中队长)说:
我是第三中队的中队长,除了安排值日的警备外,自己也骑马在警戒区内巡查,但一 件非法的事件也没看到。巡查时是不进入安全区的,但如果发生违法和火灾,必须报告 上司,进行处置,但这样的事一次都没有发生。(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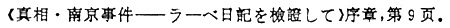 )
)
上引为无据妄说,我已详征有关文献加以证明(注:拙文《对“检证‘拉贝日记’”的 检证》,北京,《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50—183页。此文所引之外的最重要 第一手证据,是日军支那方面舰队军医长泰山弘道大佐、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旅 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日记等文献,详见前引拙文,第100页注5。)。日记再一次证明 这些老兵证言的不实。
12月14日下午3时半,小川到达可见南京城墙之处,沿途中国军队尸体重叠(注:南京 留下的大量尸体的正身主要应是被屠杀的俘虏。详见拙文《日军屠杀令研究》,北京, 《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68—79页。),到处燃烧着大火,日军只能“跨过尸体前 进”。从“南门”进城后:
一进门就看见两侧的累累尸体。(中略)在屋上眺望,广泛的市街到处都是冲天的火焰 。确实是战争的光景。(注: ,第111—112页。)
,第111—112页。)
15日巡视南京城内,“各处依然都是火灾,黑烟薰天”(注: ,第114页。)。
,第114页。)。
这样的记录,绝非时隔数十年、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回忆所能推翻。如从方法论上说, 即使同为事发当时所见,除非拿出有意作伪的过硬证据,彼眼所见也只能补充而不能否 认此眼所见。小川日记再次告诉我们,晚近日本老兵那种不留余地的断言,并没有事实 的根据。
六,从日记所记自布烟幕的传说可证日军“误炸”英舰出自有意
日军在进攻南京过程中,为堵截中国军队撤退,海军第十三航空队飞机在南京上游长 江炸沉美国军舰Panay号及美孚石油公司船只三艘,第十军野战重炮兵第十三联队在芜 湖附近击伤英国军舰Ladybird号等二艘及商轮一艘。在当时引起了英、美两国的强烈抗 议,因日本迅即“陈谢”和赔偿,此事很快得以了结。但日本当时同时强调日军是“误 炸”,声称因为事发时上述军舰都放了烟幕,致使无法看清国旗。此事究竟,似乎已成 不解之谜。但小川日记12月22日所记却为解开这一疑团提供了一条线索:
窃闻即使有些事实无法判明,但桥本部队(第十三联队长为桥本欣五郎大佐——引者) 似乎是自布烟幕,然后炮击。(注: ,第125页。)
,第125页。)
小川作为军的部长,他的“窃闻”应有相当根据。当时日军不择手段,掩人耳目,都 时或见之。而且,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向英、美道歉,第十军和中支军都表 示强烈反对。第十军“军司令部……要求取消广田外相的陈谢”(注: ,第125 页。),中支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则电报东京,表示“对责任者的处分绝对没有必要 ”(注:
,第125 页。),中支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则电报东京,表示“对责任者的处分绝对没有必要 ”(注: 偕行社1989年11月3日第1版,第18页。)。现地日军之所以反对日本政 府的“陈谢”,撇开包庇部下的一般理由,确实是因为不愿让作战受到规则的束缚。所 以,虽然从建制上看,日军对外有国际法顾问(中支军顾问为斋藤良卫法学博士)、对内 有军法会议,又有一系列可与不可的制度性规定,似乎是一支现代军队,但质之以实际 ,日军为了达到目的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罔顾国际法,不择手段的。日本左翼学者将日 本军队指为“前近代的”“野蛮的”军队(注:如津田道夫著(程兆奇、刘燕译)《南京 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第1版,第89页。),并非 苛责。
偕行社1989年11月3日第1版,第18页。)。现地日军之所以反对日本政 府的“陈谢”,撇开包庇部下的一般理由,确实是因为不愿让作战受到规则的束缚。所 以,虽然从建制上看,日军对外有国际法顾问(中支军顾问为斋藤良卫法学博士)、对内 有军法会议,又有一系列可与不可的制度性规定,似乎是一支现代军队,但质之以实际 ,日军为了达到目的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罔顾国际法,不择手段的。日本左翼学者将日 本军队指为“前近代的”“野蛮的”军队(注:如津田道夫著(程兆奇、刘燕译)《南京 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第1版,第89页。),并非 苛责。
七,从日记对军部的抱怨可见日军决不愿意让法务部束缚日军战斗力
日军军法会议由法务部成员(职业军法务官)和所谓“带剑的法官”(军事人员)组成。 从理论上说,军法官与“带剑的法官”在职权上没有区别,所谓“作为专门法官,以其 专门的知识,努力使审判事务适正,但与所谓‘带剑的法官’的判士(法官——引者)在 职务权限上没有任何差别,在事实的认定、法令的解释上,全体法官具有同一的权能。 ”(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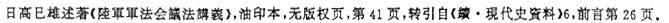 )然而正如《日本现代史资料·军事警察》编者所说:军法官“在兵科 军官 = ‘带剑的法官’的判士之下,也有只是充当无力的事务官的一面”(注:
)然而正如《日本现代史资料·军事警察》编者所说:军法官“在兵科 军官 = ‘带剑的法官’的判士之下,也有只是充当无力的事务官的一面”(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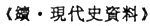 6,前言第27页。)。对此,小川女儿少时曾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体验。长森 (小川)光代说,她读小学时,因父亲军法官的领章和军帽帽圈的颜色特别(白色,当时 陆军是红色,骑兵是绿色,航空部队[时空军尚未成为独立军种]是兰色等),数量稀少 ,让人侧目,她的同学甚至问:“你父亲是支那兵么?”为此少女光代十分苦恼,想: “要是父亲是普通的军人多好,多神气,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注:
6,前言第27页。)。对此,小川女儿少时曾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体验。长森 (小川)光代说,她读小学时,因父亲军法官的领章和军帽帽圈的颜色特别(白色,当时 陆军是红色,骑兵是绿色,航空部队[时空军尚未成为独立军种]是兰色等),数量稀少 ,让人侧目,她的同学甚至问:“你父亲是支那兵么?”为此少女光代十分苦恼,想: “要是父亲是普通的军人多好,多神气,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注: )
)
法务部不为各级部队、尤其是战地部队重视,可以想见。但如果没有当时的第一手材 料,要破除所谓日军军法会议功能完备、有效之说却也并不容易。小川日记出自最直接 的当事人之手,它的相关内容,不仅对法务部长一己的内心感受,对法务部的实际处境 ,都是最真实也最无可置疑的记录。
日军军法会议由军人参与,为的是所谓“审判权和军队指挥权的一致”,军法会议的 最终裁决权也因此掌握在但任军法会议长官的各级司令官手中。所以,作为承担日常事 务的法务部,不论是为了发挥高效机能,还仅仅是为了正常周转,都必须随时保持与司 令官的紧密联系。因为参谋部、副官部、管理部、兵器部、经理部、军医部、兽医部、 法务部以及通讯班等军部各部门本来即随司令官同行,所以除非刻意安排,法务部本来 就应在司令官左近。但从小川日记可见,副官部门屡屡试图将法务部从军部支开。对此 小川十分不满。如11月24日日记记:
明日应向嘉兴出发,突然不知什么理由要我们延期到后日,对此,我们提出抗议,理 由如下。
(中略)第二,军法会议事务一切仰司令官裁决,因此我们的事务离开司令官即无法执 行。如果司令官和我们的所在相分离而无法得到司令官的裁决,最应注重迅速的战地军 法会议的手续就会造成滞涉。现下羁属中的三名放火事件嫌犯,虽然检察官的调查已经 结束,但因未得司令官命令而无法提起公诉,事件的处置只能延迟。
此节栏外又有:
我们的职务无法独断专行。如果以为我们无用,则令人遗憾万千。(注: ,第 61—62页。)
,第 61—62页。)
所谓“无用”,不是小川的无端疑心,因为法务部的不受重视以至于不受欢迎,从大 、小许多事情上都可以看出。举一件待遇方面的小事为例。12月10日第十军军部由湖州 向溧水进发,许多部长和副官坐飞机,小川被安排坐汽车。小川以为这是“歧视”,所 以在当日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愤慨”。这种情况和文官地位的普遍低下确实有关,小 川在12月12日日记中的如下记述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我们文官不得不受到这种歧视对待。(特别是军人的威势日益暴戾,极尽军人式的随心 所欲。原注:括号内原文被划除。)只是靠恩赐,也许因此还会受到某种妒忌,然而在 任何场合都一样,我们实际被当作累赘。(注: ,第109页。)
,第109页。)
但对法务部的“歧视”还不仅仅是出于战争环境下武人对文官常有的蔑视,更是因为 法务部的功能与日军败坏的军风纪确有冲突。
小川日记12月8日记:“塚本部长万事消极,万事不为。”塚本是上海派遣军法务部长塚本浩次,“不为”和“消极”的原因,小川日记说是听说“内部欠融和”(注: ,第97页。)。然而,就当时的日军状况言,仅仅因人际关系便“万事不为”,实难想象。我以为之所以“不为”,应该和法务部工作难以展开有关。东京审判时不少日本军人提到各部队对法务部的抗议,理由是法务部处罚太严,其中便有塚本浩次。他说:“对于上海派遣军法务部处罚的严厉,对于细微之罪也纠明的态度,各部队都进行了非难。”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也说到,因为“军纪极其严正(依文意应指过严——引者),便有第十六师团向法务部提出抗议那样的事。”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也说他曾为部下鸣不平(注:
,第97页。)。然而,就当时的日军状况言,仅仅因人际关系便“万事不为”,实难想象。我以为之所以“不为”,应该和法务部工作难以展开有关。东京审判时不少日本军人提到各部队对法务部的抗议,理由是法务部处罚太严,其中便有塚本浩次。他说:“对于上海派遣军法务部处罚的严厉,对于细微之罪也纠明的态度,各部队都进行了非难。”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也说到,因为“军纪极其严正(依文意应指过严——引者),便有第十六师团向法务部提出抗议那样的事。”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也说他曾为部下鸣不平(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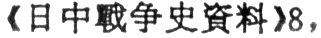 第191、252、239页。)。所谓“严厉”,从日志所载判例看完全是妄说,我们在以上“一”“量刑极不公平”中已提及,但即便重罪轻罚或不罚,法务部的性质仍决定了它不可能为日军骄兵悍将所接受。
第191、252、239页。)。所谓“严厉”,从日志所载判例看完全是妄说,我们在以上“一”“量刑极不公平”中已提及,但即便重罪轻罚或不罚,法务部的性质仍决定了它不可能为日军骄兵悍将所接受。
塚本部长所说的“非难”,从小川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到。小川38年1月赴方面军(方面军未建立法务部,小川附属于司令部),他感到方面军与军的明显不同在于没有直辖部队,因而不必考虑“人情”:
(在军时)须考虑军对于部下的罪行有直接责任问题,也有对部下人情方面的相当意见 ,因此,我们对长官条陈意见时不能不战战兢兢的深加思考。(注: ,第149页 。)
,第149页 。)
所谓“相当意见”,当就是塚本浩次所说的“各部队”的“非难”。
其实就当时情况看,对法务部门的不满,不仅仅是是基层部队。日记中有一条关于松 井石根的记载,颇值得注意。1月15日记:
司令官(原注:松井石根大将)是保持威严?还是生来的傲慢气质?和迄今接触过的大将 比,是有点奇怪的类型。长官不太端架子,能使自己的方针为下级理解,我以为这样才 好。完全没有必要那样的摆排场。过于端架子,未免不能让接触者所述的充分意见得到 考虑,因此,种种考虑也难以使上级了解。特别是长官和部下的关系,下者充分了解上 面的意见,上者充分研究下面的意见,倾听有意见者的意见决不是无益的……(省略号 为原文所有——引者)端架子的原因是什么呢?(注: ,第153—154页。)
,第153—154页。)
有关松井其人,有各种描绘,如东京审判时冈田尚等日方证人所作的不实证词(注:冈 田所说之从无人置疑而实不可信,请参拙文《南京大屠杀札记》之八《松井石根有可诉 之冤么?——冈田尚辩词析》,上海,《史林》2003年第1期,第105—108页。),但从 没有人说过“傲慢”“端架子”。松井给小川的印象之所以与众不同,我以为原因在于 松井对维持军风纪的态度。表面上松井也多次谈及要注意军风纪,但一,军风纪之于松 井,分量甚轻,不仅不能影响作战,也不能处罚肇事者,如前引Ladybird号事件;二, 日本政、军高层迫于欧美强国压力要求中支军约束军风纪,使松井十分难堪,攻占“敌 国”首都的欢愉也因此一扫而光。中支军军法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拼凑,对松井而 言,当非出自本愿(从松井继任者畑俊六大将等日记看,松井之被解任多少与 军风纪败坏有关联)。所以,对年资相若并无过节的小川,松井一反常态的“傲慢”“ 端架子”,不论是真心流露还是故作姿态,所传达的都不外乎是对军风纪压力的强烈抵 触情绪。
八,从日记所记宪兵对不起诉之异议可再见日军军法会议确有徒具形式的一面
塚本浩次的“万事消极,万事不为”,事出迫不得已,已如上述。第十军 情况虽较上海派遣军为轻,但法务部处境仍可谓左右为难。所以许多案件到了法务部都 只能不了了之。因此引起了执法宪兵的不满。12月25日小川记:
上砂中佐来部商量事务。中佐曰:近期的强奸事件多不起诉,宪兵费力的检举,到头 来努力白费。本人答说:或许如此。但本人以为,战争中的情状、犯人当时的心理、支 那妇人的贞操观念、迄今的犯罪次数(原注:实际数字莫大)、未检举而终者与偶尔被检 举者之数的比较等,不能不加考虑。另外,纯粹从理论上说,奸淫,在当时的情势下, 并不能断言全部都是刑法一七八条所谓乘不能抗拒者,不能不考虑也有容易接受要求者 。由此而言,如有奸淫的事实立即断为强奸,未免草率。应对犯罪当时的情况深加参酌 ,再决定处理。故没有立即答应同中佐的要求。
又,同中佐忧虑今后战斗休止,[强奸]增加,会影响宣抚工作。本人以为或如此。但 另一方面,慰安设施若能建立,应可防止增加。再则,人在战争中抛掷生命,接触妇女 犹如直面一大冲动线的最后一项,所以休战而会增加的忧虑是不必的。(注: ,第127—128页。)
,第127—128页。)
上砂胜七宪兵队长曾在《宪兵三十一年》(注:上砂胜七著《宪兵三十一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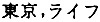 社1955年4月10日第1版。)中说到第十军军风纪的败坏,日本有些老兵一直不 以为然,以为是谎言,如第十军参谋吉永朴少佐说:“上砂氏这样的论述让人遗憾之至 ”(注:
社1955年4月10日第1版。)中说到第十军军风纪的败坏,日本有些老兵一直不 以为然,以为是谎言,如第十军参谋吉永朴少佐说:“上砂氏这样的论述让人遗憾之至 ”(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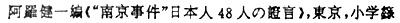 2002年1月1日第1版,第164页。)。上引有关上砂本人的记载,最可见 上砂回忆的不可诬毁。
2002年1月1日第1版,第164页。)。上引有关上砂本人的记载,最可见 上砂回忆的不可诬毁。
当时因不起诉而引起宪兵不满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上砂至法务部次日(26日),松冈宪 兵大尉又对某少佐不起诉表示不满:
不追究干部,不公平,如果队长不加以适当处置,自己今后对士兵的事件将不检举。( 注: ,第129页。)
,第129页。)
小川对法务部被冷落心中不忿,日记屡有记载,面对宪兵的不满,小川又强作解人。 不论小川是否真心以为强奸也许是“奸淫”,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他能取的惟一态度。 早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已可见他在这方面的两难:
自己的工作,如事件少空闲的话,其他人会认为法务部无用而轻视其存在。而如果事 件多,忙碌的话,至少会使相关方面不高兴。毋宁说过于认真的话不能不受到批判。( 注: ,第85页。)
,第85页。)
而在上砂对强奸不起诉表示不满之前两日,日记还留下了一条不见于日志的重要“方 针”(23日):
对强奸事件,采取只对迄今最恶性案件提起公诉的方针,处分取消极立场。如同类事 件继续频繁发生,则多少不能不再考虑。(注: ,第125页。)
,第125页。)
这一方针是出自长官的决定,还是由小川或法务部“审时度势”的自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日军军法系统对暴行确有明确的放任方针。(即使这一方针与小川 无关,小川在感情上与“消极”“处分”的“立场”也不会抵触,因为虽然他对日军犯 罪多有感叹,但那只是恨铁不成钢的惋惜。从小川称日军官兵的罪行为“九仞之功一篑 之亏”(注: ,第179页。)看,他对犯罪官兵确是深致同情的。)
,第179页。)看,他对犯罪官兵确是深致同情的。)
九,从日记所载宪兵对顺从的中国民众的驱使可见执法的宪兵并不依法,复可见日军 镇压的藉口完全不能成立
宪兵当时对日军的约束力实甚有限,但对中国人的处罚却毫不宽假,12月2日日记记:
在湖州,以许多支那人为杂役。今日从二楼的窗看,五六十名支那人,为了某项使役 ,由宪兵率领赴他处,前面的人举着太阳旗,后面列队跟着,内心不知道,但从表面看 ,看不出任何不服的样子。唯唯诺诺的按照率领者的意志行动。万一显出不服从的样子 ,我想就立即枪杀。(注: ,第84页。)
,第84页。)
小川此处说“我想”如只是凭空推断,就他的特殊身份加上身临其境,与实际情况大 概也是虽不中亦不远。但小川这样推断其实确有根据。就在前一日(12月1日)中支那方 面军刚刚通过了军律和军罚令,其中明确规定:“为了以军律保护帝国军的利益”“对 帝国臣民以外的人民可以直接适当处分”。“直接适当处分”是小川的概括,军律原文 有冠冕堂皇的所谓“叛逆行为”“间谍行为”“危害帝国军安宁,妨害其军事行动”等 限制。小川在私下不举理由,迳记直接“处分”(依十军有关部门《关于制定军律的意 见》,上述行为之“处分”该当“重罚”和“死刑”(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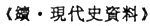 6,第196页。)), 表明的应是律令的实质。
6,第196页。)), 表明的应是律令的实质。
日本至今仍有人称日军对中国民众的“处分”,出于中国民众对日军的“袭扰”。但 日军所过之处,中国民众一如湖州的民众,表现得相当“顺从”,这是战争之初江南地 区的普遍情形。小川对此也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如11月23日记金山民众:
来金山,当地支那居民样子像菩萨,实在顺从,对我们小心的敬礼。特别是孩子,以 不动的姿势表示最尊敬的态度,让人不能不生出悯然之情。
11月28日记:
本日在市内(嘉兴)徘徊,小孩的亲切莞尔,让人觉得任何地方不论说什么小孩都是可 爱的。大人小孩都举着太阳旗,各家也都插着太阳旗。其中也有以白纸中间贴着方的红 纸代替太阳旗的。
11月29日记:
支那民众原来即顺从、质朴和勤勉。
12月27日记:
支那人的多数都很高兴,这样的样子似乎对凡事都毫不介意。败给了日本,仍和许多 日本兵混杂在一起,让人感到支那人丝毫不抱有敌忾心。作为日本人到底难以想象。
38年元旦小川访问灵隐寺,当日日记除了对庙宇的宏伟和僧人的虔诚的赞叹,还记有 :
辞行之际,得赠灵隐寺志八册一部,内附有昭和天皇万岁的寿文。(注: ,第 54、76、79、130、141页。)
,第 54、76、79、130、141页。)
中国民众的“顺从”,国内学者多以为是“消极现象”,有些人说是所谓“民族性格 ”中的“弱点”(注:如徐立刚《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及中国军人中消极现象分析》,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第1版,第130—145页。)。我以为忍辱负重,以低调自保减少无谓牺牲,不足为怪,更 不足以责。不仅忍辱负重不足以责,即使如小川所见“丝毫不抱敌忾心”,也不必深责 。在本国政府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国民时尤其如此。只要不越过“卖友求荣”的底线, 求生本是最正当的理由。这一问题涉及中国的节烈观与人的基本权利,非三言两语可以 尽其详,是故此处不拟展开。总之,即便依完全以镇压为目的的中支军律、令,“显出 不服从的样子”“就立即枪杀”,也是全然没有凭藉的。
日军侵华的日方原始文献,特别是战争初起时的公私文献,已十不存一,所以每一件 的发现,都或可补史文之缺,因此都值得细细研读。在日方否定派喧嚣日益高涨的今天 尤其如此。本文所胪列的数点,只是我在阅读小川日记中的随手所记,不敢妄称已充分 发掘了其中价值,但即便如此,已良有所获,所以,向学界推介,自以为可以不算贸然 。^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4年01期第92~105页
【作者简介】程兆奇,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 【内容提要】 | 从东京审判的被告方证人,到今天日本的虚构派,都矢口否认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这种与事实完全悖离的论调,由于日方文献在战后遭到有组织的焚毁,缺乏来自内部 的有力否证,至今对海外不知情的第三者、尤其是日本民众仍有影响。小川关治郎作为 攻占南京和江南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第十军的法务部长,他的日记重见天日,为我们从 多方面认识日军的真实表现,驳斥日本虚构派的妄说,以至于辨明小川自己在东京审判 时所作的证词为伪证,都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
日本战败后和东京审判前两次焚毁大量文书档案,给复原相关历史带来了困难。这不 仅是致力于究明战时日军暴行的日本学者的感叹,持否定日军暴行的论者也如是观。如 持温和否定观点的松本健一(丽泽大学教授)说:因为尚存的“关于日本军南京战役的正 式记录太少,使得蹈袭中国主张——没有具体统计和资料支撑的三十万人说——的洞先 生(指洞富雄,已故日本大屠杀派第一人——引者)的二十万人说得以登场和独步。”(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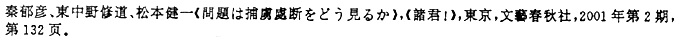 )。这也是本人近年为回应日本虚构派而搜寻日方文献时的突出体会 。所以去年末去东京访书,当看到出版已两年的日军第十军(攻占南京和江南的主力部 队之一)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时,不仅意外,也颇悔自己搜寻不细(因日记出版后 曾多次去找书)。
)。这也是本人近年为回应日本虚构派而搜寻日方文献时的突出体会 。所以去年末去东京访书,当看到出版已两年的日军第十军(攻占南京和江南的主力部 队之一)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时,不仅意外,也颇悔自己搜寻不细(因日记出版后 曾多次去找书)。小川日记珍藏到今日,长期不为人所知,连与他晚年一同生活的女儿都感到“吃惊” 、“完全没有记忆”(注:
 )。日记起自1937年10月12日“第七号军(即第 十军)动员令下达”,讫于1938年2月21日小川随中支那方面军(注:国内多将中支那方 面军译为“华中方面军”,因考虑到日本所称“中支”与我国的“华中”无论在传统所 指自然地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指行政区划上都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而中支那 方面军的活动范围也始终未逾今天通常所指的华东以外,所以本文一仍日本旧称。国内 译名避免“支那”是因为以为“支那”是蔑称,如《“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中译本 第一页第一条注释称:“支那为日本对战前中国的蔑称。《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仍 沿用了这一称呼,表明了笔者的反华立场。为了客观反映该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译者 未加任何改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原著无“大”字,“南京屠杀”加引号 ,因为日本虚构派不承认“屠杀”,故称屠杀必加引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 “内部发行”版,第1页。)日本今天仍坚持以“支那”称中国者,一定是右翼,但援用 历史名称,如“中支那方面军”时,则不论左、右翼都不加改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 将一行坐船离沪,其中11月7日小川在金山登陆后所记均为中国见闻,对认识第十军在 华数月的活动,尤其是日军“军风纪”,有重要价值。因为小川为当时日军最资深的军 法官,他的个人经历与本文主题有一定关系,所以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勾勒小川其 人,下篇举证说明此书之价值。下篇为本文重点。
)。日记起自1937年10月12日“第七号军(即第 十军)动员令下达”,讫于1938年2月21日小川随中支那方面军(注:国内多将中支那方 面军译为“华中方面军”,因考虑到日本所称“中支”与我国的“华中”无论在传统所 指自然地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指行政区划上都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而中支那 方面军的活动范围也始终未逾今天通常所指的华东以外,所以本文一仍日本旧称。国内 译名避免“支那”是因为以为“支那”是蔑称,如《“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中译本 第一页第一条注释称:“支那为日本对战前中国的蔑称。《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仍 沿用了这一称呼,表明了笔者的反华立场。为了客观反映该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译者 未加任何改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原著无“大”字,“南京屠杀”加引号 ,因为日本虚构派不承认“屠杀”,故称屠杀必加引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 “内部发行”版,第1页。)日本今天仍坚持以“支那”称中国者,一定是右翼,但援用 历史名称,如“中支那方面军”时,则不论左、右翼都不加改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 将一行坐船离沪,其中11月7日小川在金山登陆后所记均为中国见闻,对认识第十军在 华数月的活动,尤其是日军“军风纪”,有重要价值。因为小川为当时日军最资深的军 法官,他的个人经历与本文主题有一定关系,所以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勾勒小川其 人,下篇举证说明此书之价值。下篇为本文重点。上篇:日军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其人
小川关治郎,1875年(明治八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海东郡木折村(现海部郡美和町大字 木折字宫越五)。1898年进入明治法律学校(现明治大学),1904年被司法省任命为见习 检察官,1906年为预备法官,1907年被陆军省任命为第十六师团法务部员。以后转任多 职。1937年10月第十军组建时任法务部长,次年1月迁属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3月晋为 高等官一等(军事高等官最高级别,相当于中将),同月致仕。战后曾任民事调停委员等 职,卒于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小川在大正末期和昭和前期参加过许多重大案件审判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甘粕事件”(又称“大杉事件”)、“相泽事件”和“2·26事件 ”的审判。这三起“事件”的共同点是肇事者都是极右翼军人(注:“右翼”只是笼统 说法。“相泽事件”和“2·26事件”中的“皇道派”军人一方面视天皇为“万世一神 ”,主张“在天皇陛下统御下,举国一体,完成八纮一宇”,实际是进一步推动日本的军国化,这可以说是右翼;一方面痛恨贫富悬殊和上层社会的腐化,致力于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元老重臣、财阀军阀,以改造社会,这又难以用通常所说的右翼来概 括。),在当时极端民族主义的时潮中,这些案犯反而成了得时誉的“英雄”(注:时至 今日日本仍有人如此看。如七十年代日本以“2·26事件”为题材拍摄的《动乱》,便 完全站在肇事军人的立场上,将皇道派描绘成救国救民不惜舍身的志士。影片还穿插了 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由日本极负人望的高仓健、吉永小百合主演,悲恸凄绝,不能不 让日本观众一洒同情之泪。),所以这类逆风审判对审判者多少都是一个考验。
“甘粕事件”发生于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6日,当晚东京宪兵队涉谷分队长兼麴町 分队长甘粕正彦大尉率人杀害社会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妻和大杉年幼的外甥。虽 然案发后甘粕自供杀害大杉只是“个人行为”,但案发时能动用宪兵队的两辆汽车,杀 害地点又在宪兵队本部,尸体也隐藏于宪兵队之内,加上甘粕的宪兵分队长身份,这些 迹象都不能不让人感到“个人”身后的组织背景。而这正是军方所要推脱和掩饰的。所 以作为军法官的小川在审判中的严厉追究,不仅显得不合时宜,也打乱了军方的意图。 因此第一次开庭后,小川便因“辩护方要求避忌”被军方撤换。辩护方称小川与被害人 是“同乡兼远亲”。这一子虚乌有的理由瞒不过任何人,所以时人讽刺说:小川是“大 杉君的妹妹的先生的哥哥的妻子的妹夫的表兄弟的寄养家的孙子”(注:
 ) 。在军方的意志下,甘粕仅被判刑十年,而且仅仅三年即提前出狱,后来成了日本在海 外占领地最重要的宣传机构“满映”的理事长。
) 。在军方的意志下,甘粕仅被判刑十年,而且仅仅三年即提前出狱,后来成了日本在海 外占领地最重要的宣传机构“满映”的理事长。“相泽事件”是“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刺杀“统制派”中坚人物陆军省军务局 长永田铁山少将的事件,事发于1935年8月12日,其背后涉及了日本陆军内部复杂的派 系斗争。此事也成了次年2月26日军事政变的预演。“2·26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 大的政变,许多重臣被杀,给日本政、军界造成了巨大震荡。此事今天在日本仍家喻户 晓。小川参加了两案审理,对直接肇事者的审判无须多述,值得注意的是对被疑为“2 ·26事件”幕后黑手的真崎甚三郎大将的审判。真崎曾任陆军教育总监,教育总监的基 准军衔为大将,与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相同,位份很高。前一年7月15日转为闲职军事 参议官,这是导致“相泽事件”的直接起因。(真崎去职和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元帅的 坚主关系最大,但皇道派认为是统制派作梗。)真崎早在大正末出长士官学校时已开始 在青年军官中收揽人心,直至事变前仍与皇道派频有交往,所以事变后也以涉案者收审 。真崎对事变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至今扑朔迷离。真崎在临终前一年曾有一自述,为自 己撇清,称:
我并没有世间所想象的与“2·26事件”的关系,毋宁说,到事件突发为止,对这一无 谋的计划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对我来说,听到那天早晨突发事件的报道,犹如晴天霹雳 。然而这一布置周密的突发事件背后是真崎的宣传,不仅世间,宫中也确信不疑。
对他(指真崎——引者)历时一年三个月的军法会议,彻底调查,什么事也没有。
如果有一点关系的话,我决不能得救。今天没有复述全部调查的必要,但因为青年军 官如此拥戴真崎,当时的当局因此深疑被拥戴的真崎多少有所牵连。这个调查费时约半 年,直至世界法制史上所未有的推迟执行死刑,将三人作为证人,想通过延长时间来取 得有关真崎的证据,然而,没有的东西是怎么样都不会出现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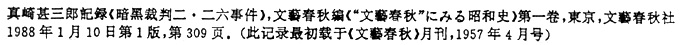 )
)虽说此事至今仍是一个疑团,但真崎所谓如有关系“决不能得救”却有悖事实。因为 近年已有证据证明,真崎“无罪释放”实出日本军方的政治考虑。据晚近发现的松木直 亮大将的日记,松木和矶村年大将、小川关治郎军法官三位真崎案的法官,对案件持三 种态度。松木认为真崎有“野心”和“策谋”;小川认为不仅是“野心”和“策谋”, 在事发时真崎还有“对反乱者好意的言动”(此点若成立,即可定真崎“利敌罪”);矶 村则认为真崎没有“野心”和“策谋”。三人各执己见,尤其是矶村和小川的对立,发 展到了不欢而散的地步。最终矶村以疾病为由提出辞呈,导致“异例”的军法会议解散 (37年9月3日日记)。最后由陆军省法务局长大山文雄等出面“说服”小川,又“将公判 审理改为多数决定”(9月14日日记),复由陆军当局对小川所拟判决书进行删削,才使 真崎得以免罪释放。(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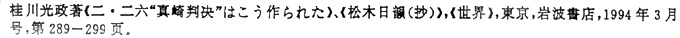 )对此,小川直至晚年仍未释然。(注:小川去 世前为小川作过一次诊断的医师增山隆雄说,在这唯一一次的接触中,小川说“真崎真 是个坏蛋”,因此让他“不能忘怀”。(
)对此,小川直至晚年仍未释然。(注:小川去 世前为小川作过一次诊断的医师增山隆雄说,在这唯一一次的接触中,小川说“真崎真 是个坏蛋”,因此让他“不能忘怀”。( 附录,第226页)对初次见面者这样说 ,可见此事在小川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附录,第226页)对初次见面者这样说 ,可见此事在小川心目中的分量之重。)此类案件的是非曲折,无须由我们来裁断,小川在真崎案中的立场确实也有“道德” 的因素在(小川向其女儿说过真崎不仅毫无担当,而且卑怯无耻,所以极其鄙视其人格) ,但从主要方面说小川还是一个严格依律行事的军法官。作为第十军法务部长,不论小 川在日军中是不是特例,说明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日军军法官和小川日记都会有一定的 帮助。
下篇:《一个军法务官日记》的史料价值
战时日军各部队都有日志,其中法务部日志是反映日军暴行——包括杀人、放火、抢 劫、强奸的最重要文献。这不仅因为它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因为日军军法会议对日军暴 行的认定总是十分“矜持”,决不肯让自己平添嫌疑,所以这种肇事方的“不打自招” ,反映的虽然只是事实下限,但作为证据却最为坚实,最不可动摇。所以,也是赖小川 得以保留的侵华日军仅存的第十军法务部日志(1937年10月12日—38年2月23日,下简为 “日志甲”)和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38年1月4日—31日,下简为“日志乙”)意 义确实非同一般。有关于此,我在拙文《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已 有详论(注:在我的有限阅读中,中、日两国学者对日志和日记迄今都未加援用。拙文 将刊于北京《近代史研究》。)。最近复将记、志加以比勘,发现虽然所记内容颇有重 复、时间几乎一致(日记仅比日志甲少了一天),小川日记仍有重要的补苴罅漏的价值。 以下摭拾数例以为证明。
一,从日记所记周继棠等被处决案可见日军对中、日两方受审者的量刑极不公平,也 可疑今刊日志已遭删节
日志乙在1月27日“发送法务局长书类”中有一条“审判请求之件报告”,括注中有“ 周△△六名”一语。因日志乙既无“犯罪事实概要”(两志所记各案均有此项)和判文, 志末所附“处理事件概要通报”亦无相关记载,而日志甲也没有丝毫踪迹可循,遂使此 事成了一个悬疑。我曾留意当时各种记录,终未得解,一直觉得是个遗憾。不意小川日 记却在多处留下了记录。1月28日记周等六人审判、处决情况如下:
午前9时审判周继棠等六名违反军律事件。其中首领周继棠作为第二区队长,原来为流 氓,即无赖、侠客,以前所辖有五百人,一见即较他人沉稳。约1时审理结束,立即准 备执行。5时执行。自己作为检察官出席审判,又作为执行指挥让宪兵执行。犯人在审 判时对自己不利之点极力否认,但在执行时却没有任何恶态。进入刑场时极其沉着,毫 无畏惧,一言不发。没有任何障碍便结束了。(中略)犯人姓名(原注:数字为年龄):周 继棠(34)、方家全(28)、杨光珺(21)、徐祥庆(17)、张满棍(23)、顾传云(30)、陈坤林(29)。(注:
 ,第170—171页。)
,第170—171页。)周继棠等所犯“罪行”,此日日记未记。从24日、26日日记看,周等被断罪当是以游 击队之名。24日记:
整日调查周继棠等六名违反军律事件文件。由不良青年纠合的别动队,依所谓游击战 术,以搅乱日本军后方为目的,在上海战役时进行了频繁活动。南京陷落后几乎都向广 东方向避遁(原文如此——引者),仅有少量残党仍进行地下活动。大部分为无赖(原注 :流氓),加入毋宁是生活困难所迫。
26日记:
作成周继棠等六名违反军律事件论告要旨。结论为:“被告等多数相结为党,属于对 帝国军加以危害的不逞集团。他们的行为不仅对帝国军队的危害甚大,对帝国所期待的 东洋和平亦是阻碍。因此,无庸置疑,绝对应扑灭此等极恶分子。故以严厉制裁,全部 应给以最重的处罚。”(注:
 ,第163—164、167—168页。)
,第163—164、167—168页。)此案审理过程的详情,如被告究竟具体犯了什么“罪”,为自己做了怎样的辩护,处 罚根据的是什么条文,今天已无从知晓。但通过上引可以看到:军律会议(注:“军律 会议”受理占领地军民案件,与“军法会议”实为一套人马。)在开审前已决定“给以 最重的处罚”,审判不过是个走过场的形式;而且从开庭到判决,从判决到执行,仅仅 一日,这个形式走得也很不象样。日本不少人每每说日军对中国军民的处决(指战场以 外)都经过军律会议的审判,言下之意都有“合法”根据,周案告诉我们,这种“审判 ”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不仅如此,如果比较至今仍为不少日本人强调的经过军法会议 处罚的日军案件(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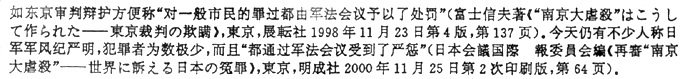 ),在徒有其名之上,更可以看到这种审判没有丝毫 公正可言。
),在徒有其名之上,更可以看到这种审判没有丝毫 公正可言。在第十军和中支军军法会议所受理的所有日军烧杀抢掠强奸等案件中,处罚最重者仅 为惩役四年(注:另有六年一例、五年两例为“以兵器胁迫长官”和“敌前逃亡、毁弃 军用品”等“反噬”案件。),许多蓄意杀人、强奸都被免于起诉。如后备山炮兵第一 中队一等兵辻某(因虑“名誉”,志、记出版时当事人姓名都仅留一字,下同)杀人案 :
被告人在嘉兴宿营中,昭和12年(1937年)11月29日午后约5时,因支那酒泥醉,在强烈 的敌忾心驱使下,生出憎恶,以所携带刺刀杀害三名通行中的支那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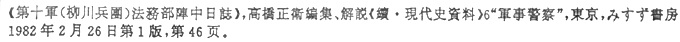 )。
)。此处“犯罪事实概要”中所谓“泥醉”和“敌忾心”其实是为宽大——日军军法会议 判决中的惯用套语叫做“情可悯谅”——留下伏笔。今天日本也许仍会有人以为“泥醉 ”是“理由”,但一,依历版陆军刑法,杀人所当都应是死刑、无期惩役刑和长期惩役 刑;二,杀三人应较杀一人更重;三,即使退一万步说,“情可悯谅”也有底线,重刑 不能减为轻刑,更不能免刑。然而,辻某无端杀害三人,最后却仍被军法会议以所谓 “三○一条告知”免于起诉。
再如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上等兵外某强奸案:
被告人昭和12年11月27日昼,赴枫泾镇征发粮秣之际,沿途看到支那女子(十五岁), 试图逃跑,生出恶心,逮住强奸(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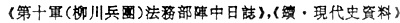 6,第47页。)。
6,第47页。)。外某“公务”在身,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谓恣肆之极,结果也被军法会议以“三 ○一条告知”开释,免于起诉。
不仅量刑的轻重完全不当,对嫌犯的调查也惟恐失之于“偏”。如后备上等兵植某杀 人,本有确据,仍由军医部早尾
 雄中尉(金泽医科大学教授)进行“精神”鉴定 。鉴定科目多达七类近三十项,如所谓“指南力”“领受力”“记铭力”(特指记忆新 事物力)“记忆力”“知识”“批判力”“妄想及幻觉”“观念联系”“胁迫观念”“ 感情”“意志”等等。植某的鉴定结论也十分烦琐,大约是饮酒过量,致“第一意识不 醒以前,受到第二意识(原注:极其原始的)发动的运动意识支配,因此误认事实,做出 不适合的行为”云云(注:
雄中尉(金泽医科大学教授)进行“精神”鉴定 。鉴定科目多达七类近三十项,如所谓“指南力”“领受力”“记铭力”(特指记忆新 事物力)“记忆力”“知识”“批判力”“妄想及幻觉”“观念联系”“胁迫观念”“ 感情”“意志”等等。植某的鉴定结论也十分烦琐,大约是饮酒过量,致“第一意识不 醒以前,受到第二意识(原注:极其原始的)发动的运动意识支配,因此误认事实,做出 不适合的行为”云云(注: ,第178页。)。如此繁复的检查,大概没有什么人 可得“正常”的结果。所以与其说是鉴定,不如说是为嫌犯开脱寻找理由。如此的调查 ,与对待周某等中国人的“斩立决”,真是有如天壤之别。
,第178页。)。如此繁复的检查,大概没有什么人 可得“正常”的结果。所以与其说是鉴定,不如说是为嫌犯开脱寻找理由。如此的调查 ,与对待周某等中国人的“斩立决”,真是有如天壤之别。周继棠等人的具体案情不得而知,但没有造成日军人员财产损失则几乎可以肯定(如李 新民、陆丹书等投掷土制手榴弹案,日军未受伤害,仍有详细记录,若对日军造成危害 ,不会没有记录)。所以对周继棠等的严苛和对辻某等的轻纵,说明日军军律会议虽有 审判的外衣,实质则只是镇压;即使不论“法”本身的问题,审判也只是与公正全然无 关的枉法。
这样的“审判”以战后的价值是没有袒护余地的,因此我疑日志不见周案详情,是出 版方或小川本人有意隐瞒,做了手脚。因为一,就一次枪毙六人而言,周案在中支军( 第十军亦如此)军法会议(包括军律会议)所有案件中为最重大刑案(注:仅就判决结果说 。就案情说,则第十军后备步兵第四大队少尉吉某等一次无端枪杀二十六名金山平民为 最大罪案,但此案肇事者全部被免于起诉。),日志绝无不加记载的任何理由。二,以 记、志所载各案相比较,日记有而日志无者,只有周继棠、陆丹书两案,其中在日志乙 范围内(1月31日讫)的仅有周案。三,日记1月28日所记限于周案审判和处决,28日军法 (军律)会议似应没有其他活动,是以日志乙此日全缺,当为删除周案后已无它事可留; 换言之,以周案以外的其他记载未能保留作为否定日志乙缺28日事出它故的理由并不存 在。四,陆丹书之处决在2月6日,逾出日志乙讫日,本可不论,但日志乙附有讫日之后 的判决书,如晚于陆案判决的上海派遣军野战衣粮厂一等兵福某监守自盗案(与陆案同 日调查,10日判决),所以日志不见陆案痕迹,理由当与周案一样,是为了遮掩,因此 不载陆案也可以作为不载周案理由的又一证据。(李新民案得以保存,因为李被判死刑 后越狱逃脱。)凡此应可证明,为了掩盖军律会议对中国人的不当重判,今刊日志经过 了删节。
二,从日记与日志的异文可见日志对事实的损益和日记的重要价值
日记在内容上与日志多有重合,但因是私下记录,较少利益考虑,不象日志那样严守 分寸,多有可以补充日志的真消息。在此谨举三例为证。
第十军作战部队11月5日登陆后,占领金山城等地基本没有遇到抵抗,但仍不断进行烧 杀抢掠。(战斗艰难、伤亡惨重激发出的报复心是造成日军暴行的原因之一,现在已成 普遍看法(注:这一看法在日本由来已久,不少当事人也供认不讳,如第六十五联队第 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位下士官称:“真是很惨重,都是‘为国’而战死的。希望把进攻 南京看作是这场激战(上海战役)的延长。俘虏来投降,便轻易地释放的气氛完全没有。 是受到那样伤害的战友的仇啊。这样的心情,我想让那时战斗的中国士兵们明白。假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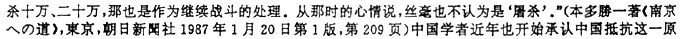 因,如称:“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也加剧了日本侵略军 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后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 保卫战的进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孙宅 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页)不过,此处所指 “抵抗”与日本所指不尽相同,日本指的是淞沪战役,而非“南京保卫战”。就当时实 际而言,日军进攻南京受到的抵抗远不及上海激烈,如上海打了近三个月,而南京不足 一周,日军的伤亡也仅是上海的数十分之一。如果将南京的“英勇抵抗”作为“基本原 因之一”,不免会留下一个疑问:日军的“暴行”为什么不是在上海更“残忍、疯狂” 。),而第十军在中国数月,没有遇到激烈抵抗,也没有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那样的 重大伤亡,除了与上海派遣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占南京,以后几乎已无战事,如占领杭 州时不费一枪一弹的“无血入城”。所以第十军的表现更能反映常态下的日军性格。) 第十军法务部7、8两日在金山登陆,次日(9日)日志甲记:
因,如称:“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也加剧了日本侵略军 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后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 保卫战的进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孙宅 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页)不过,此处所指 “抵抗”与日本所指不尽相同,日本指的是淞沪战役,而非“南京保卫战”。就当时实 际而言,日军进攻南京受到的抵抗远不及上海激烈,如上海打了近三个月,而南京不足 一周,日军的伤亡也仅是上海的数十分之一。如果将南京的“英勇抵抗”作为“基本原 因之一”,不免会留下一个疑问:日军的“暴行”为什么不是在上海更“残忍、疯狂” 。),而第十军在中国数月,没有遇到激烈抵抗,也没有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那样的 重大伤亡,除了与上海派遣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占南京,以后几乎已无战事,如占领杭 州时不费一枪一弹的“无血入城”。所以第十军的表现更能反映常态下的日军性格。) 第十军法务部7、8两日在金山登陆,次日(9日)日志甲记:午后3时军宪兵队长上砂中佐就金山卫城(今金山卫镇——引者)附近掠夺暴行等军纪弛 缓的情况与小川部长联系。(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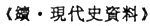 6,第29页。)
6,第29页。)小川日记同日记:
午后据视察了金山卫城的宪兵队长上砂说,同城附近掠夺十分严重,无益的杀伤惨不 忍睹。(注:
 ,第18页。)
,第18页。)不仅日记的“十分严重”在程度上显然更甚,“无益的杀伤惨不忍睹”也为日志失载 。而此处所引是小川本人得到的报告,所记自当更为可信。上引本来算不上重大区别, 可以不论,但近年日本虚构派在否认日军暴行中,常常抓住史文中的这种差别大做文章 。比如事发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的石射猪太郎曾在《外交官的一生》中说:
跟随我军回到南京的福井领事的电信报告和随即上海领事发来的书面报告,让人慨叹 。因为进入南京的日本军有对中国人掠夺、强奸、放火、屠杀的情报。(注:石射猪太 郎著
 太平出版社1974年4月15日第4次印刷版,第267页。)
太平出版社1974年4月15日第4次印刷版,第267页。)这条回忆一直被作为日本高层在南京暴行事发第一时间已经知情的证据。但因石射在 东京审判回答伊藤清律师有关石射庭证(第3287号)中说到“残暴”(Atrocities)的具体 所指时,没有提及“屠杀”二字(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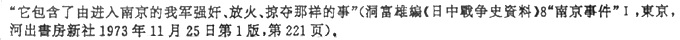 ),虚构派便抓住这一枝节的出入, 视为重大差别,声称当时实无“屠杀”(注:
),虚构派便抓住这一枝节的出入, 视为重大差别,声称当时实无“屠杀”(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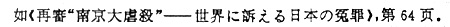 )。近又有人以石射日记未记“屠 杀”(注:
)。近又有人以石射日记未记“屠 杀”(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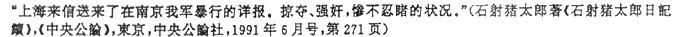 ),“证明”“原来没有‘屠杀’”(注:
),“证明”“原来没有‘屠杀’”(注: 社2002年9月 16日第1版,第179页。)。有关此事辨析,拙文(注:《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 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169—208页。)已详,此处不另。在这样的两方 相争的背景下,小川所记和日志的看似平常的差别,实有重要的意义。以上为第一例。
社2002年9月 16日第1版,第179页。)。有关此事辨析,拙文(注:《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 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169—208页。)已详,此处不另。在这样的两方 相争的背景下,小川所记和日志的看似平常的差别,实有重要的意义。以上为第一例。例二。日志甲10日记:
村落并无荒废之迹,但村落内约十处房屋被烧毁,此为敌之兵燹所致。(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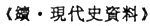 6,第30页。)
6,第30页。)日记10日记:
午后在附近视察,火灾之迹各处散见,或云是便衣队放火后逃跑,或云是日本军的行 为,真伪不明,相当惨烈。(注:
 ,第19页。)
,第19页。)“并无”和“各处散见”不同;“或云”虽不确定,比日志的断言,却是较可信的态 度。以后日记更有“真伪不明”事项得到澄清的记录,下将略及。
例三。日志甲11月18日记录军司令部会议中说到军风纪糟糕时,有“为了肃正军纪即 使有牺牲者也不得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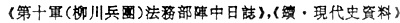 6,第37页。)之语。(“牺牲”二字并非故作危言 ,因为日军的骄兵悍将自恃卖命打仗有“功”,以为可享胡作非为的特权,并不把宪兵 放在眼里。)这确可说是“决心”的表现,但当天会议谈及此事时其实并不仅于此,小 川在当日日记中保留了日志“忽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内容与“牺牲”同条 而列之于前:
6,第37页。)之语。(“牺牲”二字并非故作危言 ,因为日军的骄兵悍将自恃卖命打仗有“功”,以为可享胡作非为的特权,并不把宪兵 放在眼里。)这确可说是“决心”的表现,但当天会议谈及此事时其实并不仅于此,小 川在当日日记中保留了日志“忽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内容与“牺牲”同条 而列之于前:第一线部队另当别论,后方部队应保持军纪。(注:
 ,第46页。)
,第46页。)这实在是不能遗漏的大关键,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日本左右两翼论及日军中央对军风 纪的告诫(12月28日),不论是以之证明日军对军风纪问题的“重视”,还是以之证明日 军军风纪问题的严重,所指都是12月末南京暴行发生、日本军政高层受到外界压力之后 。因此,我在此想慎重提出一个推断:虽然我们不能将小川所记“另当别论”简单地看 作鼓励犯罪,简单地与豁免权划等号,但在12月末之前,第十军——上海派遣军也可以 推想——对“第一线部队”应该有过“保持”军风纪可以缓行的明确表示。也就是说, 南京的骇人听闻的暴行,除了日军骄兵悍将“个人”的因素,日军“组织”也有推脱不 了的责任,这应该是一条有力的旁证。
上举日志对事实的损益之例,当非日军记录中的特例。如果这一推断不误,则日军事 发时留下的文献,就反映日军暴行而言,已经打了折扣。
三,从日记更正金山城劫掠之真凶可见事发时日方的记载确有偏见
小川日记之所以和日志比较仍别有自具的价值,和小川的客观态度也有很大关系。这 从下举之例中可以看出。11月15日日记中记:
在[金山]市内(今朱泾镇——引者)巡回,市的大部分成了废墟,这当是人为造成的。 偶尔看到烬余的房子,东西被劫后的散乱,难以名状。如大书店和药房,进去一看,其 内部的气派可以和三省堂(东京最大的书店之一——引者)匹敌,但不论是药还是书都破 损散乱了。其他所残存的店铺也无不如此。此等暴戾狼藉,当非日本兵所为。推测起来 不是支那败残兵的所为么?听说支那禁止将任何东西留给日本兵,如退却全部破坏烧毁 才逃跑,因此不论肝肤(原注:原文如此)尽可能的全部破坏烧毁。(注:
 ,第3 6页。)
,第3 6页。)小川这样推断,也许是误信传言,也许是对日军军纪估计过高,这也是不明真相的日 本人最容易接受的看法。这种偏见,即使有中国证人证明,往往也难以改变。所以小川 稍后告诉我们真凶的日记(17日)显得特别可贵:
风闻日本兵暴戾狼藉,多少有些疑问。今日军医部中佐作为前□(原文如此——引者) 者,说:10日到达金山,当时如某书店,即前记可与东京三省堂匹敌的那家,毫无被害 的痕迹,后来到同店一看,如前所记实在是凄惨暴戾狼藉之极,显然这决不是支那兵的 所为,而完全是日本兵的所为。实际确如所说,让人不胜惊骇。(注:
 ,第45 页。)
,第45 页。)10日后金山已是日军的天下,所以从“毫无被害的痕迹”一变而成为“凄惨”“狼藉 ”,只可能是日本兵的所为。这是一个可以举一反三的例子,当时日本的观察者,官兵 、记者、外交官等等,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日军的暴行总是宁信其无。小川日记的 特别价值就在于:它既是对所见所闻的照实而录,又是站在日军立场上的记录。所以它 所记录的“支那兵”的暴行虽不免为误传,但所记日军暴行则均应是有据的确证。
四,从日记所记日军犯罪和小川对日军犯罪的“痛恶”可证小川在东京审判时为辩护 方提供的证词为伪证
东京审判时许多参与侵华的辩护方证人都一口咬定日军在华军纪严明,没有暴行,不 仅对审判产生了影响(注:如松井石根虽然最终被判处最高量刑——绞刑的处罚,但所 罚只是消极的“不作为责任”,否认了公诉人提出的被告的“非法命令、授权、许可” 。),对以后长时间在日本学者以至民众认识上出现的“歧义”也有重要影响(注:详请 参拙文《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北京,《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 —57页;《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论著平议》之五,拙著《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 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0—354页。)。我在前面已说过,侵华日军的战时文书档案 大多已被焚毁,这是对这些“证言”证伪的最大困难(注:中、西方留下的证据,日本 相当多的人不予承认,认为它是战时“敌国”或助敌之国的宣传。如铃木明、北村稔、 东中野修道等分别“考证”出田伯烈(H.J.Timperley)、贝茨(M.S.Bates)等为中国顾问 ,中、西方的证据都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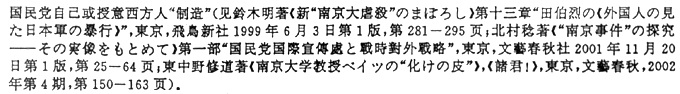 )。小川东京审判时也曾出庭,为日军作了无罪证 明。所以小川日记如能有相关记录,当可成为解明此事的一个突破口。小川在向远东军 事法庭提出的“宣誓供述书”(辩护方文书第2708号、法庭庭证第3400号)中这样说:
)。小川东京审判时也曾出庭,为日军作了无罪证 明。所以小川日记如能有相关记录,当可成为解明此事的一个突破口。小川在向远东军 事法庭提出的“宣誓供述书”(辩护方文书第2708号、法庭庭证第3400号)中这样说:没有听说日本军的不法行为,也没有不法事件被起诉之事。日本军是作战态势,军纪 很严肃。(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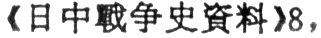 第256页。)
第256页。)小川的两个“没有”说得很肯定。这种证言出自法务部长之口,对不明真相的日本人 有特殊的分量。幸而小川日记仍存于世,使判别这一证言的真伪,有了最可靠的根据。 以下我们就来对小川日记做一检查,查一查他当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是不 是像他自己说的什么都“没有”。
前记小川登陆次日即得上砂胜七宪兵队长报告日军掠夺和杀戮,接着小川记:“担心 引起非常的问题”(注:
 ,第18页。)。以后小川所见日多,在日记中也每有感 慨。因为此事不仅关系小川一人的证言,对其他辩护人辩词也有比照的意义,所以在此 不妨较详援引。11月24日日记记:
,第18页。)。以后小川所见日多,在日记中也每有感 慨。因为此事不仅关系小川一人的证言,对其他辩护人辩词也有比照的意义,所以在此 不妨较详援引。11月24日日记记:所到之处恣意强奸,不以掠夺、放火为恶事,作为皇军,这实在是难以言表的可耻。 作为日本人,特别是应该成为日本中枢的青年男子,假使带着这样无所顾忌的心理风习 凯旋而归,对日本今后全体的思想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想到这一点,让人栗然。我想 日本政府当局应对此研究,对思想问题应加以根本的大改革。这是稍稍极端地说法。然 而如某人所说:日本兵比支那兵更残虐,这是作为日本人的我们不胜感慨的。听说支那 人将我们日本人称为猛兽,将日本兵称为兽兵,闻之使人战栗。从支那方面来看当然是 这样。作为我们,对日本兵的实际见闻不堪遗憾之例不遑枚举。(注:
 ,第59 页。)
,第59 页。)小川并不以“野兽”“兽兵”为诬枉,是因为“实际见闻不堪遗憾之例不遑枚举”, 所以作为职业军法官的他只能“不胜感慨”。
11月25日记:
昨夜3时半松冈宪兵大尉不拘深夜来报告重大事件。事件为第六师团五名士兵(内伍长 一名)在约三里(一日里约当近四公里——引者)的乡间劫持十几至二十六岁女子在某处 大空宅恣意强奸。而且,劫持之际枪杀逃跑的五十五岁女子,并射伤另一女大腿部。违 反军纪,不逞之极,让人无话可说。
△(日记原符号——引者)日本政府声明,今后以支那政府为敌,不以一般国民为敌。 然而,日本兵对没有任何罪过的良民的行为不逞之极,如何看待在这样行为之下的一般 支那国民的更进一步的抗日思想呢?为了日本帝国的将来计,让人不寒而栗。
(中略)看日本兵对支那人的使役,用枪对着,完全像对待猫狗,因为是支那人,完全 不抵抗。反过来,如果和日本人易位而处,会怎么样呢?(注:
 ,第62—63页。 )
,第62—63页。 )虐待军人,因战争的酷烈有时难以完全避免,但非人的对待“良民”,则再怎么退而 说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小川能将心比心,想到“易位而处”,既说明小川还有起 码的良知,更是由于日军表现“不逞之极”,使小川不能不受到震撼。
11月26日记:
从各方面的观察,不仅第一线部队,后方部队的狡狯之兵也故意落伍,进入民家干恶 事。如上记杀人、掠夺、强奸事件的被告人即是此类。结果,正直的、认真的士兵在第 一线英勇奋战,稍一疏忽即战死,狡狯的家伙恣意妄为,什么战斗也不参加,称作国贼 、反逆者、害群之马绝非过言。越发使人感慨。
(中略)他们一看到日本兵立即逃散,女子、小孩似对日本兵极其恐惧,这是日本兵所 做恶事造成的。如果什么恶事也没做,理当不会逃跑。真是使人非常遗憾。
皇军的脸面是什么呢?所谓战争,自己开始什么都不能判断,但上记支那人对日本人的 感情,日本兵素质今后对青年男子的影响,完全让人寒心。(注:
 ,第65—66 页。)
,第65—66 页。)(此日日记后记法务部成员田岛隆弌调查25日日记所记强奸杀人案,谓“听现场调查 状况,其恶劣超出想象”,而特别可注意者为此案中杀死三人、杀伤三人,而日志乙所 载正式案卷和判文仅为一死一伤。)中国民众对日军“极其恐慌”,由“日本兵所做恶 事造成”,“让人寒心”,单凭此日所记就足见小川的法庭证词全未据实。
11月29日记:
有的士兵让支那人背负行李,(中略)稍有不从或显出不从的样子,就立遭处罚,让人 无话可说。途中看到士兵二人拔出剑刺击一个仰向的支那人。又一个支那人沾满鲜血, 苦痛不堪。见及于此,感到战败国国民之可怜无以复加。(注:
 ,第78页。)
,第78页。)当时强征中国人随军服苦役的情况十分普遍,12月11日又记:
这些支那人拼着命背负行李,其中有相当的老人,没有比战败国良民更不幸了。这样 的场合,对我士兵稍有不从,立即处罚。万一逃跑,就在这一带立即处决。(注:
 ,第105页。)
,第105页。)行文至此,忆及前些年美国日侨为战时收容向美国政府索赔(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 曾将日本侨民集中监管,这一举措是由当时的特定背景决定的。作为一个敌对国,尤其 是一个以偷袭方式使自己蒙受巨大损失的敌对国,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已毫无信用可言。 因此,疑及日本侨民,采取防范措施,不仅十分自然,也有充分理由。但事过境迁,在 一个没有硝烟的时代,你死我活的环境已为人淡忘,圈居与现代立国理念的抵触却日益 突出。于是,在美日侨向美国政府控诉战时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要求美国政府道歉 赔偿,不仅得到日本朝野的一致支持,美国也不得不作出让步,给予赔偿。),在索赔 过程中,日本电视台数度播放难民营实景,作为所谓“不人道”待遇的证据。对照小川 所述及类似记录,日军加诸中国人的苦痛比起日侨所受的“迫害”真是何止百倍!
因为第十军登陆后并未受到激烈抵抗,所以第十军所过之处留下的尸体,必有相当部 分是此类随意“处决”的受害者。从金山登陆起,几乎每到一处,小川都会遇到中国人 的尸体。如11月14日上午往张堰镇途中,“河、潭、田中到处都是尸体”“尸体不计其 数”,下午到达金山时所见尸体中居然有的“全裸”(注:
 ,第27、30页。)。 11月17日在金山郊外,“今日仍有支那人尸体”(注:
,第27、30页。)。 11月17日在金山郊外,“今日仍有支那人尸体”(注: ,第44页。)。11月28日 在往湖州途中,看到“累累尸体”,其中相当部分穿着平民服装。12月10日小川记:“ 途中各地所见支那人尸体,不计其数”(注:
,第44页。)。11月28日 在往湖州途中,看到“累累尸体”,其中相当部分穿着平民服装。12月10日小川记:“ 途中各地所见支那人尸体,不计其数”(注: ,第102页。)。这样大量的尸体 使小川的感觉变得麻木,诚如他在12月11日日记中所说:
,第102页。)。这样大量的尸体 使小川的感觉变得麻木,诚如他在12月11日日记中所说:最初由李宅向金山进发途中看到支那人的尸体时,总有异常的感觉,但渐渐看到大量 的尸体,就习以为常了。此时的感觉就如在内地看到狗的遗骸一样。(注:
 , 第107页。)
, 第107页。)杀人,或者说抹杀中国人的生命权,是第十军在中国的最严重犯罪,其他“军风纪” 问题,直至中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的建制撤消,行将回国之前,同样也很 严重。如2月15日日记中有:
塚本法务官到,听取南京方面事件的状况。特别是接受了天野中尉强奸事 件的详细报告。(中略)各方面强奸事件频频发生,对之如何防止是应特别研究的问题。 (注:
 ,第192页。)
,第192页。)以上所见种种,都是驳斥小川在东京审判所说未闻日军犯罪的最有力证明。虽然,我 们不能将小川之例无限夸张,断言当时类似的证据都是有意作伪,但小川证词和日记的 相反记载,至少可以证明东京审判时与小川相同的那些证词不合实情。
五,从日记所记南京南门之中国军队尸体和大火可再驳日本老兵城内无尸体和火灾之 “证言”
日本旧军人团体偕行社所刊《偕行》(月刊),主要发表有关日军战史的文字,近三十 年来刊有不少参加南京战役的老兵的回忆,其中多有南京既无尸体,亦无火灾的“证言 ”。如亩本正己(日军攻克南京时为独立轻装甲车队的小队长)在《检证“拉贝日记”》 中所引伊庭益夫“没有尸体”,栗原直行“在扫荡区域内,既没有住民的人影,也没有 遗弃的尸体”(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土屋正治“在城内巡回,没有看到尸体”(注:附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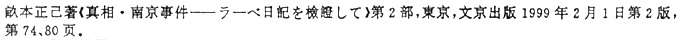 )等等。近年积极策动状告东史郎的森英生(日军攻占南京时为步兵第二十联 队第三中队中队长)说:
)等等。近年积极策动状告东史郎的森英生(日军攻占南京时为步兵第二十联 队第三中队中队长)说:我是第三中队的中队长,除了安排值日的警备外,自己也骑马在警戒区内巡查,但一 件非法的事件也没看到。巡查时是不进入安全区的,但如果发生违法和火灾,必须报告 上司,进行处置,但这样的事一次都没有发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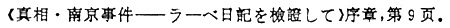 )
)上引为无据妄说,我已详征有关文献加以证明(注:拙文《对“检证‘拉贝日记’”的 检证》,北京,《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50—183页。此文所引之外的最重要 第一手证据,是日军支那方面舰队军医长泰山弘道大佐、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旅 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日记等文献,详见前引拙文,第100页注5。)。日记再一次证明 这些老兵证言的不实。
12月14日下午3时半,小川到达可见南京城墙之处,沿途中国军队尸体重叠(注:南京 留下的大量尸体的正身主要应是被屠杀的俘虏。详见拙文《日军屠杀令研究》,北京, 《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68—79页。),到处燃烧着大火,日军只能“跨过尸体前 进”。从“南门”进城后:
一进门就看见两侧的累累尸体。(中略)在屋上眺望,广泛的市街到处都是冲天的火焰 。确实是战争的光景。(注:
 ,第111—112页。)
,第111—112页。)15日巡视南京城内,“各处依然都是火灾,黑烟薰天”(注:
 ,第114页。)。
,第114页。)。这样的记录,绝非时隔数十年、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回忆所能推翻。如从方法论上说, 即使同为事发当时所见,除非拿出有意作伪的过硬证据,彼眼所见也只能补充而不能否 认此眼所见。小川日记再次告诉我们,晚近日本老兵那种不留余地的断言,并没有事实 的根据。
六,从日记所记自布烟幕的传说可证日军“误炸”英舰出自有意
日军在进攻南京过程中,为堵截中国军队撤退,海军第十三航空队飞机在南京上游长 江炸沉美国军舰Panay号及美孚石油公司船只三艘,第十军野战重炮兵第十三联队在芜 湖附近击伤英国军舰Ladybird号等二艘及商轮一艘。在当时引起了英、美两国的强烈抗 议,因日本迅即“陈谢”和赔偿,此事很快得以了结。但日本当时同时强调日军是“误 炸”,声称因为事发时上述军舰都放了烟幕,致使无法看清国旗。此事究竟,似乎已成 不解之谜。但小川日记12月22日所记却为解开这一疑团提供了一条线索:
窃闻即使有些事实无法判明,但桥本部队(第十三联队长为桥本欣五郎大佐——引者) 似乎是自布烟幕,然后炮击。(注:
 ,第125页。)
,第125页。)小川作为军的部长,他的“窃闻”应有相当根据。当时日军不择手段,掩人耳目,都 时或见之。而且,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向英、美道歉,第十军和中支军都表 示强烈反对。第十军“军司令部……要求取消广田外相的陈谢”(注:
 ,第125 页。),中支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则电报东京,表示“对责任者的处分绝对没有必要 ”(注:
,第125 页。),中支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则电报东京,表示“对责任者的处分绝对没有必要 ”(注: 偕行社1989年11月3日第1版,第18页。)。现地日军之所以反对日本政 府的“陈谢”,撇开包庇部下的一般理由,确实是因为不愿让作战受到规则的束缚。所 以,虽然从建制上看,日军对外有国际法顾问(中支军顾问为斋藤良卫法学博士)、对内 有军法会议,又有一系列可与不可的制度性规定,似乎是一支现代军队,但质之以实际 ,日军为了达到目的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罔顾国际法,不择手段的。日本左翼学者将日 本军队指为“前近代的”“野蛮的”军队(注:如津田道夫著(程兆奇、刘燕译)《南京 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第1版,第89页。),并非 苛责。
偕行社1989年11月3日第1版,第18页。)。现地日军之所以反对日本政 府的“陈谢”,撇开包庇部下的一般理由,确实是因为不愿让作战受到规则的束缚。所 以,虽然从建制上看,日军对外有国际法顾问(中支军顾问为斋藤良卫法学博士)、对内 有军法会议,又有一系列可与不可的制度性规定,似乎是一支现代军队,但质之以实际 ,日军为了达到目的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罔顾国际法,不择手段的。日本左翼学者将日 本军队指为“前近代的”“野蛮的”军队(注:如津田道夫著(程兆奇、刘燕译)《南京 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第1版,第89页。),并非 苛责。七,从日记对军部的抱怨可见日军决不愿意让法务部束缚日军战斗力
日军军法会议由法务部成员(职业军法务官)和所谓“带剑的法官”(军事人员)组成。 从理论上说,军法官与“带剑的法官”在职权上没有区别,所谓“作为专门法官,以其 专门的知识,努力使审判事务适正,但与所谓‘带剑的法官’的判士(法官——引者)在 职务权限上没有任何差别,在事实的认定、法令的解释上,全体法官具有同一的权能。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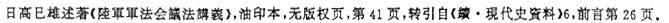 )然而正如《日本现代史资料·军事警察》编者所说:军法官“在兵科 军官 = ‘带剑的法官’的判士之下,也有只是充当无力的事务官的一面”(注:
)然而正如《日本现代史资料·军事警察》编者所说:军法官“在兵科 军官 = ‘带剑的法官’的判士之下,也有只是充当无力的事务官的一面”(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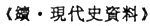 6,前言第27页。)。对此,小川女儿少时曾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体验。长森 (小川)光代说,她读小学时,因父亲军法官的领章和军帽帽圈的颜色特别(白色,当时 陆军是红色,骑兵是绿色,航空部队[时空军尚未成为独立军种]是兰色等),数量稀少 ,让人侧目,她的同学甚至问:“你父亲是支那兵么?”为此少女光代十分苦恼,想: “要是父亲是普通的军人多好,多神气,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注:
6,前言第27页。)。对此,小川女儿少时曾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体验。长森 (小川)光代说,她读小学时,因父亲军法官的领章和军帽帽圈的颜色特别(白色,当时 陆军是红色,骑兵是绿色,航空部队[时空军尚未成为独立军种]是兰色等),数量稀少 ,让人侧目,她的同学甚至问:“你父亲是支那兵么?”为此少女光代十分苦恼,想: “要是父亲是普通的军人多好,多神气,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注: )
)法务部不为各级部队、尤其是战地部队重视,可以想见。但如果没有当时的第一手材 料,要破除所谓日军军法会议功能完备、有效之说却也并不容易。小川日记出自最直接 的当事人之手,它的相关内容,不仅对法务部长一己的内心感受,对法务部的实际处境 ,都是最真实也最无可置疑的记录。
日军军法会议由军人参与,为的是所谓“审判权和军队指挥权的一致”,军法会议的 最终裁决权也因此掌握在但任军法会议长官的各级司令官手中。所以,作为承担日常事 务的法务部,不论是为了发挥高效机能,还仅仅是为了正常周转,都必须随时保持与司 令官的紧密联系。因为参谋部、副官部、管理部、兵器部、经理部、军医部、兽医部、 法务部以及通讯班等军部各部门本来即随司令官同行,所以除非刻意安排,法务部本来 就应在司令官左近。但从小川日记可见,副官部门屡屡试图将法务部从军部支开。对此 小川十分不满。如11月24日日记记:
明日应向嘉兴出发,突然不知什么理由要我们延期到后日,对此,我们提出抗议,理 由如下。
(中略)第二,军法会议事务一切仰司令官裁决,因此我们的事务离开司令官即无法执 行。如果司令官和我们的所在相分离而无法得到司令官的裁决,最应注重迅速的战地军 法会议的手续就会造成滞涉。现下羁属中的三名放火事件嫌犯,虽然检察官的调查已经 结束,但因未得司令官命令而无法提起公诉,事件的处置只能延迟。
此节栏外又有:
我们的职务无法独断专行。如果以为我们无用,则令人遗憾万千。(注:
 ,第 61—62页。)
,第 61—62页。)所谓“无用”,不是小川的无端疑心,因为法务部的不受重视以至于不受欢迎,从大 、小许多事情上都可以看出。举一件待遇方面的小事为例。12月10日第十军军部由湖州 向溧水进发,许多部长和副官坐飞机,小川被安排坐汽车。小川以为这是“歧视”,所 以在当日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愤慨”。这种情况和文官地位的普遍低下确实有关,小 川在12月12日日记中的如下记述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我们文官不得不受到这种歧视对待。(特别是军人的威势日益暴戾,极尽军人式的随心 所欲。原注:括号内原文被划除。)只是靠恩赐,也许因此还会受到某种妒忌,然而在 任何场合都一样,我们实际被当作累赘。(注:
 ,第109页。)
,第109页。)但对法务部的“歧视”还不仅仅是出于战争环境下武人对文官常有的蔑视,更是因为 法务部的功能与日军败坏的军风纪确有冲突。
小川日记12月8日记:“塚本部长万事消极,万事不为。”塚本是上海派遣军法务部长塚本浩次,“不为”和“消极”的原因,小川日记说是听说“内部欠融和”(注:
 ,第97页。)。然而,就当时的日军状况言,仅仅因人际关系便“万事不为”,实难想象。我以为之所以“不为”,应该和法务部工作难以展开有关。东京审判时不少日本军人提到各部队对法务部的抗议,理由是法务部处罚太严,其中便有塚本浩次。他说:“对于上海派遣军法务部处罚的严厉,对于细微之罪也纠明的态度,各部队都进行了非难。”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也说到,因为“军纪极其严正(依文意应指过严——引者),便有第十六师团向法务部提出抗议那样的事。”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也说他曾为部下鸣不平(注:
,第97页。)。然而,就当时的日军状况言,仅仅因人际关系便“万事不为”,实难想象。我以为之所以“不为”,应该和法务部工作难以展开有关。东京审判时不少日本军人提到各部队对法务部的抗议,理由是法务部处罚太严,其中便有塚本浩次。他说:“对于上海派遣军法务部处罚的严厉,对于细微之罪也纠明的态度,各部队都进行了非难。”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也说到,因为“军纪极其严正(依文意应指过严——引者),便有第十六师团向法务部提出抗议那样的事。”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也说他曾为部下鸣不平(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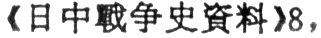 第191、252、239页。)。所谓“严厉”,从日志所载判例看完全是妄说,我们在以上“一”“量刑极不公平”中已提及,但即便重罪轻罚或不罚,法务部的性质仍决定了它不可能为日军骄兵悍将所接受。
第191、252、239页。)。所谓“严厉”,从日志所载判例看完全是妄说,我们在以上“一”“量刑极不公平”中已提及,但即便重罪轻罚或不罚,法务部的性质仍决定了它不可能为日军骄兵悍将所接受。塚本部长所说的“非难”,从小川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到。小川38年1月赴方面军(方面军未建立法务部,小川附属于司令部),他感到方面军与军的明显不同在于没有直辖部队,因而不必考虑“人情”:
(在军时)须考虑军对于部下的罪行有直接责任问题,也有对部下人情方面的相当意见 ,因此,我们对长官条陈意见时不能不战战兢兢的深加思考。(注:
 ,第149页 。)
,第149页 。)所谓“相当意见”,当就是塚本浩次所说的“各部队”的“非难”。
其实就当时情况看,对法务部门的不满,不仅仅是是基层部队。日记中有一条关于松 井石根的记载,颇值得注意。1月15日记:
司令官(原注:松井石根大将)是保持威严?还是生来的傲慢气质?和迄今接触过的大将 比,是有点奇怪的类型。长官不太端架子,能使自己的方针为下级理解,我以为这样才 好。完全没有必要那样的摆排场。过于端架子,未免不能让接触者所述的充分意见得到 考虑,因此,种种考虑也难以使上级了解。特别是长官和部下的关系,下者充分了解上 面的意见,上者充分研究下面的意见,倾听有意见者的意见决不是无益的……(省略号 为原文所有——引者)端架子的原因是什么呢?(注:
 ,第153—154页。)
,第153—154页。)有关松井其人,有各种描绘,如东京审判时冈田尚等日方证人所作的不实证词(注:冈 田所说之从无人置疑而实不可信,请参拙文《南京大屠杀札记》之八《松井石根有可诉 之冤么?——冈田尚辩词析》,上海,《史林》2003年第1期,第105—108页。),但从 没有人说过“傲慢”“端架子”。松井给小川的印象之所以与众不同,我以为原因在于 松井对维持军风纪的态度。表面上松井也多次谈及要注意军风纪,但一,军风纪之于松 井,分量甚轻,不仅不能影响作战,也不能处罚肇事者,如前引Ladybird号事件;二, 日本政、军高层迫于欧美强国压力要求中支军约束军风纪,使松井十分难堪,攻占“敌 国”首都的欢愉也因此一扫而光。中支军军法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拼凑,对松井而 言,当非出自本愿(从松井继任者畑俊六大将等日记看,松井之被解任多少与 军风纪败坏有关联)。所以,对年资相若并无过节的小川,松井一反常态的“傲慢”“ 端架子”,不论是真心流露还是故作姿态,所传达的都不外乎是对军风纪压力的强烈抵 触情绪。
八,从日记所记宪兵对不起诉之异议可再见日军军法会议确有徒具形式的一面
塚本浩次的“万事消极,万事不为”,事出迫不得已,已如上述。第十军 情况虽较上海派遣军为轻,但法务部处境仍可谓左右为难。所以许多案件到了法务部都 只能不了了之。因此引起了执法宪兵的不满。12月25日小川记:
上砂中佐来部商量事务。中佐曰:近期的强奸事件多不起诉,宪兵费力的检举,到头 来努力白费。本人答说:或许如此。但本人以为,战争中的情状、犯人当时的心理、支 那妇人的贞操观念、迄今的犯罪次数(原注:实际数字莫大)、未检举而终者与偶尔被检 举者之数的比较等,不能不加考虑。另外,纯粹从理论上说,奸淫,在当时的情势下, 并不能断言全部都是刑法一七八条所谓乘不能抗拒者,不能不考虑也有容易接受要求者 。由此而言,如有奸淫的事实立即断为强奸,未免草率。应对犯罪当时的情况深加参酌 ,再决定处理。故没有立即答应同中佐的要求。
又,同中佐忧虑今后战斗休止,[强奸]增加,会影响宣抚工作。本人以为或如此。但 另一方面,慰安设施若能建立,应可防止增加。再则,人在战争中抛掷生命,接触妇女 犹如直面一大冲动线的最后一项,所以休战而会增加的忧虑是不必的。(注:
 ,第127—128页。)
,第127—128页。)上砂胜七宪兵队长曾在《宪兵三十一年》(注:上砂胜七著《宪兵三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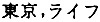 社1955年4月10日第1版。)中说到第十军军风纪的败坏,日本有些老兵一直不 以为然,以为是谎言,如第十军参谋吉永朴少佐说:“上砂氏这样的论述让人遗憾之至 ”(注:
社1955年4月10日第1版。)中说到第十军军风纪的败坏,日本有些老兵一直不 以为然,以为是谎言,如第十军参谋吉永朴少佐说:“上砂氏这样的论述让人遗憾之至 ”(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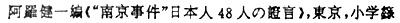 2002年1月1日第1版,第164页。)。上引有关上砂本人的记载,最可见 上砂回忆的不可诬毁。
2002年1月1日第1版,第164页。)。上引有关上砂本人的记载,最可见 上砂回忆的不可诬毁。当时因不起诉而引起宪兵不满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上砂至法务部次日(26日),松冈宪 兵大尉又对某少佐不起诉表示不满:
不追究干部,不公平,如果队长不加以适当处置,自己今后对士兵的事件将不检举。( 注:
 ,第129页。)
,第129页。)小川对法务部被冷落心中不忿,日记屡有记载,面对宪兵的不满,小川又强作解人。 不论小川是否真心以为强奸也许是“奸淫”,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他能取的惟一态度。 早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已可见他在这方面的两难:
自己的工作,如事件少空闲的话,其他人会认为法务部无用而轻视其存在。而如果事 件多,忙碌的话,至少会使相关方面不高兴。毋宁说过于认真的话不能不受到批判。( 注:
 ,第85页。)
,第85页。)而在上砂对强奸不起诉表示不满之前两日,日记还留下了一条不见于日志的重要“方 针”(23日):
对强奸事件,采取只对迄今最恶性案件提起公诉的方针,处分取消极立场。如同类事 件继续频繁发生,则多少不能不再考虑。(注:
 ,第125页。)
,第125页。)这一方针是出自长官的决定,还是由小川或法务部“审时度势”的自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日军军法系统对暴行确有明确的放任方针。(即使这一方针与小川 无关,小川在感情上与“消极”“处分”的“立场”也不会抵触,因为虽然他对日军犯 罪多有感叹,但那只是恨铁不成钢的惋惜。从小川称日军官兵的罪行为“九仞之功一篑 之亏”(注:
 ,第179页。)看,他对犯罪官兵确是深致同情的。)
,第179页。)看,他对犯罪官兵确是深致同情的。)九,从日记所载宪兵对顺从的中国民众的驱使可见执法的宪兵并不依法,复可见日军 镇压的藉口完全不能成立
宪兵当时对日军的约束力实甚有限,但对中国人的处罚却毫不宽假,12月2日日记记:
在湖州,以许多支那人为杂役。今日从二楼的窗看,五六十名支那人,为了某项使役 ,由宪兵率领赴他处,前面的人举着太阳旗,后面列队跟着,内心不知道,但从表面看 ,看不出任何不服的样子。唯唯诺诺的按照率领者的意志行动。万一显出不服从的样子 ,我想就立即枪杀。(注:
 ,第84页。)
,第84页。)小川此处说“我想”如只是凭空推断,就他的特殊身份加上身临其境,与实际情况大 概也是虽不中亦不远。但小川这样推断其实确有根据。就在前一日(12月1日)中支那方 面军刚刚通过了军律和军罚令,其中明确规定:“为了以军律保护帝国军的利益”“对 帝国臣民以外的人民可以直接适当处分”。“直接适当处分”是小川的概括,军律原文 有冠冕堂皇的所谓“叛逆行为”“间谍行为”“危害帝国军安宁,妨害其军事行动”等 限制。小川在私下不举理由,迳记直接“处分”(依十军有关部门《关于制定军律的意 见》,上述行为之“处分”该当“重罚”和“死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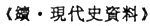 6,第196页。)), 表明的应是律令的实质。
6,第196页。)), 表明的应是律令的实质。日本至今仍有人称日军对中国民众的“处分”,出于中国民众对日军的“袭扰”。但 日军所过之处,中国民众一如湖州的民众,表现得相当“顺从”,这是战争之初江南地 区的普遍情形。小川对此也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如11月23日记金山民众:
来金山,当地支那居民样子像菩萨,实在顺从,对我们小心的敬礼。特别是孩子,以 不动的姿势表示最尊敬的态度,让人不能不生出悯然之情。
11月28日记:
本日在市内(嘉兴)徘徊,小孩的亲切莞尔,让人觉得任何地方不论说什么小孩都是可 爱的。大人小孩都举着太阳旗,各家也都插着太阳旗。其中也有以白纸中间贴着方的红 纸代替太阳旗的。
11月29日记:
支那民众原来即顺从、质朴和勤勉。
12月27日记:
支那人的多数都很高兴,这样的样子似乎对凡事都毫不介意。败给了日本,仍和许多 日本兵混杂在一起,让人感到支那人丝毫不抱有敌忾心。作为日本人到底难以想象。
38年元旦小川访问灵隐寺,当日日记除了对庙宇的宏伟和僧人的虔诚的赞叹,还记有 :
辞行之际,得赠灵隐寺志八册一部,内附有昭和天皇万岁的寿文。(注:
 ,第 54、76、79、130、141页。)
,第 54、76、79、130、141页。)中国民众的“顺从”,国内学者多以为是“消极现象”,有些人说是所谓“民族性格 ”中的“弱点”(注:如徐立刚《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及中国军人中消极现象分析》,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第1版,第130—145页。)。我以为忍辱负重,以低调自保减少无谓牺牲,不足为怪,更 不足以责。不仅忍辱负重不足以责,即使如小川所见“丝毫不抱敌忾心”,也不必深责 。在本国政府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国民时尤其如此。只要不越过“卖友求荣”的底线, 求生本是最正当的理由。这一问题涉及中国的节烈观与人的基本权利,非三言两语可以 尽其详,是故此处不拟展开。总之,即便依完全以镇压为目的的中支军律、令,“显出 不服从的样子”“就立即枪杀”,也是全然没有凭藉的。
日军侵华的日方原始文献,特别是战争初起时的公私文献,已十不存一,所以每一件 的发现,都或可补史文之缺,因此都值得细细研读。在日方否定派喧嚣日益高涨的今天 尤其如此。本文所胪列的数点,只是我在阅读小川日记中的随手所记,不敢妄称已充分 发掘了其中价值,但即便如此,已良有所获,所以,向学界推介,自以为可以不算贸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