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作品中对神谕的描述
郭海良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3年06期第107~112页
【作者简介】郭海良,1957年生,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62
【关 键 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神谕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6-0107-06
在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待古希腊传统宗教及超自然因素的态度问题上,中外学 术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一般认为,希罗多德出于其拥护古希腊传统宗教的基本立场 ,因而对神谕、朕兆、预言、幻象、奇迹等深信不疑;修昔底德则由于其深受古希腊“ 诡辩派”哲学的影响,因而不仅对所有这些超自然的因素一概视为迷信,而且还能对日 食、月食、地震、风暴等自然现象作出理性的解释。(注:参见我国已出版或发表的各 种西方史学史著作中的相关章节和论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者序言>第27~28页;J.B.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New York,1908.第128页以下;J.Hart,Herodotus and Greek History,London and Camberra,1983.)第43页以下;K.Dover,The Greeks and their Legacy,Basil Blackwell,1988.第65~73页;S.Oost,“Thucydides and the Irrational:Sundry Passage”,Classical Philology 70(1975),pp.186-196.;A.Powell,“Thucydides and Divinatio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6(1979),pp.45-50.;村川坚太郎编:“世界の名著?5へロド トストウキユデイデス”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31页和第51页。)有些研究修昔底德的 学者在承认他与希罗多德的这种基本差异的同时,也看到了修昔底德在对待希腊传统宗 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指出了他对待神谕、朕兆等现象的保留态度,并试图从他 的整个宗教观的角度去解释这种保留态度。(注:前引S.Oost的论文(Classical Philology 70(1975),p.195.);青木千佳子:“前五世 託”,载“史 林”第77卷第6期(1994年),第32~62页。)然而,希腊传统宗教、神谕、朕兆、预言、 幻象以及奇迹等等,它们各自的内涵、表现形式、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 位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许多古希腊哲人在有时对 待其中不同对象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差别。以往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由于 忽视了这种不同的涉及对象之间的区别,研究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都不免过于笼统, 所以也就未能比较准确地分别揭示出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等当事人在这些具体方面的真 正态度,多数学者的注意力还纠缠在古人对这些超自然因素的“信”与“不信”的问题 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神谕的描述为切入点 ,具体地讨论一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对待神谕的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为古 希腊史学史和古希腊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做些有益的尝试,恳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託”,载“史 林”第77卷第6期(1994年),第32~62页。)然而,希腊传统宗教、神谕、朕兆、预言、 幻象以及奇迹等等,它们各自的内涵、表现形式、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 位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许多古希腊哲人在有时对 待其中不同对象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差别。以往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由于 忽视了这种不同的涉及对象之间的区别,研究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都不免过于笼统, 所以也就未能比较准确地分别揭示出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等当事人在这些具体方面的真 正态度,多数学者的注意力还纠缠在古人对这些超自然因素的“信”与“不信”的问题 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神谕的描述为切入点 ,具体地讨论一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对待神谕的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为古 希腊史学史和古希腊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做些有益的尝试,恳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
古希腊人一般都认为,在人类即将遭遇重大的历史变故之际,神明都会对人类有所启 示,希罗多德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他曾明确地断言道:“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 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至于神托,我不能说它不是真的;当 我亲眼看到下面的一些事情时,我也并不试图否定那些他们讲得十分清楚的事情:…… 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听到巴奇司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则我既不敢在神托的事情上反对他, 又不能认可别人的反对论调了”。(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 第412页和590页。)因此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有关神谕、朕兆等神明启示的记载可谓 随处可见,而且尤其对神谕显示出了极大的重视。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述及神谕的地方共有上百次之多,大大超过了关于日食 、风暴等朕兆的描述。(注:据有些研究者的统计,希罗多德提及朕兆的次数为35次。 如前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序言>第27页,郭圣铭 王晴佳主编:《西方著名史 学家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郭圣铭 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 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不仅如此,神谕遍布全书的各个章 节、几乎涉及到每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 样。神谕以如此高的频率和如此多的数量出现在同一部著作中,这在众多古希腊作家的 作品中也是极为罕见,以致于有的学者甚至主张把神谕视为构成《历史》一书的基本框 架和理解该书的基本线索。(注:H.W.Parke and D.E.W.Wormell,The Delphic Oracle, 2vols.Blackwell,1956.第2卷第Ⅶ页。)
希罗多德不厌其详地把神谕写进自己的著作中去,固然是出于他对神谕的相信,同时 也是由于他想利用神谕来证实自己写作内容的可信性、或者显示自己某些观念的准确性 。希罗多德笔下的神谕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特尔斐神托所,这与当时希腊人的普遍认同倾 向是一致的。然而也许是由于他思想中“亲蛮”意识在发挥作用的缘故,他的注意力并 没有仅仅局限于来自特尔斐神托所或者希腊本土其他神托所的神谕,而是面向所有不同 来源的神谕。换而言之,希罗多德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写作内容及其具体需要来选择神谕 的,而并不在乎神谕的来源。譬如在诸多事例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在讨论埃及的 领土范围时,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就搬出了阿蒙神庙里的神谕,并且特意 声明道:“我是在形成了我的关于埃及的看法以后,才听到了神的这一宣托的”,(注 :希罗多德:《历史》,第117页。)以显示神谕的神圣性和自己的客观性。
与上述这种把神谕直接用于证实自己观点的写法相比,希罗多德更多的是把神谕用来 说明“因果报应”原则。众所周知,“因果报应”是希罗多德理解和解读历史事件时所 信奉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写作揭示给人们的一条历史发 展的基本规律。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神谕,绝大多数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 度展示着这项基本原则的严肃性和这条基本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无论是在描述吕底亚、 埃及、波斯等异国他邦的形势以及克洛伊索斯、居鲁士、冈比西斯等异邦君王的命运过 程中,还是在描述希波战争过程中希腊人的抗争及其命运结局的时候,都始终贯穿了希 罗多德的这一意图。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对克洛伊索斯统治下的吕底亚王国的描述为开篇,这一方面是 由于吕底亚和克洛伊索斯是古希腊人最为熟悉的小亚细亚国家及其君王,因而就成了希 罗多德介绍小亚细亚地区概况时最合适的切入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克洛伊索斯统治下 的吕底亚王国走向灭亡的命运历程最能体现“因果报应”原则,因而希罗多德就以此作 为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注:有些学者曾经对这两点采取了“二者择一”的态度并展 开过争论,详见M.E.White,“Herodotus's Starting—Point”,Phoenix,23(1969),p.4 5ff.和H?P?Stahl,“Learning through Suffering?Croisus'Conversation in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Yale Classical Studies,24(1975),pp.1—3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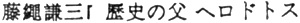 ”新潮社,1989年,第31~42页。)作为显示“因果报应”原则的一种基本因素,贯穿 于有关这个典型事例的描述文字之中的神谕尤其具有代表性,历来被学者们视为了解希 罗多德神谕观的典型例证。在希罗多德叙述吕底亚王国历史的文字中,神谕共出现过14 次,(注:希罗多德:《历史》,第4、7、9、21、24、25、43、47页。)其中最后的5次 与克洛伊索斯有关。另外,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王国事务的时候,也经常会涉及到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些与希腊人相关的情况),而即使在这些文字中也屡 屡出现神谕,(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9~33、42~43页。)与主题叙述中的神谕相 互呼应、相辅相成。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希罗多德对神谕深信不疑的基本倾向,也反映出 他在实际运用神谕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和方法。
”新潮社,1989年,第31~42页。)作为显示“因果报应”原则的一种基本因素,贯穿 于有关这个典型事例的描述文字之中的神谕尤其具有代表性,历来被学者们视为了解希 罗多德神谕观的典型例证。在希罗多德叙述吕底亚王国历史的文字中,神谕共出现过14 次,(注:希罗多德:《历史》,第4、7、9、21、24、25、43、47页。)其中最后的5次 与克洛伊索斯有关。另外,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王国事务的时候,也经常会涉及到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些与希腊人相关的情况),而即使在这些文字中也屡 屡出现神谕,(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9~33、42~43页。)与主题叙述中的神谕相 互呼应、相辅相成。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希罗多德对神谕深信不疑的基本倾向,也反映出 他在实际运用神谕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和方法。
希罗多德在对神谕确信不疑的前提下,把能否正确地理解和解读神谕的问题提到了极 其重要的高度。在他看来,历史上一些国家和个人之所以会使自己蒙受巨大灾难乃至身 败名裂,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读神谕的真正含义。他的这种 态度,在他叙述克洛伊索斯与神谕的关系的文字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注:希罗多德 :《历史》第24~26、35~37和38页。)在这些描述中,希罗多德并没有对那些模棱两 可的神谕本身作任何解释,而只是反复强调了克洛伊索斯本人对神谕的一再误解、以及 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举动与吕底亚王国的亡国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字里行间 处处透露出对克洛伊索斯愚蠢行为的批判,而且如果当事人对神谕表示疑问或埋怨的话 ,他还会借其他事件当事人或神明之口直截了当地说明其中的缘由。譬如最具代表性的 例子就是:克洛伊索斯当了波斯军队的俘虏以后,觉得自己是被神谕所误导,于是就派 人去特尔斐神托所谴责神明,结果却领受了神谕宣示人的一番反唇相讥。(注:希罗多 德:《历史》第47~48页。)从关于克洛伊索斯与神谕的关系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希罗 多德完全把克洛伊索斯的例子提升为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所作所为与国家、民 族以及个人命运之间因果关系的范例。实际上,这既是他把克洛伊索斯统治下的吕底亚 王国逐步走向灭亡的历史作为自己著作的开篇的目的之一,同时也是他撰写这部《历史 》时最想强调的深层内容之一。
除了上述克洛伊索斯的遭遇之外,希罗多德还在书中讲述了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民 族中大量类似的典型事例,以证明自己这个基本观点的普遍正确性。他具体地叙述了波 凯亚人向库尔诺斯殖民过程中的遭遇,也详细地记载了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在阿格巴塔拿 丧生和库列涅国王阿尔凯西拉欧斯在巴尔卡死亡的经过。在他的笔下,这些人遭遇灭顶 之灾的原因和方式都与克洛伊索斯如出一辙。(注:希罗多德:《历史》第83~84、223 ~224和330~331页。)
相比之下,希罗多德在描述包括希波战争在内的与希腊城邦相关的事务过程中涉及神 谕的次数略少于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等非希腊地区,然而他却同时更多地提到了朕兆 、预言等,而且所要体现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却始终没变:误解或无视神谕必然给自己带 来灾难。不仅如此,希罗多德在叙述方法上也有所改变。此前在叙述非希腊地区的此类 事例时,他基本上都是客观地描述事情的具体经过,并不附加自己的主观评判。而在叙 述与希腊相关的有关事例时,他却经常毫不掩饰地发表一些自己的议论,从而使得主题 更加明确。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在叙述了埃乌波亚人遭到希腊 军队重创的经过之后,希罗多德明确地指出这是他们因无视神谕而得到的报应;(注: 希罗多德:《历史》,第568页。)另一个是对普拉塔伊阿战役前夕波斯军队统帅玛尔多 纽斯在进行战前动员时误解神谕的描述,在这里希罗多德虽然没有正面指出玛尔多纽斯 对于神谕的错误解释,但是却特意强调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玛尔多纽斯信以为真并因 此而作出错误决断的那条神谕实际上是针对伊里利亚人和恩凯列斯人的,另外一条神谕 才是针对波斯人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第643页。)
希罗多德在书中除了大量地叙述由于误解或无视神谕而遭到报应的事例之外,也列举 了许多因正确理解神谕而获得成功的事例,而且这些成功的事例几乎都发生在希腊人中 间。希罗多德在叙述在叙述吕底亚王国历史的过程中,就在两处提到了与希腊城邦有关 的神谕。一处讲述了庇西特拉图因正确地领会了神谕并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从而又一次 在雅典建立绝对统治的经过;(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9~30页。)另一处则讲述 了斯巴达人在攻打铁该亚人过程中两次接受神谕的不同经历,从正反两方面昭示了神谕 的神圣性和正确理解神谕的重要性。(注:希罗多德:《历史》,第31~34页。)除此之 外,在诸多此类事例的记载中,关于斯巴达人根据神谕确定国王人选的经过(注:希罗 多德:《历史》,第422页。)和撒拉米斯海战前夕雅典人讨论神谕的情景(注:希罗多 德:《历史》,第518~521页。)的描述,可以说更加具有代表性,而且言词中尤其明 显地反映出希罗多德对雅典的偏爱。
从所有涉及到神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希罗多德对正确解读神谕的人们的赞许 和对误解或无视神谕的行为的批判,还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对那些在私欲的作用下伪造神 谕或者有选择地宣示神谕的巫师们的揭露、以及对买通巫师假传神谕的野心家们的鞭挞 。(注:例如希罗多德:《历史》,第428页和第465页。)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 希罗多德确实相信神谕的神圣性和准确性,承认神谕对人类事务的干预作用。然而与此 同时,希罗多德又一再强调神谕的这种干预作用的实现取决于人类本身的行为方式,关 键在于人们是否具备准确地识别真假神谕和正确地理解神谕中词语的真正含义的智慧与 能力。在他的笔下,克洛伊索斯和冈比西斯等人无疑就是因无视或误解神谕而蒙受灾难 的典型代表,而斯巴达人里卡司(注:希罗多德:《历史》,第33~34页。)和雅典人铁 米司托克列斯(注:希罗多德:《历史》,第520~521页。)则是因正确地理解神谕并采 取相应的行动而获益的典型代表。另外在希罗多德看来,能否对神谕作出正确的判断, 并不仅仅取决于理解者和解释者是否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巧,还在于他是否具备了良好 的知识功底和对相关事件的了解程度;因而巫师等专业的神谕宣示者的解释未必一定正 确,事件的实际参与者却往往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和“好运气”(注:希罗多德 :《历史》,第33页。)将神谕与事件的具体进程结合起来,从而把握住神谕的关键并 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由此可见,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神谕本身只是一种体现冥冥之 中神秘力量的客观存在,它规定着或者指示着人间事务发展变化的方向和结局、并对当 事人作出某种提示,但是它并不直接作用于这种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当事人究竟能否 因此而获得实际利益,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本身的所作所为。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在 自己的书中从未对神谕本身做过任何价值评判,他赞扬或批判的对象始终都是那些能否 正确理解神谕并作出正确选择的当事人,他尤其讨厌那些假传或伪造神谕的人物及其行 为。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历史观中的“人文主义”特征。
二
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极少提到神谕、朕兆等超自然因素 ,而且从未直接用这些因素来说明战争的进程与结果,这是他与希罗多德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出来的最大不同。另外,他虽然试图对地震、风暴、日食、月食等被当时绝大多数 希腊人视为朕兆的自然现象进行过理性的解释,(注:参见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第243页关于地震引起水灾的解释。)但是他却从未对神谕的性质做过任何说 明。这种情况固然对后人具体探讨修昔底德对神谕的态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却也 不能简单地用“相信”或“不相信”等概念进行概括。(注:前引青木千佳子论文中曾 提到过类似的看法,但是论述过于笼统。)
修昔底德在书中涉及到神谕的地方只有15处,而且丝毫没有将神谕跟他本人对伯罗奔 尼撒战争过程的描述和战争结局的解释联系起来。这与希罗多德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但是这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修昔底德对神谕的相对冷漠、或者说是有意回避的态 度。修昔底德的这种回避态度或许可以被用来说明他对神谕的怀疑,但并不足以证明他 对神谕的“不相信”,更不能将此作为论证他对神谕持批判态度的一种依据。《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中有几处涉及神谕的描述,譬如第2卷第2章中关于禁止人们住在皮拉斯基 人土地上的神谕的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9页注②。) 第2卷第5章中关于神谕诗句中两个词语的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第142页。)以及第5卷第3章中在说明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持续时间的计算方法 时涉及到的神谕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73页[此处的译 文表现得不明确,请参考英文版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Unabridged Crawley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seph Gavorse,Random House,1934 .(西学基本经典工作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西学基本经典·历 史学类》中所收)第297页]。)经常被引用来说明修昔底德对神谕的“不相信”态度。( 注:参见前引谢德风:<译者序言>第27~28页;前引K?多弗:《希腊人及其遗产》第71 页;前引A?鲍威尔论文:《修昔底德与占卜》(所载杂志第45页)。)然而只要仔细分析 一下即可看出,修昔底德之所以提及这些神谕并不是为了对它们本身进行评论或批判, 而是要说明当时人们接受和理解神谕的态度和方式,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记载下来;从 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所有那些“不相信”或者“批判”的语气和矛头都不是针对神谕本 身,而是针对那些理解和解读神谕的人们及其行为。
与此同时,修昔底德毫不留情地对各种别有用心地利用神谕的恶意行为进行了揭露。 他的矛头所指,既包括那些为了在民众中煽动战争情绪而刻意散布神谕的好战小人,( 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0页、第121~122页、第567页。)也包 括那些为了一己私欲而以不正当手段伪造和假传神谕的政治野心家和堕落巫师。(注: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65~366页。)不仅如此,修昔底德还对那些 由于自以为是地错误理解神谕而导致身败名裂的愚蠢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意在警示 世人。(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86~88页。)所有这些揭露性描述 的对象和内容同样都不是神谕本身,而是人们接受和利用神谕的方法和态度,我们虽然 无法从中得到修昔底德“相信”神谕的依据,但是也决不能因此而认定他“不相信”神 谕甚至批判神谕。
通过上述涉及神谕的具体描述,修昔底德实际上一直在提醒人们要正确地理解和谨慎 地对待神谕。他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将自己的这种意思表达出来,但是他所叙述的那 些因理解错误处理不慎而深受其害的事例和人们知道受骗后所表现出来的懊丧情景都足 以唤起人们的警觉。另外,修昔底德在描述与神谕相关的事例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按照 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以凸显当事人的错误和正确理解神谕的重要性。在他的笔下,当 然也有因以谨慎的态度利用神谕而获益的事例,这就是公元前432年斯巴达人在召开同 盟代表大会讨论对雅典宣战时请示神谕的做法。(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第81~82页。)由此可见,修昔底德在书中涉及神谕的描述尽管不多,但其中包 括的类型以及通过这些事例所倡导的对待神谕的基本原则却与希罗多德是一致的。
至于能否正确理解和解读神谕的关键是什么,修昔底德也没有像希罗多德那样用明确 的语言归之于理解者或解释者的“才智”和“好运气”。不过从他对撒拉米斯海战前夕 敢于否定权威而正确解释神谕的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赞誉(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第96~97页。)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类预测未来事物发展趋势的能力是持 肯定态度的。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神谕实际上就是一种相对“可靠”的对未来的预测 ;人们之所以对它乐而不疲,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预先知道事物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 行正确的决断,以保证行动的成功从而使自己受益。古人把对未来的预测寄希望于神谕 ,其实是对人类自身预测能力的怀疑和否定。既然修昔底德相信人类甚至有预测未来的 能力,那么在他看来至少这种能力与解读神谕的能力是一致的,只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都是人类中并不多见的“超凡”的“显著天才”而已。如此看来,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 一样,也是把人的知识才能和对事物的了解视为能否正确解读神谕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仅从《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来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 德这两位古希腊杰出的史学家在关于神谕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并不是 截然相反或者互相对立的。他们二人对神谕的不同态度,与他们在进行历史创作过程中 的不同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希罗多德没有直接经历过希波战争,他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说 都是他听来的遥远的往事;由于无法用亲身经历来证实或者证伪,所以还残留着纪事家 某些特征的他就宁可“信其有”了,而且它们确实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些道理。修昔底德 亲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过程,对这一历史过程中“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前因后果都 十分熟悉;由于他更能够理解“人”的作用及其与这场战争的关系,所以自然就把注意 力放到了“人”这一边。另外,他们的这种不同态度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以 及社会的发展变化。希罗多德对神谕的深信不疑是那个时代古希腊社会敬神祭神传统的 反映,体现了古希腊人宗教信仰的一般倾向;修昔底德对神谕的冷漠回避则是当时古希 腊社会随着“诡辩派”哲学兴起和自然科学发展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思想界的直接反 映,体现出怀疑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
然而与此同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 且几乎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在人与神谕的关系中,他们偏重的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强 调的都是人正确解读神谕的重要性以及人自身基本素质的必要性,而这些恰恰又是古希 腊社会开始由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时期的现实反映。如果说从希罗多德的《历史》 中还残留着“神”的影子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神”的敬而远之是 古希腊历史学的一大进步,那么他们在处理人与神谕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偏重 就是古希腊历史学的“人文主义”这一基本特征的具体体现。
我们因此也就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历来被视为古希腊历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并受 到中外学者们高度评价的这个“人文主义”,是否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在没有否定神本主 义这一基本前提下的、对“人”的价值及其作用的强调呢?或者说,我们在理解和把握 它的时候,是否应该有一种“动态”的意识呢?(注:最早对古希腊历史学中的“人文主 义”特征进行系统论述的是R·G·柯林武德(参见柯林武德所著《历史的观念》的第1编 第10节),其后学界对它的评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在古希腊人那里,神谕和地震、 风暴、日食、月食等朕兆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存在,因而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 德对待朕兆的态度、以及他们心目中的朕兆与神谕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有待进一 步展开具体研究的课题,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古希腊历史学的“人文主义”特征, 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3年06期第107~112页
【作者简介】郭海良,1957年生,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62
| 【内容提要】 | 本文探讨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对待神谕的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如果说从《 历史》中还残留着“神”的影子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神”的敬而远之是古希 腊史学的一大进步,那么他们在处理人与神谕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偏重就是古 希腊历史学的“人文主义”这一基本特征的具体体现。 |
在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待古希腊传统宗教及超自然因素的态度问题上,中外学 术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一般认为,希罗多德出于其拥护古希腊传统宗教的基本立场 ,因而对神谕、朕兆、预言、幻象、奇迹等深信不疑;修昔底德则由于其深受古希腊“ 诡辩派”哲学的影响,因而不仅对所有这些超自然的因素一概视为迷信,而且还能对日 食、月食、地震、风暴等自然现象作出理性的解释。(注:参见我国已出版或发表的各 种西方史学史著作中的相关章节和论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者序言>第27~28页;J.B.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New York,1908.第128页以下;J.Hart,Herodotus and Greek History,London and Camberra,1983.)第43页以下;K.Dover,The Greeks and their Legacy,Basil Blackwell,1988.第65~73页;S.Oost,“Thucydides and the Irrational:Sundry Passage”,Classical Philology 70(1975),pp.186-196.;A.Powell,“Thucydides and Divinatio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6(1979),pp.45-50.;村川坚太郎编:“世界の名著?5へロド トストウキユデイデス”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31页和第51页。)有些研究修昔底德的 学者在承认他与希罗多德的这种基本差异的同时,也看到了修昔底德在对待希腊传统宗 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指出了他对待神谕、朕兆等现象的保留态度,并试图从他 的整个宗教观的角度去解释这种保留态度。(注:前引S.Oost的论文(Classical Philology 70(1975),p.195.);青木千佳子:“前五世
 託”,载“史 林”第77卷第6期(1994年),第32~62页。)然而,希腊传统宗教、神谕、朕兆、预言、 幻象以及奇迹等等,它们各自的内涵、表现形式、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 位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许多古希腊哲人在有时对 待其中不同对象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差别。以往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由于 忽视了这种不同的涉及对象之间的区别,研究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都不免过于笼统, 所以也就未能比较准确地分别揭示出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等当事人在这些具体方面的真 正态度,多数学者的注意力还纠缠在古人对这些超自然因素的“信”与“不信”的问题 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神谕的描述为切入点 ,具体地讨论一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对待神谕的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为古 希腊史学史和古希腊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做些有益的尝试,恳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託”,载“史 林”第77卷第6期(1994年),第32~62页。)然而,希腊传统宗教、神谕、朕兆、预言、 幻象以及奇迹等等,它们各自的内涵、表现形式、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 位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许多古希腊哲人在有时对 待其中不同对象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差别。以往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由于 忽视了这种不同的涉及对象之间的区别,研究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都不免过于笼统, 所以也就未能比较准确地分别揭示出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等当事人在这些具体方面的真 正态度,多数学者的注意力还纠缠在古人对这些超自然因素的“信”与“不信”的问题 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神谕的描述为切入点 ,具体地讨论一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对待神谕的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为古 希腊史学史和古希腊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做些有益的尝试,恳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一
古希腊人一般都认为,在人类即将遭遇重大的历史变故之际,神明都会对人类有所启 示,希罗多德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他曾明确地断言道:“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 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至于神托,我不能说它不是真的;当 我亲眼看到下面的一些事情时,我也并不试图否定那些他们讲得十分清楚的事情:…… 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听到巴奇司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则我既不敢在神托的事情上反对他, 又不能认可别人的反对论调了”。(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 第412页和590页。)因此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有关神谕、朕兆等神明启示的记载可谓 随处可见,而且尤其对神谕显示出了极大的重视。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述及神谕的地方共有上百次之多,大大超过了关于日食 、风暴等朕兆的描述。(注:据有些研究者的统计,希罗多德提及朕兆的次数为35次。 如前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序言>第27页,郭圣铭 王晴佳主编:《西方著名史 学家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郭圣铭 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 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不仅如此,神谕遍布全书的各个章 节、几乎涉及到每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 样。神谕以如此高的频率和如此多的数量出现在同一部著作中,这在众多古希腊作家的 作品中也是极为罕见,以致于有的学者甚至主张把神谕视为构成《历史》一书的基本框 架和理解该书的基本线索。(注:H.W.Parke and D.E.W.Wormell,The Delphic Oracle, 2vols.Blackwell,1956.第2卷第Ⅶ页。)
希罗多德不厌其详地把神谕写进自己的著作中去,固然是出于他对神谕的相信,同时 也是由于他想利用神谕来证实自己写作内容的可信性、或者显示自己某些观念的准确性 。希罗多德笔下的神谕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特尔斐神托所,这与当时希腊人的普遍认同倾 向是一致的。然而也许是由于他思想中“亲蛮”意识在发挥作用的缘故,他的注意力并 没有仅仅局限于来自特尔斐神托所或者希腊本土其他神托所的神谕,而是面向所有不同 来源的神谕。换而言之,希罗多德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写作内容及其具体需要来选择神谕 的,而并不在乎神谕的来源。譬如在诸多事例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在讨论埃及的 领土范围时,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就搬出了阿蒙神庙里的神谕,并且特意 声明道:“我是在形成了我的关于埃及的看法以后,才听到了神的这一宣托的”,(注 :希罗多德:《历史》,第117页。)以显示神谕的神圣性和自己的客观性。
与上述这种把神谕直接用于证实自己观点的写法相比,希罗多德更多的是把神谕用来 说明“因果报应”原则。众所周知,“因果报应”是希罗多德理解和解读历史事件时所 信奉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写作揭示给人们的一条历史发 展的基本规律。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神谕,绝大多数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 度展示着这项基本原则的严肃性和这条基本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无论是在描述吕底亚、 埃及、波斯等异国他邦的形势以及克洛伊索斯、居鲁士、冈比西斯等异邦君王的命运过 程中,还是在描述希波战争过程中希腊人的抗争及其命运结局的时候,都始终贯穿了希 罗多德的这一意图。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对克洛伊索斯统治下的吕底亚王国的描述为开篇,这一方面是 由于吕底亚和克洛伊索斯是古希腊人最为熟悉的小亚细亚国家及其君王,因而就成了希 罗多德介绍小亚细亚地区概况时最合适的切入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克洛伊索斯统治下 的吕底亚王国走向灭亡的命运历程最能体现“因果报应”原则,因而希罗多德就以此作 为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注:有些学者曾经对这两点采取了“二者择一”的态度并展 开过争论,详见M.E.White,“Herodotus's Starting—Point”,Phoenix,23(1969),p.4 5ff.和H?P?Stahl,“Learning through Suffering?Croisus'Conversation in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Yale Classical Studies,24(1975),pp.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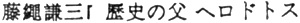 ”新潮社,1989年,第31~42页。)作为显示“因果报应”原则的一种基本因素,贯穿 于有关这个典型事例的描述文字之中的神谕尤其具有代表性,历来被学者们视为了解希 罗多德神谕观的典型例证。在希罗多德叙述吕底亚王国历史的文字中,神谕共出现过14 次,(注:希罗多德:《历史》,第4、7、9、21、24、25、43、47页。)其中最后的5次 与克洛伊索斯有关。另外,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王国事务的时候,也经常会涉及到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些与希腊人相关的情况),而即使在这些文字中也屡 屡出现神谕,(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9~33、42~43页。)与主题叙述中的神谕相 互呼应、相辅相成。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希罗多德对神谕深信不疑的基本倾向,也反映出 他在实际运用神谕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和方法。
”新潮社,1989年,第31~42页。)作为显示“因果报应”原则的一种基本因素,贯穿 于有关这个典型事例的描述文字之中的神谕尤其具有代表性,历来被学者们视为了解希 罗多德神谕观的典型例证。在希罗多德叙述吕底亚王国历史的文字中,神谕共出现过14 次,(注:希罗多德:《历史》,第4、7、9、21、24、25、43、47页。)其中最后的5次 与克洛伊索斯有关。另外,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王国事务的时候,也经常会涉及到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些与希腊人相关的情况),而即使在这些文字中也屡 屡出现神谕,(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9~33、42~43页。)与主题叙述中的神谕相 互呼应、相辅相成。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希罗多德对神谕深信不疑的基本倾向,也反映出 他在实际运用神谕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和方法。希罗多德在对神谕确信不疑的前提下,把能否正确地理解和解读神谕的问题提到了极 其重要的高度。在他看来,历史上一些国家和个人之所以会使自己蒙受巨大灾难乃至身 败名裂,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读神谕的真正含义。他的这种 态度,在他叙述克洛伊索斯与神谕的关系的文字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注:希罗多德 :《历史》第24~26、35~37和38页。)在这些描述中,希罗多德并没有对那些模棱两 可的神谕本身作任何解释,而只是反复强调了克洛伊索斯本人对神谕的一再误解、以及 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举动与吕底亚王国的亡国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字里行间 处处透露出对克洛伊索斯愚蠢行为的批判,而且如果当事人对神谕表示疑问或埋怨的话 ,他还会借其他事件当事人或神明之口直截了当地说明其中的缘由。譬如最具代表性的 例子就是:克洛伊索斯当了波斯军队的俘虏以后,觉得自己是被神谕所误导,于是就派 人去特尔斐神托所谴责神明,结果却领受了神谕宣示人的一番反唇相讥。(注:希罗多 德:《历史》第47~48页。)从关于克洛伊索斯与神谕的关系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希罗 多德完全把克洛伊索斯的例子提升为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所作所为与国家、民 族以及个人命运之间因果关系的范例。实际上,这既是他把克洛伊索斯统治下的吕底亚 王国逐步走向灭亡的历史作为自己著作的开篇的目的之一,同时也是他撰写这部《历史 》时最想强调的深层内容之一。
除了上述克洛伊索斯的遭遇之外,希罗多德还在书中讲述了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民 族中大量类似的典型事例,以证明自己这个基本观点的普遍正确性。他具体地叙述了波 凯亚人向库尔诺斯殖民过程中的遭遇,也详细地记载了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在阿格巴塔拿 丧生和库列涅国王阿尔凯西拉欧斯在巴尔卡死亡的经过。在他的笔下,这些人遭遇灭顶 之灾的原因和方式都与克洛伊索斯如出一辙。(注:希罗多德:《历史》第83~84、223 ~224和330~331页。)
相比之下,希罗多德在描述包括希波战争在内的与希腊城邦相关的事务过程中涉及神 谕的次数略少于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等非希腊地区,然而他却同时更多地提到了朕兆 、预言等,而且所要体现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却始终没变:误解或无视神谕必然给自己带 来灾难。不仅如此,希罗多德在叙述方法上也有所改变。此前在叙述非希腊地区的此类 事例时,他基本上都是客观地描述事情的具体经过,并不附加自己的主观评判。而在叙 述与希腊相关的有关事例时,他却经常毫不掩饰地发表一些自己的议论,从而使得主题 更加明确。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在叙述了埃乌波亚人遭到希腊 军队重创的经过之后,希罗多德明确地指出这是他们因无视神谕而得到的报应;(注: 希罗多德:《历史》,第568页。)另一个是对普拉塔伊阿战役前夕波斯军队统帅玛尔多 纽斯在进行战前动员时误解神谕的描述,在这里希罗多德虽然没有正面指出玛尔多纽斯 对于神谕的错误解释,但是却特意强调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玛尔多纽斯信以为真并因 此而作出错误决断的那条神谕实际上是针对伊里利亚人和恩凯列斯人的,另外一条神谕 才是针对波斯人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第643页。)
希罗多德在书中除了大量地叙述由于误解或无视神谕而遭到报应的事例之外,也列举 了许多因正确理解神谕而获得成功的事例,而且这些成功的事例几乎都发生在希腊人中 间。希罗多德在叙述在叙述吕底亚王国历史的过程中,就在两处提到了与希腊城邦有关 的神谕。一处讲述了庇西特拉图因正确地领会了神谕并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从而又一次 在雅典建立绝对统治的经过;(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9~30页。)另一处则讲述 了斯巴达人在攻打铁该亚人过程中两次接受神谕的不同经历,从正反两方面昭示了神谕 的神圣性和正确理解神谕的重要性。(注:希罗多德:《历史》,第31~34页。)除此之 外,在诸多此类事例的记载中,关于斯巴达人根据神谕确定国王人选的经过(注:希罗 多德:《历史》,第422页。)和撒拉米斯海战前夕雅典人讨论神谕的情景(注:希罗多 德:《历史》,第518~521页。)的描述,可以说更加具有代表性,而且言词中尤其明 显地反映出希罗多德对雅典的偏爱。
从所有涉及到神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希罗多德对正确解读神谕的人们的赞许 和对误解或无视神谕的行为的批判,还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对那些在私欲的作用下伪造神 谕或者有选择地宣示神谕的巫师们的揭露、以及对买通巫师假传神谕的野心家们的鞭挞 。(注:例如希罗多德:《历史》,第428页和第465页。)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 希罗多德确实相信神谕的神圣性和准确性,承认神谕对人类事务的干预作用。然而与此 同时,希罗多德又一再强调神谕的这种干预作用的实现取决于人类本身的行为方式,关 键在于人们是否具备准确地识别真假神谕和正确地理解神谕中词语的真正含义的智慧与 能力。在他的笔下,克洛伊索斯和冈比西斯等人无疑就是因无视或误解神谕而蒙受灾难 的典型代表,而斯巴达人里卡司(注:希罗多德:《历史》,第33~34页。)和雅典人铁 米司托克列斯(注:希罗多德:《历史》,第520~521页。)则是因正确地理解神谕并采 取相应的行动而获益的典型代表。另外在希罗多德看来,能否对神谕作出正确的判断, 并不仅仅取决于理解者和解释者是否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巧,还在于他是否具备了良好 的知识功底和对相关事件的了解程度;因而巫师等专业的神谕宣示者的解释未必一定正 确,事件的实际参与者却往往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和“好运气”(注:希罗多德 :《历史》,第33页。)将神谕与事件的具体进程结合起来,从而把握住神谕的关键并 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由此可见,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神谕本身只是一种体现冥冥之 中神秘力量的客观存在,它规定着或者指示着人间事务发展变化的方向和结局、并对当 事人作出某种提示,但是它并不直接作用于这种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当事人究竟能否 因此而获得实际利益,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本身的所作所为。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在 自己的书中从未对神谕本身做过任何价值评判,他赞扬或批判的对象始终都是那些能否 正确理解神谕并作出正确选择的当事人,他尤其讨厌那些假传或伪造神谕的人物及其行 为。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历史观中的“人文主义”特征。
二
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极少提到神谕、朕兆等超自然因素 ,而且从未直接用这些因素来说明战争的进程与结果,这是他与希罗多德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出来的最大不同。另外,他虽然试图对地震、风暴、日食、月食等被当时绝大多数 希腊人视为朕兆的自然现象进行过理性的解释,(注:参见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第243页关于地震引起水灾的解释。)但是他却从未对神谕的性质做过任何说 明。这种情况固然对后人具体探讨修昔底德对神谕的态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却也 不能简单地用“相信”或“不相信”等概念进行概括。(注:前引青木千佳子论文中曾 提到过类似的看法,但是论述过于笼统。)
修昔底德在书中涉及到神谕的地方只有15处,而且丝毫没有将神谕跟他本人对伯罗奔 尼撒战争过程的描述和战争结局的解释联系起来。这与希罗多德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但是这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修昔底德对神谕的相对冷漠、或者说是有意回避的态 度。修昔底德的这种回避态度或许可以被用来说明他对神谕的怀疑,但并不足以证明他 对神谕的“不相信”,更不能将此作为论证他对神谕持批判态度的一种依据。《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中有几处涉及神谕的描述,譬如第2卷第2章中关于禁止人们住在皮拉斯基 人土地上的神谕的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9页注②。) 第2卷第5章中关于神谕诗句中两个词语的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第142页。)以及第5卷第3章中在说明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持续时间的计算方法 时涉及到的神谕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73页[此处的译 文表现得不明确,请参考英文版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Unabridged Crawley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seph Gavorse,Random House,1934 .(西学基本经典工作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西学基本经典·历 史学类》中所收)第297页]。)经常被引用来说明修昔底德对神谕的“不相信”态度。( 注:参见前引谢德风:<译者序言>第27~28页;前引K?多弗:《希腊人及其遗产》第71 页;前引A?鲍威尔论文:《修昔底德与占卜》(所载杂志第45页)。)然而只要仔细分析 一下即可看出,修昔底德之所以提及这些神谕并不是为了对它们本身进行评论或批判, 而是要说明当时人们接受和理解神谕的态度和方式,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记载下来;从 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所有那些“不相信”或者“批判”的语气和矛头都不是针对神谕本 身,而是针对那些理解和解读神谕的人们及其行为。
与此同时,修昔底德毫不留情地对各种别有用心地利用神谕的恶意行为进行了揭露。 他的矛头所指,既包括那些为了在民众中煽动战争情绪而刻意散布神谕的好战小人,( 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0页、第121~122页、第567页。)也包 括那些为了一己私欲而以不正当手段伪造和假传神谕的政治野心家和堕落巫师。(注: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65~366页。)不仅如此,修昔底德还对那些 由于自以为是地错误理解神谕而导致身败名裂的愚蠢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意在警示 世人。(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86~88页。)所有这些揭露性描述 的对象和内容同样都不是神谕本身,而是人们接受和利用神谕的方法和态度,我们虽然 无法从中得到修昔底德“相信”神谕的依据,但是也决不能因此而认定他“不相信”神 谕甚至批判神谕。
通过上述涉及神谕的具体描述,修昔底德实际上一直在提醒人们要正确地理解和谨慎 地对待神谕。他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将自己的这种意思表达出来,但是他所叙述的那 些因理解错误处理不慎而深受其害的事例和人们知道受骗后所表现出来的懊丧情景都足 以唤起人们的警觉。另外,修昔底德在描述与神谕相关的事例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按照 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以凸显当事人的错误和正确理解神谕的重要性。在他的笔下,当 然也有因以谨慎的态度利用神谕而获益的事例,这就是公元前432年斯巴达人在召开同 盟代表大会讨论对雅典宣战时请示神谕的做法。(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第81~82页。)由此可见,修昔底德在书中涉及神谕的描述尽管不多,但其中包 括的类型以及通过这些事例所倡导的对待神谕的基本原则却与希罗多德是一致的。
至于能否正确理解和解读神谕的关键是什么,修昔底德也没有像希罗多德那样用明确 的语言归之于理解者或解释者的“才智”和“好运气”。不过从他对撒拉米斯海战前夕 敢于否定权威而正确解释神谕的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赞誉(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第96~97页。)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类预测未来事物发展趋势的能力是持 肯定态度的。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神谕实际上就是一种相对“可靠”的对未来的预测 ;人们之所以对它乐而不疲,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预先知道事物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 行正确的决断,以保证行动的成功从而使自己受益。古人把对未来的预测寄希望于神谕 ,其实是对人类自身预测能力的怀疑和否定。既然修昔底德相信人类甚至有预测未来的 能力,那么在他看来至少这种能力与解读神谕的能力是一致的,只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都是人类中并不多见的“超凡”的“显著天才”而已。如此看来,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 一样,也是把人的知识才能和对事物的了解视为能否正确解读神谕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仅从《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来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 德这两位古希腊杰出的史学家在关于神谕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并不是 截然相反或者互相对立的。他们二人对神谕的不同态度,与他们在进行历史创作过程中 的不同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希罗多德没有直接经历过希波战争,他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说 都是他听来的遥远的往事;由于无法用亲身经历来证实或者证伪,所以还残留着纪事家 某些特征的他就宁可“信其有”了,而且它们确实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些道理。修昔底德 亲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过程,对这一历史过程中“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前因后果都 十分熟悉;由于他更能够理解“人”的作用及其与这场战争的关系,所以自然就把注意 力放到了“人”这一边。另外,他们的这种不同态度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以 及社会的发展变化。希罗多德对神谕的深信不疑是那个时代古希腊社会敬神祭神传统的 反映,体现了古希腊人宗教信仰的一般倾向;修昔底德对神谕的冷漠回避则是当时古希 腊社会随着“诡辩派”哲学兴起和自然科学发展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思想界的直接反 映,体现出怀疑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
然而与此同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 且几乎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在人与神谕的关系中,他们偏重的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强 调的都是人正确解读神谕的重要性以及人自身基本素质的必要性,而这些恰恰又是古希 腊社会开始由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时期的现实反映。如果说从希罗多德的《历史》 中还残留着“神”的影子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神”的敬而远之是 古希腊历史学的一大进步,那么他们在处理人与神谕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偏重 就是古希腊历史学的“人文主义”这一基本特征的具体体现。
我们因此也就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历来被视为古希腊历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并受 到中外学者们高度评价的这个“人文主义”,是否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在没有否定神本主 义这一基本前提下的、对“人”的价值及其作用的强调呢?或者说,我们在理解和把握 它的时候,是否应该有一种“动态”的意识呢?(注:最早对古希腊历史学中的“人文主 义”特征进行系统论述的是R·G·柯林武德(参见柯林武德所著《历史的观念》的第1编 第10节),其后学界对它的评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在古希腊人那里,神谕和地震、 风暴、日食、月食等朕兆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存在,因而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 德对待朕兆的态度、以及他们心目中的朕兆与神谕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有待进一 步展开具体研究的课题,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古希腊历史学的“人文主义”特征, 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