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
黄洋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1年05期第100~107页
【作者简介】作者黄洋,1965年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关 键 词】希腊城邦/公共空间/政治文化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虽然是当代社会哲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却同历史学研究 不无关系。这首先是因为,它是用来表述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结构性特征的。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一书中,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从兴起到解体的 过程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关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 共领域,但他认为,其起源要追溯到古代希腊。在论及这一点时,哈贝马斯说,在希腊城邦 中,“城邦领域”(sphere of the polis)同“家庭领域”(sphere of the oikos)严格区分 开来,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 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注: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 r 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he MIT Press,1989,p.3.)。在此之前,汉娜·阿伦特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区分可追溯到 城邦兴起之时,而且同样把公共领域定义为城邦领域,把私人领域定义为家庭领域(注: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A Study of the Central Dilemmas Facing Mod e rn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7—28.)。社会 哲学家们的这种视角具有启发性,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城邦的政治生活。众所周知, 希腊城邦最主要的考古遗迹是它的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神庙、祭坛、露天剧 院 、体育馆、运动场等。然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希腊史学界,都较少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 视角对它们进行解析。诚然,艺术史家和文化史家们有较多的讨论,但其视角全然不同。艺 术史家主要关注其艺术形式,这一点自不待言。文化史家们关注的是不同的遗迹所传载的不 同文化活动,如宗教崇拜活动、文化艺术活动、体育活动等等。如果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来看 ,这些遗迹具有共同性,即它们都是城邦公共生活的场所,是城邦的公共空间,亦即社会哲 学家们所说的“城邦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同城邦的政治生活又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本文试图从公共空间的层面,结合文献资料,对希腊城邦的公共建筑及其空间格局进 行历史的解读,并试图由此揭示城邦政治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
在希腊城邦中,公共领域或“城邦领域”是以公共生活空间作为表象的,而公共生活空间 又是通过公共建筑之格局而形成的。同时,希腊城邦通常是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形成的,这个 中心城市即是城邦公共建筑的首要集中地。根据考古学家以现代理念为基础的划分,城邦最 主要的公共建筑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宗教性公共建筑如神庙、圣殿、祭坛和公共墓地;二是 城邦的市政建筑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民大会会场、法庭、公共食堂等;三是城邦社会 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如体育馆、运动场、摔跤场、露天剧场等。这些公共建筑雄伟、坚固,它 们成为城邦恒久的人文景观。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古代希腊的神庙、露天剧场和体 育场还屹立在城邦的遗址之上,一面向后世的人们无言地展示希腊文化独特的魅力,一面也 将希腊城邦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恒久地固化了下来。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是密切相连的。前城邦时代的典型建筑 遗存不是公共建筑,而是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王宫和城堡。就连宗教性建筑,也通常 是 同王宫联系在一起,以圣室或圣殿的形式出现(注:Water 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Oxford:Basil Blackwell,1 98 5,Chapter I.)。显然,王宫及其附属的宗教建筑主要为王 室成员所用,并不向公众开放,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建筑。在迈锡尼文明毁灭之后的 “黑暗时代”,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建筑都已不见于考古记载,尽管荷马史诗中描述了一些宏 伟的宫殿。而即使在荷马史诗的描述中,宗教祭祀活动往往因地而宜,而不是在某个固定的 圣地(注:如荷马《奥德修记》Ⅲ,1—68行(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38—41页)记载 ,派洛斯王国的人们是在海滩上祭祀海神波赛冬。参见 de Polignac,Cults,Ter ri 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 5,pp.15—16。)。
de Polignac,Cults,Ter ri 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 5,pp.15—16。)。
到古风时代初期,随着希腊城邦的兴起,公共建筑开始在希腊各地出现。考古资料表明, 在 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 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注:A.Snodgrass,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inaugural lecture),Ca 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最早的神庙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在时间上同城邦的兴起相吻 合(注:A.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 e ss,1980,pp.58-60;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pp.17—19.)。在同一时期,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文化性公共建筑也相继出现。学者们认为, 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密切相关。议事大厅和公民大会会场等市政建筑固然是城邦兴 起的直接结果,其他公共建筑如神庙和体育场的修建也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因为对规模相对 很小的城邦来说,要修建如此巨大的建筑,需要共同的努力和城邦集体的决策(注:A.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33;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pp.17—19.)。在同一时期,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文化性公共建筑也相继出现。学者们认为, 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密切相关。议事大厅和公民大会会场等市政建筑固然是城邦兴 起的直接结果,其他公共建筑如神庙和体育场的修建也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因为对规模相对 很小的城邦来说,要修建如此巨大的建筑,需要共同的努力和城邦集体的决策(注:A.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33; de Poligna c, 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pp.19—20.)。
de Poligna c, 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pp.19—20.)。
从社会功能上看,城邦公共建筑格局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由神庙和祭 坛组成的宗教圣地,是人们参与宗教崇拜的地方。在古代希腊,宗教崇拜不同于后来出现的 基督教,虽然希腊人都崇拜一个奥林匹斯神系,但他们既没有正统而抽象的宗教教义,也没 有无所不包的圣经,宗教崇拜主要是以公共节日的形式出现。在古代希腊,这类的宗教节日 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00个以上,崇拜的神祇则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 年 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注:P.Cartledge,“The Greek religious festivals”,in P.E.Easterling & J.V.Muir ed s. ,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98—127.)。在节日里,人们往往举行盛大的游行,以迎送神祇,然后 在圣地的祭坛上举行献祭的仪式。献祭所用的牺牲一般是牛或羊,在隆重的献祭时,宰杀的 牛羊多达上百头。献祭仪式结束后,所有参加祭祀的人一起举行祭餐,平均分享祭祀所用的 牛羊肉。虽然希腊人对不同的宗教节日的参与者有所限制,但从总体上看,公共的宗教节日 是向城邦的所有公民开放的,祭祀仪式之后的祭餐也是公民群体的聚餐。
另一方面,古代希腊宗教崇拜的形式亦不同于古代西亚、埃及和其他古代文明。从总体上 看,不存在一个特权的祭司或僧侣阶层,宗教崇拜活动不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祭司主持,而 是由城邦任命官员直接主持(注:Water 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p.95.)。在雅典,负责祭神和主持祭祀仪式的官员俱是从公民中抽签 选举出来的,任期仅限一年(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4;参见苗立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7年,57页。)。也就是说,主持祭祀的是普通的公民。而且对希腊人来说, 和神的沟通一般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因此,当希罗多德在波斯看到祈祷由专门的巫师(Mag us)主持时,感到十分惊诧(注: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I,132(牛津大学出版社希腊文原版,1927年 第3版)。)。
显而易见,希腊的宗教崇拜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城邦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共同 的活动。因此,宗教性公共空间对于城邦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将宗教崇拜活动看 成是全体公民共同的公共生活,才能理解为什么希腊城邦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 建宏伟的神庙。一般而言,一个城邦的总人口只有几万人,无论是从人力上看,还是从财力 上看,要建造巨大的神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耗费几代人之力,但每个城邦似乎都 还是不遗余力。在位于西西里西部的阿克拉加(Acragas),至今仍然保存了至少6座神庙的遗 址,均用当地的石灰石建造而成。在意大利南部的波西多尼亚(Posidonia),仍有3座巨大的 大理石神庙完好地屹立着,另有一座业已倒塌的神庙遗址。这两个弱小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根 本没有起过什么重要作用,文献中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有关它们的记载。但任何参观过这两 个城邦遗址上这些宏伟神庙及其遗迹的人恐怕都想像不到,它们在希腊世界处于极其边缘的 地位。
不仅如此,城邦的宗教崇拜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法国学者de Polignac指出,城邦宗教 崇拜是理解城邦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他从城邦的兴起与宗教崇拜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 ,提出宗教崇拜的确立即神庙的修建和宗教圣地的界定导致了城邦的形成。他认为,通过共 同的宗教崇拜,人们获得了一种自我意识,一种集体的认同感,这是城邦最根本的基础。另 一方面,宗教圣地也确定了城邦的领土界限。在希腊,除了位于中心城市的宗教圣地外,还 有些神庙和宗教圣地建立在城邦的边界。这些宗教圣地同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之间形成一种 呼应,一方面通过特定的、不同于其他城邦的宗教崇拜明确地界定了城邦领土的疆界,另一 方面,边界圣地和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之间形成双向交流和互动。在宗教节日中,游行的队 伍要么从城市中心的圣地出发,行进到边界的圣地,要么以反方向游行。人们在两个宗教圣 地之间的来回流动,把居于中心城市之外的城邦人口也纳入到城邦的公共生活中来,从而使 城邦的成员形成一个意识上的整体,也使得边缘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注: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 e,参见2章。)。英国学者Sourvino u-Inwood在对埃留西斯秘仪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位于雅典领土西北边陲的埃留 西斯秘仪同城邦最中心的机构交织在一起,形成“城邦中一个重要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崇拜 中心”(注:C.Sourvinou-Inwood,“Reconstructing change:ideology and the Eleusinian Myste ri es”,in Mark Golden & Peter Toohey eds.,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Historicism,P eriodization,and the Ancient World,London,1997,pp.132—164.)。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 e,参见2章。)。英国学者Sourvino u-Inwood在对埃留西斯秘仪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位于雅典领土西北边陲的埃留 西斯秘仪同城邦最中心的机构交织在一起,形成“城邦中一个重要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崇拜 中心”(注:C.Sourvinou-Inwood,“Reconstructing change:ideology and the Eleusinian Myste ri es”,in Mark Golden & Peter Toohey eds.,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Historicism,P eriodization,and the Ancient World,London,1997,pp.132—164.)。
城邦的市政广场是城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这里是最大的集市,店铺林立,人们定期 从各地聚集到这里,从事买卖。同时这里又是市政建筑集中的地方,是城邦公共生活和政治 生活的空间。在古希腊语中,“市政广场”(agora)一词的原意是“民众大会”,以后逐渐 被用来表示市政广场,其本身就含有“集会之地”的意思。人们在这里交流有关城邦事务的 信息,参与市政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在雅典的市政广场上,建有一个称做“纪名英雄墙”(E ponymous Heroes)的建筑,其顶端树立着10个雅典英雄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雅典的10个部 落,墙身用做公告栏。有关城邦的事务诸如公民大会等皆公告于此,各项法令的预案也公告 于此,供人们讨论,而后在公民大会上投票表决(注:德谟斯梯尼:《演说集》(Demosthenis Orationes),XX,94(牛津大学希腊文原版,2卷 上 册,1920年)和XIV,23(牛津大学希腊文原版,1卷,1903年)。)。同时公民大会所通过的法令都刻在石碑 上,然后公布于广场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在市政广场上建母亲神的圣殿,称做M etroon,它同时又是雅典的公共档案馆,城邦所有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500人议事会 的决议,以及收支账目俱都存放于此,以供公民们查询(注:参见James P.Sickinger,Public Records and Archives in Classical Athens,Univers 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Chapters 3—4。)。在斯巴达,公共生活的中心是训 练场和公共食堂。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城邦,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场上从事 集体性的身体锻炼或军事训练,用餐则在公共食堂,而不是在家里。所有的男性公民——包 括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内——都在公共食堂用餐。因为莱库古的立法,公民如不参加共餐制, 即丧失公民权。另外,在克里特的一些城邦也存在着共餐制。
露天剧场是进行戏剧表演和观看戏剧的地方。戏剧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于雅典,而后迅速传 遍整个希腊世界。到古典时代,露天剧场已经成为城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戏剧表演和 观看戏剧的场所,露天剧场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空间。为了使公民都能够观看戏剧表演,它的 规模一般都很大,可容纳数千人乃至万人以上,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可容纳15000人左 右。然而,露天剧场并非仅仅是观看戏剧的场所,它也常常用做政治活动的空间。在雅典, 公民大会有时在狄奥尼索斯剧场举行(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2.4,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45页。)。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种文化活动的戏 剧表演却和城邦的政治生活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每年狄奥尼索斯戏剧节的开幕式上,雅典 城邦都要把同盟诸邦所缴纳的贡赋摆在狄奥尼索斯剧场的舞台中央,向全体公民展示(注:依索克拉底:《论和平》,82(罗叶布古典丛书版,哈佛大学出版社)。);同 时在战争中牺牲的公民的子女也一一走上舞台,领取城邦给予他们的抚恤。戏剧节同时变成 了一个展示城邦实力、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舞台(注:Simon Goldhill,“The Great Dionysia and civic ideology”,Journal of Hellenic S tudies,107(1987),pp.58—76.)。另一方面,即便是戏剧表演本身,也 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从根本上说,戏剧是一项公民群体的活动,演员由公民担任,歌队也 由公民组成,而且常常用来代表城邦的公民集体。观看表演的观众是城邦的公民,他们不是 被动的观看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是评判者。首先,戏剧表演活动是由公民群体直接组织 和管理的。在雅典,由从公民中抽签选出的官员确定每年戏剧节所上演的剧目,并指定富有 的雅典公民担任戏剧的制作人。其次,戏剧表演以竞赛的形式上演,由公民进行评判。其方 法是,从各部落中抽签选出评委,再评出获奖者。而且,表演的内容常常同城邦及其公民群 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描写的是雅典人在萨拉米海战中战胜波斯人的 情景,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尼亚人》则表达了作者对雅典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的态 度。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公民群体对城邦事务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以便时时更正违背城邦 政治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进一步明晰城邦政治的理想。最后,戏剧表演培养了公民的集体精 神。聚集于同一剧场的公民观看同样的表演,经历同样的感觉。这样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意识 到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一个区别于剧场之外、区别于其他剧场的整体,他们之间滋生了 一种共同的情感(注:Jean-Pierre Vemant ed.,The Greek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te r 6,pp.210-212.)。
体育场馆同样是城邦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正如布克哈特所说,竞争精神是希腊人最重要 的精神。而体育竞技则是希腊人表现其竞争精神的最主要形式之一。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庇底亚运动会、地峡运动会和尼米亚运动会这四大泛希腊的运动会之外,每个城邦都有自己 的运动会,在运动会上赢得冠军的人获得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得到城邦的重奖。例如在雅典 最大的运动会——泛雅典娜节的运动会上,少年组短跑冠军的奖励是50缸橄榄油,价值约60 0德拉克玛(注:Inscriptiones Graecae Ⅱ,2311.)。除奖品之外,泛希腊运动会的冠军还会得到城邦的其他奖励,如奖励金钱、 为其塑雕像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在竞技中获胜本身即是一种优秀品质(arete)。因此, 城邦的公民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体育训练。在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即是从事军 事训练和体育锻炼。同这种需要相适应,每个城邦都建有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体育场 馆,它们成为现代体育场馆的原型(注:英文中的体育场(stadium)、体操馆(gymnasium)等词汇出自希腊文stadion或gymnasion 。)。所不同的是,希腊城邦的体育场所同时也是公民之间 主 要的社交场所,是城邦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公民们不仅在这里参与体育训练,而且在这里 参与城邦的社会生活。即使是不直接参与体育训练的人,也往往在体育馆里消磨时光。但他 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者。
二
希腊城邦创造了一系列的公共生活空间,成为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布景和舞台,它生动 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希腊城邦社会政治文化的 一些显著特征。城邦的公共生活空间反映了城邦政治相对的民主性。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相 对民主性是一个普遍的特点,不只是民主的雅典如此,也不只是其他少数几个像雅典那样建 立民主政体的城邦如此,即使实行贵族政治与寡头政治的城邦也如此。所有的城邦——无论 是民主政治的城邦还是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的城邦——都设有公民参政的公民大会。当然, 不是每个城邦都像雅典那样,公民大会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也不是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公民 大会。在实行贵族政治的城邦如斯巴达,贵族元老会议能够推翻公民大会的决议;同时,有 些寡头政体对政治参与实行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但无论如何,公民群体被看成是城邦政治 生活的主体,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则是不争的事实。政治的民主性和参与的广泛性明显 地反映在城邦的公共空间之中。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宗教圣地、露天剧场、体育场馆 等都是公民群体的活动场所,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法国著名学者Vidal-Naquet在论及城邦 公共空间的民主性时说:“城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一个以市政广场及其公共建 筑 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争论。权力不再限于王宫之中 ,而是置于这个公共的中心。”(注:Pierre Vidal-Naquet,The Black Hunter:Forms of Thought and Forms of Society i n the Greek Worl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257.)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其规模的巨大都说明,为数众多的公 民经常性地参加城邦的各种公共活动。
但是,公共空间并不仅仅是政治民主性的表现,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政治生 活的民主性。首先,公共生活空间培养了一种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本身 鼓励了公民的参与意识。雅典“纪名英雄墙”下的布告栏公告城邦的一应事务,显然会吸引 众多的公民前来了解情况。同时,城邦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公民参与。在公元前5世纪 ,阿里斯托芬提到,雅典城邦让行使警察职能的公共奴隶用染成红色的绳子驱使公民参加公 民大会,如果拒不参与,衣服上染上红色,即遭罚款的处罚(注:阿里斯托芬:《阿卡地亚人》,21—22行,参见Aristophanes,Lysistrata and Other P lays,Penguin Books,1973,p.50。)。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开始 推行公民大会补贴法,给予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一定的补贴。最初,参加每次公民大会的补 贴是1个奥布尔;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补贴的数量上升到1个半德拉克玛(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1.3;62.2,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44、65页。)。补贴的目的显 然是让贫穷公民也能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但补贴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中 期,雅典还实施了观戏补贴法(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3.1;47.2(《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46、49页)。亚里 士多德在这两处提到的“观戏金”(to theorikon)主要用于观戏津贴。此处引《亚里士多德 全集》版两处分别译作“……军队司库、祭祀钱财(to theorikon)监管人……”和“……与 军队司库和掌领祭祀(to theorikon)的官员一道……”,在关键处均未能体现原文的意思, 且对同一词语前后译法不一。),对在戏剧节观看戏剧的公民进行补贴,此后这种补贴又扩 大到其他的公共节日(注: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Oxford :Basil Blacwell,1991,p.98.)。在斯巴达,对共餐制的参与甚至是强迫性的。观戏补贴和强制性的 共餐制都说明,公共生活对城邦来说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它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活动 ,强化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强化了公民的集体观念和民主意识。经常性 的集体活动使公民们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还是一个有着共同生 活经历、共同传统和共同感受的集体。
其次,公共生活空间向公民群体灌输和强化了民主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公共空间是城邦 进行社会动员、向公民群体传递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对公民群体来说,公共生活是 一种民主的教育。在公共空间中,贵族与平民为伍,政治领袖与普通公民打成一片。在斯巴 达的共餐制中,王和普通公民同桌而食。在公民大会上,希波战争时期雅典的著名领袖阿里 斯泰德甚至被身旁的人当成了普通公民(注:普鲁塔克:《阿里斯泰德传》,7;参见Plutarch,The Rise and Fall of Athens,Pengu in Books,1960,p.117。)。即使是叙拉古的僭主,在公共空间中也没有明显 的特权。虽然他在露天剧场拥有固定的座位,上刻“巴昔琉斯”一词,但这一座位并不在显 耀的位置,同其他的座位也没有任何区别(注:此为笔者在实地考察时亲眼所见。)。精英贵族不是生活在远离民众、象征特权的深 宫大院里,领袖和民众的距离拉近了。另一方面,在不断的面对面的接触中,领袖的神秘感 和威严也消失了,民众在面对领袖时的自信心相应地增加了。
公共空间对民主意识的强化还体现在,它是民主观念的展示台,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识形态 。在雅典,刺杀僭主的阿里斯托格通和哈莫迪俄斯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英雄,他们的雕像树 立在市政广场上,雅典人还为他们设立了祭坛(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8,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62页。)。同时,在雅典市政广场一个称做“绘画柱 廊”的公共建筑上,绘有巨幅壁画,突出表现了两个拟人化的人物形象,一是“民主”,一 是“人民”(注:宝桑尼阿斯,I,3—5;参见Pausanias,Guide to Greece,Vol.1,Penguin Books,1979,p p.17-18。)。这种民主的意识形态甚至还反映在宗教圣地和公共墓地里。雅典的公共墓地 主要用于埋葬牺牲的战士,城邦为他们树立墓碑,分部落刻上所有牺牲者的名字,但并不标 明他们的家世。十分明显,这种做法是为了强调牺牲者作为城邦一份子的集体性和平等性, 而隐去其高低贵贱之分。在这里,城邦每年都要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公共葬礼,邀请最著名的 演说家发表葬礼演说。研究表明,这些葬礼演说所阐述的主要是雅典城邦的意识形态,而不 是对死者的赞扬(注:Nicole Loraux,The Invention of Athens: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 it 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巴特侬神庙上的浮雕刻画了泛雅典娜节的游行队伍和马拉松之战中牺牲 的194名战士。学者们注意到,整幅浮雕没有突出任何个人,强调的是整体。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它想要突出的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公民群体。同公共墓地里的墓碑上只刻有牺牲者的名 字、而不表现其家世一样,它旨在强调公民的平等性、公民群体的集体性,是民主意识形态 的体现(注:Robin Osborne,“The viewing and obscuring of the Parthenon frieze”,Journal o f Hellenic Studies 107(1987),pp.98-105.)。显而易见,集体性的活动、公共生活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教育的作用, 是民主的意识形态。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而希腊的城邦数 量众多,且各有差异,其中像雅典这样建立起民主政体的并不多。严格地说,雅典并不具有 完全的代表性,我们的分析因而是有局限的。不过,由于原始材料本身的限制,任何对希腊 城邦的总体分析都必须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雅典的资料,这种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 如此,笔者还是认为,从总体上看,上述分析是适用于所有城邦的。公共空间的发达以及对 公共生活的强调,是希腊城邦的普遍特征:一方面,它是城邦政治文化的反映,体现了城邦 政治的相对民主性;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强化城邦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 可以说是建构了公民的群体意识。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对公共空间的考察还有助于把握希腊城邦政治文化中有别于现代 人观念的一些总体特征。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宗教、政治与文化是一些 相互区分开来的概念,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但我们对希腊城邦公共空间的分析表 明,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宗教等并不是分开的,而是融为一个整体。比 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现代意义的宗教概念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希腊文中并没有 “宗教”一词,我们所说的宗教,在希腊文中称eusebeia,实际上指的是“有关神的事务” 或“对神的关爱”(注:Vernant ed.,The Greeks,Chapter 8,p.256.),而有关神的事务和对神的关爱都是城邦事务的一部分,是城邦的政治 。正因为宗教的这种政治性,学者们又将城邦中的宗教节日称为“宗教—政治节日”(注:Cartledge,“The Greek religious festivals”.)。从 这里可以看出,在希腊城邦中,政治活动所包含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确实如此,希腊 人的政治概念要广于现代人的政治概念。在古希腊语中,用来表示政治的一组词如“政治” (politike)、“政治制度”(politeia)、“政治的”(politikos)、“公民”(polites)等, 都是源出于“城邦”(polis)一词,其基本含义都表示“属于城邦的”。例如,“政治”即 表示“城邦的事务”。也就是说,所有城邦的事务——无论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的、宗教的、 还是社会的、文化的——都是政治。在城邦生活中,这个广义的政治概念以公共生活空间的 方式得到具像化。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即是对城邦政治的参与,公共空间则成为政治空间,属 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性公共领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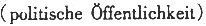 。在这个政治空间 中,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固然是城邦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即连旁观者也是政治生活的 积极参与者,正如Goldhill所说:“成为观众的一员并不仅仅是成为城邦社会组织中的一缕 ,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行动。作为一个进行评价和判断的观众来参与,就是作为一个政治 主体来参与。”(注:见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C a 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
。在这个政治空间 中,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固然是城邦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即连旁观者也是政治生活的 积极参与者,正如Goldhill所说:“成为观众的一员并不仅仅是成为城邦社会组织中的一缕 ,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行动。作为一个进行评价和判断的观众来参与,就是作为一个政治 主体来参与。”(注:见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C a 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
希腊城邦中公共生活空间的重要,是同私人生活空间的弱化相伴随的。在建筑格局上,公 共建筑空间显得压倒一切;私人生活空间虽然存在,但相比起来,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例 如在斯巴达,男性公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公共空间里,在训练场上,在公共食堂里。就连 已婚男子同妻子相会,也得偷偷摸摸。公共空间同私人空间的对立,反映了城邦政治及其观 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集体的权利压倒个人的权利。公共空间强调的是积极的参与,公民 参与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城邦的鼓励。私人空间是个人自由的体现,而个人的自由同城邦政治 即使不是格格不入,至少也是相背离的。对城邦社会来说,私人空间是可疑的,它往往同反 动势力联系在一起。酒会是私人生活空间的一种主要形式,因而受到怀疑。公元前415 年,雅典发生毁坏神像案,迅即被与酒会联系在一起。报案者称,虽然没有目睹神像被毁的 过程,但以前经常看到阿西比德和他的同伴一起聚饮,其间诸多可疑言行,定为他们所为(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28,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443页。)。结果身为雅典将军的阿西比德及其同伴均被判有罪。苏格拉底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同私人 空间生活有关。他不仅是贵族酒会的常客,而且经常是主角。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他被 描绘成一个想法怪异的人物。他招收弟子,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教授颠倒黑白的技艺(注:《云》,94行以往(Aristophanes,Lysistrata and Other Plays,116f)。)。 显然,这样的私人生活空间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同城邦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
公共空间的重要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是同城邦的根本特征相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 政治动物”,实际上是指人是属于城邦的动物。脱离了城邦、生活在城邦集体之外者,要么 是动物,要么是鬼神(注:《政治学》,1252b34—1253a39,参见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7—9页。)。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在希腊城邦中,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参与的 自由,或以撒亚·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不存在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个人自由,即脱离 社 会的自由,或者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只是经历了基督教兴起、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之后,个人自由或“消极自由”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1年05期第100~107页
【作者简介】作者黄洋,1965年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 【内容提要】 | 从公共空间的视角,对古希腊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及其空间进行历史的解读 ,可以看到它们所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与文化活动——都是城 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因而体现出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 私人空间的次要性,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 要特征。 |
一
在希腊城邦中,公共领域或“城邦领域”是以公共生活空间作为表象的,而公共生活空间 又是通过公共建筑之格局而形成的。同时,希腊城邦通常是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形成的,这个 中心城市即是城邦公共建筑的首要集中地。根据考古学家以现代理念为基础的划分,城邦最 主要的公共建筑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宗教性公共建筑如神庙、圣殿、祭坛和公共墓地;二是 城邦的市政建筑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民大会会场、法庭、公共食堂等;三是城邦社会 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如体育馆、运动场、摔跤场、露天剧场等。这些公共建筑雄伟、坚固,它 们成为城邦恒久的人文景观。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古代希腊的神庙、露天剧场和体 育场还屹立在城邦的遗址之上,一面向后世的人们无言地展示希腊文化独特的魅力,一面也 将希腊城邦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恒久地固化了下来。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是密切相连的。前城邦时代的典型建筑 遗存不是公共建筑,而是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王宫和城堡。就连宗教性建筑,也通常 是 同王宫联系在一起,以圣室或圣殿的形式出现(注:Water 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Oxford:Basil Blackwell,1 98 5,Chapter I.)。显然,王宫及其附属的宗教建筑主要为王 室成员所用,并不向公众开放,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建筑。在迈锡尼文明毁灭之后的 “黑暗时代”,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建筑都已不见于考古记载,尽管荷马史诗中描述了一些宏 伟的宫殿。而即使在荷马史诗的描述中,宗教祭祀活动往往因地而宜,而不是在某个固定的 圣地(注:如荷马《奥德修记》Ⅲ,1—68行(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38—41页)记载 ,派洛斯王国的人们是在海滩上祭祀海神波赛冬。参见
 de Polignac,Cults,Ter ri 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 5,pp.15—16。)。
de Polignac,Cults,Ter ri 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 5,pp.15—16。)。到古风时代初期,随着希腊城邦的兴起,公共建筑开始在希腊各地出现。考古资料表明, 在 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 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注:A.Snodgrass,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inaugural lecture),Ca 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最早的神庙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在时间上同城邦的兴起相吻 合(注:A.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 e ss,1980,pp.58-60;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pp.17—19.)。在同一时期,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文化性公共建筑也相继出现。学者们认为, 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密切相关。议事大厅和公民大会会场等市政建筑固然是城邦兴 起的直接结果,其他公共建筑如神庙和体育场的修建也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因为对规模相对 很小的城邦来说,要修建如此巨大的建筑,需要共同的努力和城邦集体的决策(注:A.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33;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pp.17—19.)。在同一时期,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文化性公共建筑也相继出现。学者们认为, 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密切相关。议事大厅和公民大会会场等市政建筑固然是城邦兴 起的直接结果,其他公共建筑如神庙和体育场的修建也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因为对规模相对 很小的城邦来说,要修建如此巨大的建筑,需要共同的努力和城邦集体的决策(注:A.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33; de Poligna c, 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pp.19—20.)。
de Poligna c, 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pp.19—20.)。从社会功能上看,城邦公共建筑格局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由神庙和祭 坛组成的宗教圣地,是人们参与宗教崇拜的地方。在古代希腊,宗教崇拜不同于后来出现的 基督教,虽然希腊人都崇拜一个奥林匹斯神系,但他们既没有正统而抽象的宗教教义,也没 有无所不包的圣经,宗教崇拜主要是以公共节日的形式出现。在古代希腊,这类的宗教节日 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00个以上,崇拜的神祇则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 年 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注:P.Cartledge,“The Greek religious festivals”,in P.E.Easterling & J.V.Muir ed s. ,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98—127.)。在节日里,人们往往举行盛大的游行,以迎送神祇,然后 在圣地的祭坛上举行献祭的仪式。献祭所用的牺牲一般是牛或羊,在隆重的献祭时,宰杀的 牛羊多达上百头。献祭仪式结束后,所有参加祭祀的人一起举行祭餐,平均分享祭祀所用的 牛羊肉。虽然希腊人对不同的宗教节日的参与者有所限制,但从总体上看,公共的宗教节日 是向城邦的所有公民开放的,祭祀仪式之后的祭餐也是公民群体的聚餐。
另一方面,古代希腊宗教崇拜的形式亦不同于古代西亚、埃及和其他古代文明。从总体上 看,不存在一个特权的祭司或僧侣阶层,宗教崇拜活动不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祭司主持,而 是由城邦任命官员直接主持(注:Water 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p.95.)。在雅典,负责祭神和主持祭祀仪式的官员俱是从公民中抽签 选举出来的,任期仅限一年(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4;参见苗立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7年,57页。)。也就是说,主持祭祀的是普通的公民。而且对希腊人来说, 和神的沟通一般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因此,当希罗多德在波斯看到祈祷由专门的巫师(Mag us)主持时,感到十分惊诧(注: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I,132(牛津大学出版社希腊文原版,1927年 第3版)。)。
显而易见,希腊的宗教崇拜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城邦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共同 的活动。因此,宗教性公共空间对于城邦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将宗教崇拜活动看 成是全体公民共同的公共生活,才能理解为什么希腊城邦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 建宏伟的神庙。一般而言,一个城邦的总人口只有几万人,无论是从人力上看,还是从财力 上看,要建造巨大的神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耗费几代人之力,但每个城邦似乎都 还是不遗余力。在位于西西里西部的阿克拉加(Acragas),至今仍然保存了至少6座神庙的遗 址,均用当地的石灰石建造而成。在意大利南部的波西多尼亚(Posidonia),仍有3座巨大的 大理石神庙完好地屹立着,另有一座业已倒塌的神庙遗址。这两个弱小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根 本没有起过什么重要作用,文献中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有关它们的记载。但任何参观过这两 个城邦遗址上这些宏伟神庙及其遗迹的人恐怕都想像不到,它们在希腊世界处于极其边缘的 地位。
不仅如此,城邦的宗教崇拜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法国学者de Polignac指出,城邦宗教 崇拜是理解城邦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他从城邦的兴起与宗教崇拜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 ,提出宗教崇拜的确立即神庙的修建和宗教圣地的界定导致了城邦的形成。他认为,通过共 同的宗教崇拜,人们获得了一种自我意识,一种集体的认同感,这是城邦最根本的基础。另 一方面,宗教圣地也确定了城邦的领土界限。在希腊,除了位于中心城市的宗教圣地外,还 有些神庙和宗教圣地建立在城邦的边界。这些宗教圣地同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之间形成一种 呼应,一方面通过特定的、不同于其他城邦的宗教崇拜明确地界定了城邦领土的疆界,另一 方面,边界圣地和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之间形成双向交流和互动。在宗教节日中,游行的队 伍要么从城市中心的圣地出发,行进到边界的圣地,要么以反方向游行。人们在两个宗教圣 地之间的来回流动,把居于中心城市之外的城邦人口也纳入到城邦的公共生活中来,从而使 城邦的成员形成一个意识上的整体,也使得边缘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注: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 e,参见2章。)。英国学者Sourvino u-Inwood在对埃留西斯秘仪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位于雅典领土西北边陲的埃留 西斯秘仪同城邦最中心的机构交织在一起,形成“城邦中一个重要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崇拜 中心”(注:C.Sourvinou-Inwood,“Reconstructing change:ideology and the Eleusinian Myste ri es”,in Mark Golden & Peter Toohey eds.,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Historicism,P eriodization,and the Ancient World,London,1997,pp.132—164.)。
de Polignac,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 e,参见2章。)。英国学者Sourvino u-Inwood在对埃留西斯秘仪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位于雅典领土西北边陲的埃留 西斯秘仪同城邦最中心的机构交织在一起,形成“城邦中一个重要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崇拜 中心”(注:C.Sourvinou-Inwood,“Reconstructing change:ideology and the Eleusinian Myste ri es”,in Mark Golden & Peter Toohey eds.,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Historicism,P eriodization,and the Ancient World,London,1997,pp.132—164.)。城邦的市政广场是城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这里是最大的集市,店铺林立,人们定期 从各地聚集到这里,从事买卖。同时这里又是市政建筑集中的地方,是城邦公共生活和政治 生活的空间。在古希腊语中,“市政广场”(agora)一词的原意是“民众大会”,以后逐渐 被用来表示市政广场,其本身就含有“集会之地”的意思。人们在这里交流有关城邦事务的 信息,参与市政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在雅典的市政广场上,建有一个称做“纪名英雄墙”(E ponymous Heroes)的建筑,其顶端树立着10个雅典英雄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雅典的10个部 落,墙身用做公告栏。有关城邦的事务诸如公民大会等皆公告于此,各项法令的预案也公告 于此,供人们讨论,而后在公民大会上投票表决(注:德谟斯梯尼:《演说集》(Demosthenis Orationes),XX,94(牛津大学希腊文原版,2卷 上 册,1920年)和XIV,23(牛津大学希腊文原版,1卷,1903年)。)。同时公民大会所通过的法令都刻在石碑 上,然后公布于广场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在市政广场上建母亲神的圣殿,称做M etroon,它同时又是雅典的公共档案馆,城邦所有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500人议事会 的决议,以及收支账目俱都存放于此,以供公民们查询(注:参见James P.Sickinger,Public Records and Archives in Classical Athens,Univers 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Chapters 3—4。)。在斯巴达,公共生活的中心是训 练场和公共食堂。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城邦,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场上从事 集体性的身体锻炼或军事训练,用餐则在公共食堂,而不是在家里。所有的男性公民——包 括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内——都在公共食堂用餐。因为莱库古的立法,公民如不参加共餐制, 即丧失公民权。另外,在克里特的一些城邦也存在着共餐制。
露天剧场是进行戏剧表演和观看戏剧的地方。戏剧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于雅典,而后迅速传 遍整个希腊世界。到古典时代,露天剧场已经成为城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戏剧表演和 观看戏剧的场所,露天剧场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空间。为了使公民都能够观看戏剧表演,它的 规模一般都很大,可容纳数千人乃至万人以上,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可容纳15000人左 右。然而,露天剧场并非仅仅是观看戏剧的场所,它也常常用做政治活动的空间。在雅典, 公民大会有时在狄奥尼索斯剧场举行(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2.4,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45页。)。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种文化活动的戏 剧表演却和城邦的政治生活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每年狄奥尼索斯戏剧节的开幕式上,雅典 城邦都要把同盟诸邦所缴纳的贡赋摆在狄奥尼索斯剧场的舞台中央,向全体公民展示(注:依索克拉底:《论和平》,82(罗叶布古典丛书版,哈佛大学出版社)。);同 时在战争中牺牲的公民的子女也一一走上舞台,领取城邦给予他们的抚恤。戏剧节同时变成 了一个展示城邦实力、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舞台(注:Simon Goldhill,“The Great Dionysia and civic ideology”,Journal of Hellenic S tudies,107(1987),pp.58—76.)。另一方面,即便是戏剧表演本身,也 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从根本上说,戏剧是一项公民群体的活动,演员由公民担任,歌队也 由公民组成,而且常常用来代表城邦的公民集体。观看表演的观众是城邦的公民,他们不是 被动的观看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是评判者。首先,戏剧表演活动是由公民群体直接组织 和管理的。在雅典,由从公民中抽签选出的官员确定每年戏剧节所上演的剧目,并指定富有 的雅典公民担任戏剧的制作人。其次,戏剧表演以竞赛的形式上演,由公民进行评判。其方 法是,从各部落中抽签选出评委,再评出获奖者。而且,表演的内容常常同城邦及其公民群 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描写的是雅典人在萨拉米海战中战胜波斯人的 情景,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尼亚人》则表达了作者对雅典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的态 度。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公民群体对城邦事务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以便时时更正违背城邦 政治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进一步明晰城邦政治的理想。最后,戏剧表演培养了公民的集体精 神。聚集于同一剧场的公民观看同样的表演,经历同样的感觉。这样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意识 到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一个区别于剧场之外、区别于其他剧场的整体,他们之间滋生了 一种共同的情感(注:Jean-Pierre Vemant ed.,The Greek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te r 6,pp.210-212.)。
体育场馆同样是城邦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正如布克哈特所说,竞争精神是希腊人最重要 的精神。而体育竞技则是希腊人表现其竞争精神的最主要形式之一。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庇底亚运动会、地峡运动会和尼米亚运动会这四大泛希腊的运动会之外,每个城邦都有自己 的运动会,在运动会上赢得冠军的人获得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得到城邦的重奖。例如在雅典 最大的运动会——泛雅典娜节的运动会上,少年组短跑冠军的奖励是50缸橄榄油,价值约60 0德拉克玛(注:Inscriptiones Graecae Ⅱ,2311.)。除奖品之外,泛希腊运动会的冠军还会得到城邦的其他奖励,如奖励金钱、 为其塑雕像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在竞技中获胜本身即是一种优秀品质(arete)。因此, 城邦的公民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体育训练。在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即是从事军 事训练和体育锻炼。同这种需要相适应,每个城邦都建有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体育场 馆,它们成为现代体育场馆的原型(注:英文中的体育场(stadium)、体操馆(gymnasium)等词汇出自希腊文stadion或gymnasion 。)。所不同的是,希腊城邦的体育场所同时也是公民之间 主 要的社交场所,是城邦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公民们不仅在这里参与体育训练,而且在这里 参与城邦的社会生活。即使是不直接参与体育训练的人,也往往在体育馆里消磨时光。但他 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者。
二
希腊城邦创造了一系列的公共生活空间,成为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布景和舞台,它生动 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希腊城邦社会政治文化的 一些显著特征。城邦的公共生活空间反映了城邦政治相对的民主性。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相 对民主性是一个普遍的特点,不只是民主的雅典如此,也不只是其他少数几个像雅典那样建 立民主政体的城邦如此,即使实行贵族政治与寡头政治的城邦也如此。所有的城邦——无论 是民主政治的城邦还是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的城邦——都设有公民参政的公民大会。当然, 不是每个城邦都像雅典那样,公民大会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也不是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公民 大会。在实行贵族政治的城邦如斯巴达,贵族元老会议能够推翻公民大会的决议;同时,有 些寡头政体对政治参与实行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但无论如何,公民群体被看成是城邦政治 生活的主体,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则是不争的事实。政治的民主性和参与的广泛性明显 地反映在城邦的公共空间之中。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宗教圣地、露天剧场、体育场馆 等都是公民群体的活动场所,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法国著名学者Vidal-Naquet在论及城邦 公共空间的民主性时说:“城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一个以市政广场及其公共建 筑 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争论。权力不再限于王宫之中 ,而是置于这个公共的中心。”(注:Pierre Vidal-Naquet,The Black Hunter:Forms of Thought and Forms of Society i n the Greek Worl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257.)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其规模的巨大都说明,为数众多的公 民经常性地参加城邦的各种公共活动。
但是,公共空间并不仅仅是政治民主性的表现,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政治生 活的民主性。首先,公共生活空间培养了一种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本身 鼓励了公民的参与意识。雅典“纪名英雄墙”下的布告栏公告城邦的一应事务,显然会吸引 众多的公民前来了解情况。同时,城邦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公民参与。在公元前5世纪 ,阿里斯托芬提到,雅典城邦让行使警察职能的公共奴隶用染成红色的绳子驱使公民参加公 民大会,如果拒不参与,衣服上染上红色,即遭罚款的处罚(注:阿里斯托芬:《阿卡地亚人》,21—22行,参见Aristophanes,Lysistrata and Other P lays,Penguin Books,1973,p.50。)。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开始 推行公民大会补贴法,给予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一定的补贴。最初,参加每次公民大会的补 贴是1个奥布尔;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补贴的数量上升到1个半德拉克玛(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1.3;62.2,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44、65页。)。补贴的目的显 然是让贫穷公民也能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但补贴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中 期,雅典还实施了观戏补贴法(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3.1;47.2(《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46、49页)。亚里 士多德在这两处提到的“观戏金”(to theorikon)主要用于观戏津贴。此处引《亚里士多德 全集》版两处分别译作“……军队司库、祭祀钱财(to theorikon)监管人……”和“……与 军队司库和掌领祭祀(to theorikon)的官员一道……”,在关键处均未能体现原文的意思, 且对同一词语前后译法不一。),对在戏剧节观看戏剧的公民进行补贴,此后这种补贴又扩 大到其他的公共节日(注: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Oxford :Basil Blacwell,1991,p.98.)。在斯巴达,对共餐制的参与甚至是强迫性的。观戏补贴和强制性的 共餐制都说明,公共生活对城邦来说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它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活动 ,强化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强化了公民的集体观念和民主意识。经常性 的集体活动使公民们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还是一个有着共同生 活经历、共同传统和共同感受的集体。
其次,公共生活空间向公民群体灌输和强化了民主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公共空间是城邦 进行社会动员、向公民群体传递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对公民群体来说,公共生活是 一种民主的教育。在公共空间中,贵族与平民为伍,政治领袖与普通公民打成一片。在斯巴 达的共餐制中,王和普通公民同桌而食。在公民大会上,希波战争时期雅典的著名领袖阿里 斯泰德甚至被身旁的人当成了普通公民(注:普鲁塔克:《阿里斯泰德传》,7;参见Plutarch,The Rise and Fall of Athens,Pengu in Books,1960,p.117。)。即使是叙拉古的僭主,在公共空间中也没有明显 的特权。虽然他在露天剧场拥有固定的座位,上刻“巴昔琉斯”一词,但这一座位并不在显 耀的位置,同其他的座位也没有任何区别(注:此为笔者在实地考察时亲眼所见。)。精英贵族不是生活在远离民众、象征特权的深 宫大院里,领袖和民众的距离拉近了。另一方面,在不断的面对面的接触中,领袖的神秘感 和威严也消失了,民众在面对领袖时的自信心相应地增加了。
公共空间对民主意识的强化还体现在,它是民主观念的展示台,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识形态 。在雅典,刺杀僭主的阿里斯托格通和哈莫迪俄斯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英雄,他们的雕像树 立在市政广场上,雅典人还为他们设立了祭坛(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8,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62页。)。同时,在雅典市政广场一个称做“绘画柱 廊”的公共建筑上,绘有巨幅壁画,突出表现了两个拟人化的人物形象,一是“民主”,一 是“人民”(注:宝桑尼阿斯,I,3—5;参见Pausanias,Guide to Greece,Vol.1,Penguin Books,1979,p p.17-18。)。这种民主的意识形态甚至还反映在宗教圣地和公共墓地里。雅典的公共墓地 主要用于埋葬牺牲的战士,城邦为他们树立墓碑,分部落刻上所有牺牲者的名字,但并不标 明他们的家世。十分明显,这种做法是为了强调牺牲者作为城邦一份子的集体性和平等性, 而隐去其高低贵贱之分。在这里,城邦每年都要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公共葬礼,邀请最著名的 演说家发表葬礼演说。研究表明,这些葬礼演说所阐述的主要是雅典城邦的意识形态,而不 是对死者的赞扬(注:Nicole Loraux,The Invention of Athens: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 it 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巴特侬神庙上的浮雕刻画了泛雅典娜节的游行队伍和马拉松之战中牺牲 的194名战士。学者们注意到,整幅浮雕没有突出任何个人,强调的是整体。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它想要突出的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公民群体。同公共墓地里的墓碑上只刻有牺牲者的名 字、而不表现其家世一样,它旨在强调公民的平等性、公民群体的集体性,是民主意识形态 的体现(注:Robin Osborne,“The viewing and obscuring of the Parthenon frieze”,Journal o f Hellenic Studies 107(1987),pp.98-105.)。显而易见,集体性的活动、公共生活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教育的作用, 是民主的意识形态。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而希腊的城邦数 量众多,且各有差异,其中像雅典这样建立起民主政体的并不多。严格地说,雅典并不具有 完全的代表性,我们的分析因而是有局限的。不过,由于原始材料本身的限制,任何对希腊 城邦的总体分析都必须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雅典的资料,这种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 如此,笔者还是认为,从总体上看,上述分析是适用于所有城邦的。公共空间的发达以及对 公共生活的强调,是希腊城邦的普遍特征:一方面,它是城邦政治文化的反映,体现了城邦 政治的相对民主性;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强化城邦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 可以说是建构了公民的群体意识。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对公共空间的考察还有助于把握希腊城邦政治文化中有别于现代 人观念的一些总体特征。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宗教、政治与文化是一些 相互区分开来的概念,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但我们对希腊城邦公共空间的分析表 明,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宗教等并不是分开的,而是融为一个整体。比 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现代意义的宗教概念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希腊文中并没有 “宗教”一词,我们所说的宗教,在希腊文中称eusebeia,实际上指的是“有关神的事务” 或“对神的关爱”(注:Vernant ed.,The Greeks,Chapter 8,p.256.),而有关神的事务和对神的关爱都是城邦事务的一部分,是城邦的政治 。正因为宗教的这种政治性,学者们又将城邦中的宗教节日称为“宗教—政治节日”(注:Cartledge,“The Greek religious festivals”.)。从 这里可以看出,在希腊城邦中,政治活动所包含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确实如此,希腊 人的政治概念要广于现代人的政治概念。在古希腊语中,用来表示政治的一组词如“政治” (politike)、“政治制度”(politeia)、“政治的”(politikos)、“公民”(polites)等, 都是源出于“城邦”(polis)一词,其基本含义都表示“属于城邦的”。例如,“政治”即 表示“城邦的事务”。也就是说,所有城邦的事务——无论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的、宗教的、 还是社会的、文化的——都是政治。在城邦生活中,这个广义的政治概念以公共生活空间的 方式得到具像化。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即是对城邦政治的参与,公共空间则成为政治空间,属 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性公共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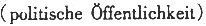 。在这个政治空间 中,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固然是城邦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即连旁观者也是政治生活的 积极参与者,正如Goldhill所说:“成为观众的一员并不仅仅是成为城邦社会组织中的一缕 ,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行动。作为一个进行评价和判断的观众来参与,就是作为一个政治 主体来参与。”(注:见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C a 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
。在这个政治空间 中,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固然是城邦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即连旁观者也是政治生活的 积极参与者,正如Goldhill所说:“成为观众的一员并不仅仅是成为城邦社会组织中的一缕 ,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行动。作为一个进行评价和判断的观众来参与,就是作为一个政治 主体来参与。”(注:见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C a 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希腊城邦中公共生活空间的重要,是同私人生活空间的弱化相伴随的。在建筑格局上,公 共建筑空间显得压倒一切;私人生活空间虽然存在,但相比起来,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例 如在斯巴达,男性公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公共空间里,在训练场上,在公共食堂里。就连 已婚男子同妻子相会,也得偷偷摸摸。公共空间同私人空间的对立,反映了城邦政治及其观 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集体的权利压倒个人的权利。公共空间强调的是积极的参与,公民 参与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城邦的鼓励。私人空间是个人自由的体现,而个人的自由同城邦政治 即使不是格格不入,至少也是相背离的。对城邦社会来说,私人空间是可疑的,它往往同反 动势力联系在一起。酒会是私人生活空间的一种主要形式,因而受到怀疑。公元前415 年,雅典发生毁坏神像案,迅即被与酒会联系在一起。报案者称,虽然没有目睹神像被毁的 过程,但以前经常看到阿西比德和他的同伴一起聚饮,其间诸多可疑言行,定为他们所为(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28,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443页。)。结果身为雅典将军的阿西比德及其同伴均被判有罪。苏格拉底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同私人 空间生活有关。他不仅是贵族酒会的常客,而且经常是主角。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他被 描绘成一个想法怪异的人物。他招收弟子,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教授颠倒黑白的技艺(注:《云》,94行以往(Aristophanes,Lysistrata and Other Plays,116f)。)。 显然,这样的私人生活空间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同城邦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
公共空间的重要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是同城邦的根本特征相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 政治动物”,实际上是指人是属于城邦的动物。脱离了城邦、生活在城邦集体之外者,要么 是动物,要么是鬼神(注:《政治学》,1252b34—1253a39,参见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7—9页。)。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在希腊城邦中,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参与的 自由,或以撒亚·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不存在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个人自由,即脱离 社 会的自由,或者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只是经历了基督教兴起、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之后,个人自由或“消极自由”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