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世界史的新解说
张树栋/唐舒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3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4年04期第82~89,65页
【作者简介】张树栋,1932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唐舒澜,1970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地区史、国别史研究生。
二战后,西方世界史界可谓新说层出不穷。除饮誉史坛的法国年鉴学派之外,英美同行也提出种种新说,企图重新解释世界历史的运行轨迹。近年,三位美国学者又提出崭新的理论框架,引人瞩目。斯塔夫里阿诺斯用全球观点观察世界历史,把“易接近性”视为推动文明起源和演进的主要驱动力;威廉·麦克尼尔将生态学引入历史研究领域,提出“微寄生物”理论和“巨型寄生物”理论,对学科交叉作了有益的尝试;马丁·伯纳尔笃信“非洲中心论”,认为非洲文明是西方古典文明之母,对传统的“雅里安模式”提出挑战。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重新诠释世界历史,体现了摒弃“欧洲中心论”的共同意向。这些学说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对我们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不无启发作用。
过去的已经不可改变,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却不断地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人新著相继问世。本文将要讨论的仅限于三位美国学者的耀眼之作。他们的作品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体现了摒弃“欧洲中心论”的鲜明意向,使人感到活泼有趣,耳目一新。
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全球通史”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术语,起初被称为“总体史”或“整体历史”,是指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地区中,对一定时段的历史进行地理、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综合研究,以反映这一整体的历史全貌。按照年鉴学派的观点,“全球通史”有时与世界通史同义,或者等同于进行研究的历史。①
从全球的角度研究历史是当代史学的一股新潮流。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us)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 History)、《全球通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Mankind's Past and Present:A Global History)就是这股新潮的代表。
“全球通史”打破传统的地区分界线,按历史活动本身的空间来描述历史。作者认为:把地球划分为若干大陆这种传统的方法,对地理学也许有用,但对世界史却没有多大的意义。正如世界史的结构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一样,世界历史地理也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发生那些历史运动的区域。世界史不仅仅是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世界史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拼凑。②世界史在结构上需要以对人类进展造成重大影响之历史运动为中心,基于同样理由,世界史在地理上涵盖的范围也须以发生这些历史运动的地区为中心。③要把握世界史必须打破条条块块。由此出发,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欧亚大陆是人类世界的中心。④欧亚大陆往来方便,不断面临被同化的威胁,被迫前进。其它地区相对闭塞,发展缓慢。
社会集团的文化进步与否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它社会集团;彼此之间交流途径愈多,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其它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易接近性”(accessility),因为它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他们可以沿袭习惯来生存。欧亚大陆的优势是“易接近性”,其地理环境使生长于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它们日渐互相威胁,互相促进。在这种背景下,这里孕育了人类灿烂的古典文明。游牧部族的活动把这些分散的文明联成一体,那些非欧亚地区的文明根本不能与它们相提并论。现代文明肇始于欧亚大陆一隅,欧亚民族的活动使分散的世界走向整体。
非欧亚大陆世界由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散布在大洋中的岛屿组成。根据易接近性原则,它们没有建立稳定联系,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那里的文明之火始终未能形成燎原之势。后来在欧亚文明影响下,它们才逐渐被纳入世界体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深受本世纪美国学术风气的影响。本世纪中期美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术倾向:对知识进行重新组织和调整,开展综合领域的研究,以及对不同领域的比较研究等,增加了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知识的传统划分受到“统一论”、“整体论”的影响。学科之间要求进一步融合,这些注重整体统一的观点对当时的专业化垄断现象形成了压力。斯塔夫里阿诺斯无疑在这种新的学术气氛中充当了桥梁专家和多面手的角色。
“全球通史”真正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作者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一章开头就指出:“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1500年以前,人类文明象星星渔火散布在地球上,彼此隔绝,大多数文明自生自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新旧大陆汇合之前的漫长的数千年中,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微不足道的,但各种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确实已经存在,只不过其程度随着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接踵而来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人类通迅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改进,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活动方式日益增多,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民族之间的距离缩小,人类的“地球村”依稀可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愈将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缩小。”⑤人类的未来不再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然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发展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⑥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互相作用的方面:纵向发展指由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形态依次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横向发展指与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相适应的各民族、各地区交换、交往的增加,闭塞和隔绝状态的突破、文化的扩散和汇合,由此导致整个世界的形成。总之,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阿克顿勋爵曾说:“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体;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它将照亮人们的灵魂:世界历史朝着诸民族均附属于它的方向发展”。⑦世界历史最终将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历史研究就得探究其形成的过程、发展趋势以及形成动因。“易接近性”原则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此。世界史的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过程,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只有从全球而不是地区或民族的角度研究历史才能揭示世界史的真谛。
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对斯氏的治史方法给予高度评价:“近年来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⑧
此外,在写作方法上,斯氏继承了西方世界史著作中大量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优良传统,通过多层次,多因素的纵横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各种偏见,较客观地论述了各民族对世界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全球通史”大量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与作者从全球文明的客观历史角度研究世界史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中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在比较的基础上,“全球通史”融合了传统世界史编纂模式,探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各种有影响力量的冲突和交汇。
“全球通史”中也有粗糙之笔。就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旧框架而言,斯氏作出了努力,但仍然带着“欧洲中心论”的烙印:他提出人类的历史“几乎等于”“欧亚文明史”,1500年以后“欧洲的进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欧洲是变化之源”。事实上,各种文明以不同的方式为建构世界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责任不应该全部由作者一人承担,当今的史学家们在确立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哪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一基本问题上仍是人各异词。我们缺少一个恰当而又得到一致承认的体系以便把世界文明表达为一个完整的整体。⑨尽管如此,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所代表的研究方法——用全球的观点囊括全球文明,将对世界史理论的建设和世界通史的编纂产生有益的影响。
除了从全球的角度研究世界历史,还可以从吸收、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构筑世界史体系。这种新近出现的跨学科研究造就了一批史坛新人,麦克尼尔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二、麦克尼尔的“寄生物理论”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是继汤因比之后享有盛名的世界史家,1971年后担任《现代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主编至今。他勤奋治学,著述甚丰,至1980年已出书19种。重要者:《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1963)、《世界史》(A World History,1971)、《疾病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1976)、《追求实力》(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h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1980)、《用生态与历史观看人类的生存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View,1980,讲演集)。
麦克尼尔“以新的角度回顾过去,以新的答案展望未来”,是一位颇具智慧与创造力的学者,通过《疾病与人类》一书研究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将生态平衡概念引入史学。麦氏研究历史上的疾病,是为了探求西班牙人所以能够击败阿兹忒克人并征服墨西哥和印加帝国的原因。他发现,当时爆发的天花使阿兹忒克人大量死亡,西班牙人却安然无恙,致使迷信的土著把他们奉若天神。然而西班牙人为何不受天花之害?新的问题将他的研究引向深入,终于提出一套有传染病学根据的假说,即“微寄生物”和“巨型寄生物“理论。
所谓“微寄生物”理论旨在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和寄生虫、细菌等微生物一样也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例如,当人类从狩猎、采集食物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后,许多寄生虫以及鼠、蚤之类也会随粮食和人口的增加而大量繁殖。它们传播疾病,抑制人口增长。瘟疫和疾病有地区性。某些疫疾流行于某个地区,久而久之,当地居民有了免疫力。一旦病原被带入陌生地区,当地居民因缺少抵抗力而容易感染甚至死亡。毁灭阿兹忒克人的天花,就是西班牙人带去的。因此,各地区的相互接触,一方面促成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使疾病有了传播的机会。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与东方接触,麻疹、天花便渐渐的流行于地中海世界。十三世纪,蒙古征服欧亚两洲,建立起欧亚接触的通道,欧洲却在十四世纪爆发了一场黑死病。
所谓“巨型寄生物”理论旨在说明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二者类似寄生虫和寄主,保持着微妙的、相生相克的平衡关系。大致说来,二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1000年以前)以“命令强制结构”为特色。各主要文明社会依据“权威原则”动员其经济与非经济资源。公前4000年,两河流域有了灌溉犁耕农业,进入定居生活。农产品的剩余,足以维持一个以祭司、战士为主的不事生产的寄生统治阶级。这是城市国家的初起。寄生的统治阶级以缓和的租税取代暴虐的掠夺,以稳定和寄主(广大农业人口)的关系。但基本上是以命令强制方式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这种动员是通过日益庞大的官僚组织进行的,两河流域的阿卡德王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秦、汉以及罗马帝国均为显例。大约在公元前后,各文明之间的远距离贸易日渐重要,统治者为了商业利益不得不依照市场价格原则调整强制命令的统治方式,这一原则在六、七世纪的阿拉伯世界表现得最清楚,穆罕默德就是商人出身。命令强制结构与市场结构并非单独存在、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寻求利益、创造财富上,市场商人远比强制结构下的官僚有效。于是,以“市场的结构”为特色的第二阶段(公元10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可以划分出来。此时,各主要国家依照市场原则行事。原来是世界上最都市化、工商最发达、技术最进步的中国,因官僚命令强制过于强大,市场自主性未能确立,市场结构的发展竟告夭折。西方自中古以来,命令强制结构就一直处于多元状态,城市商人得以在缝隙中不断成长。到1500年前后,统治者甚至要依靠商人和银行家的贷款维持军队和进行战争。市场结构达成自主,继而与强制的官僚结构相结合,使1500年以后的欧洲成为世界霸主,这种结合的典型代表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特点是权威原则再度复活,世界面临“权威服从”和“市场自由”的两难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命令强制结构又有凌驾市场结构的趋势。探讨这种原则的转变是《追求实力》的主要内容,此书即在剖析科技之进步以及军火生产的工业化、商业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大致言,十五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凭借船坚炮利主宰世界。十九世纪以后,军火生产走向工业化和商业化,各国在军备竞赛中实行计划经济,以期更能集中人力物力,得以求得生存,这种情形在两次大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至此,一种命令强制结构又逐渐超越市场结构。强有力的政府官僚组织以及庞大的工商组织,在现代化的交通和传播技术协助下,日益依照强制命令原则主宰着世界动向。1945年以后出现了原子武器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出路何在?麦克尼尔主张将命令强制结构发展到极限,组织世界政府或世界帝国,借此解散各国武器研究机构,控制核武器,将毁灭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至于人类终将建立世界帝国还是走向毁灭,非个人所能预料。麦氏只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使未来的决策者多少理智一点。⑩
运用自然科学知识进行人文学科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后期已颇为流行,不过由于简单照搬,致使人文学科过于强调科学化而失去自身的特点。虽然如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趋势却日渐明朗,尤其在战后自然科学持续超前的发展,给相对滞后的人文科学带来了新的气息。麦克尼尔的著作是这种趋势的反映,他在《疾病与人类》一书中第一次考察了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把自然科学的知识引入史学,从一个新的侧面考察人类历史,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可以预料,随着学科间更加密切的结合,“历史研究的范围不仅可以大大扩展与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11)
麦克尼尔所提出的“命令强制原则”不失为调动一切资源以确保统治稳固的强有力手段,但随着人类的进步,它的作用将不断弱化。麦氏基于数千年文明史而得出的强制原则与市场原则相辅相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权威原则再度复活,命令强制结构大有凌驾市场结构之上的趋势。为了追求实力,求得生存,各国竞相把科技力量投入杀伤性毁灭性武器的生产研究、使麦克尼尔深以为忧。此前,汤因比已就此作了深入研究,认为一个社会控制外部环境的力量增强后,环境的挑战减轻了,会产生新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控制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本身。科技进步不等于文明在生长,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技术进步、地理扩张而文明却在衰落的例证。麦克尼尔继承了汤因比的力量有效控制与文明延续之间关系的思想,尽管对这种力量的产物——核武器的威胁深感恐惧,但他仍然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就是文明生长的显例。可以说,庞大的官僚组织实际上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产物,各类组织机构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发挥科技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管理控制它的使用。因此宠大的组织本身就有抑制这种力量偏离正轨发展的潜在功能。尽管现状可忧,两人对西方文明的延续均有信心,不同的是汤因比把延续寄托在基督教上,认为它能调动人的精神道德的自觉;麦克尼尔则把希望寄托在“由一个愿意并能够单一控制核武器的世界帝国”身上,通过它来“解散武器研究机构和解除所有核弹头”。
麦克尼尔的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自我的层面,构建了新的世界史体系。同样地,一反“欧洲中心论”的伯纳尔,以其惊动西方史学界的“非洲中心论”重新解释希腊文明的起源。
三、所谓“非洲中心论”
近年来,西方产生了一种与“欧洲中心论”迥然相异的论断——“非洲中心论”。这种史观认为,源远流长的非洲文明是人类历史的发端和西方文明之母。至今见诸于教科书上的关于古希腊的一切辉煌创造,包括哲学、艺术、政治理论和法律观念等,都是古希腊人从“黑皮肤”的埃及人那里窃取的。当前的任务是建立以非洲人(或许还可以加上小亚细亚的古代闪米特人)为中心的世界史观,重建以“非洲中心论”为主题的世界史体系,以彻底推翻欧洲学者二百年来所经营的以“欧洲中心论”为框架的世界史体系。
“非洲中心论”出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其著名代表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Matin Bernal)。自1983年以来,他就陆续推出计划中的五卷本巨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12)在古希腊众人供奉的神——雅典娜前面前加上“黑色”这一修饰语,证明他笃信希腊文明的“黑色”血统。他指出:正是由于受到埃及文明的影响,希腊才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伯纳尔称这种真正的历史发展模式为“古代模式”,以区别于欧洲学者“捏造”的“雅里安模式”。一系列爆炸性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震动,(13)自然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埃及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她那辉煌灿烂的文化曾经吸引了许多希腊名流。希罗多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看一看他的希腊、埃及观,对于了解当代“非洲中心论”的思想渊源是大有帮助的。
1、传播说
古人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不过我认为,至少“较大的一部分是起源于埃及的”。(14)
海拉克列斯(埃及12神之一)之名不是源于希腊,是希腊人从埃及得到的,根据是此神的双亲均出身埃及。(15)
皮拉司吉人首先从埃及学到其他诸神的名字,此后希腊人又从皮拉司吉人学到这些名字。(16)
希腊人的“许多风习”是从埃及学来的。(17)埃及人好象是第一个举行庄严宗教集会、游行行列和法事的民族,“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切事物。”(18)
2、黑人说
埃及人是黑人。
多多那的女祭司说,两只黑鸽子,一只从埃及飞到利比亚,一只飞到多多那。其实它们是两位妇女。这里的人把这些妇女称为鸽子,她们是埃及人,所以是“黑”鸽子。底比斯(埃及的)和多多那的神托方式相似,而且从牺牲来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及学来的。”(19)
科尔启斯人是埃及人。根据之一,他们的皮肤是黑的,毛发是卷曲的。(20)
亚里士多德说:太黑的人是懦夫,比如说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21)
3、偷窃说
埃及人第一次教给人们说,人类灵魂是不朽的。当肉体死去,灵魂就进入正在生下的其他生物里面。希腊人也采用此说,就好象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我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但是不把他们记在这里。(22)
4、差异说
不但埃及的气候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而且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和他人相反。妇女去市场做买卖,男人在家里纺织;妇女用肩挑东西,男人用头顶东西;他们用脚和面,用手和泥;他族是人畜分开,埃及人和畜类住在一起;别国祭司留长发,埃及祭司要剃发。他们只吃牛肉、鹅肉,饮葡萄酒,不能吃鱼和蚕豆(因为不洁),埃及人绝不吃动物的头;写算时,希腊人从左到右运笔,埃及人从右到左。他们使用两种不同的文字,一种是圣体文,一种是俗体文。(23)
可见,希罗多德是一位朴素的文化传播论者:只要希腊与埃及存在相似之处,那就是来自埃及,因为后者比希腊古老得多,这个文化游动公式显示,原来他是当代“非洲中心论”的原祖。不过有一点对伯纳尔先生十分不利,这就是“差异说”。埃及人是黑人,所以”窃”自埃及的希腊文明是“黑色”文明,可是在希罗多德的公式中并没有这个要素。在他的看来,埃及是埃及,希腊是希腊,不但气候、习俗不同,甚至文字也不相同。
希腊文明深受埃及文明影响,已是公认的事实。在文化的互动中,每个民族不但有吸收力,同时也有改铸力,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仅举文字为例。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多数字母文字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埃及象形文字→西奈字母文字(塞姆人对象形文字的吸收与改铸)→腓尼基字母文字(对西奈文字的吸收与改铸)→希腊字母文字(希腊人对腓尼基文字的吸收与改铸)→拉丁字母文字(拉丁人对腓尼基和希腊文字的吸收与改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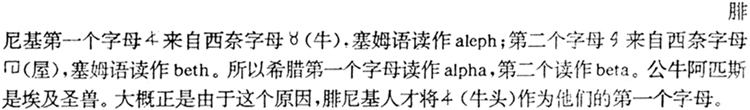 后来,拉丁人将(牛头)竖起来写作A(又一次改铸),于是成为许多字母文字的第一个字母。(24)由此可见,不但希腊字母实实在在具有“黑色”血统,其他字母文字也是如此,能不能说都是从埃及窃得的?
后来,拉丁人将(牛头)竖起来写作A(又一次改铸),于是成为许多字母文字的第一个字母。(24)由此可见,不但希腊字母实实在在具有“黑色”血统,其他字母文字也是如此,能不能说都是从埃及窃得的?
文明究竟是从一个中心向外辐射,还是不同的文明可以互动互补?这是伯纳尔先生面临的第二个不易超越的障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指出东方没有私人土地所有制存在,这是我们了解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以及实行君主专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埃及人利用尼罗河河水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共同用水是其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在埃及需要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古代埃及是一个实行等级制度的国家,僧侣位居第一等级。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和农民,受着经济、思想等的多重剥削和压迫,以至对现实世界丧失信心。“在埃及,凡是看不见的东西越来越被认为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东西。”(25)因此,以死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举不胜举。
在希腊,尽管有斯巴达的贵族政体,但是希腊的发展情况一般是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然后又过渡到僭主制与民主制。国王并没有很大的权力,他们须听从元老院的劝告,违背了习俗便不会不受惩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雅典国家“是由十个部落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的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26)雅典的民主自由思想由此产生,其政治社会的标准也深深地扎根于这种理性结构之中。雅典所以能在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海战中以少胜多,正是因为民主政治起了作用。民主政治鼓励着雅典公民多方面的积极性,公民对城邦的忠诚使社会团结受益匪浅。古希腊造就了大批先贤圣哲,他们博大精深的思想,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希腊翻开了古代历史新的一页,迸发着新兴文明的火花。
不难发现,部分吸收了埃及文明成果的希腊文明与埃及文明在总框架上似有天壤之别。“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释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27)没有理由认为希腊文明是黑人文明,更没有理由认为希腊文明窃自埃及。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和民族都不可能固步自封。愈是辉煌灿烂的文明,愈是能在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从异族吸取文化精华,以减少文化碰撞中的能量流失,达到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希腊文明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将“偷窃”理解为“改铸”。
“非洲中心论”给本来相对平衡的古代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迫使历史学家在已有的知识范围内对古代史中的重大问题作一次更深刻的反思和审视,这无疑有利于史学的发展。马丁·伯纳尔通过大量考古资料以及深入的鉴别、校勘,断定古代希腊和埃及文明具有子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勾勒了一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图,进一步展示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紧密联系,对批驳“欧洲中心论”具有积极意义。诚如剑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约翰·莱伊所言:“如果完全赞同伯纳尔的理论,那或许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但如果史学家们根本不理会伯纳尔的观点,那就证明他们是地道的外行。”(28)
但是,“非洲中心论”毕竟是以“黑人至上”为基点,企图以黑人这一种族为中心来构建世界历史的框架。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其学术性是可疑的。
每一代人都怀着当代的感受重新解释过去,只要人类生存一日,历史学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生存意义、前景目标的关注而不断在往昔典籍中探微索隐的精神就会继续一时。现实世界愈是纷繁复杂,人类文明愈是高度发达,就愈需要历史学家不失个人的立场,构建新的世界史观,以加深对人类自身的研究。斯塔夫里阿诺斯、威廉·麦克尼尔、马丁·伯纳尔等人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百家争鸣,百舸争流,通过大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古代史研究一定会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注释:
①②⑤⑦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页,第46页,第576页,第2页。
③邢义田:《西洋古代史参与资料》,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90页。
④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欧亚大陆不能只看成是包含欧、亚两洲,而是包含五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域: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⑧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5页,第248页。
⑩本节根据邢义田的两篇文章写成,见邢义田译著《西洋古代史参考资料》(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487页以下。
(11)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0页。
(12)第一卷《捏造古希腊(1785-1985)》(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ee 1785-1985)和第二卷《考古和文献证据》(The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分别于1987年和1991年问世,均由罗杰思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关于“非洲中心论”,沈宗美先生已有详细介绍,见《作为一种世界史观的“非洲中心论”》,《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14)(15)(16)(17)(18)(19)(20)(22)(23)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50段,第43段,第52段,第51段,第58段,第50段,第104段,第123段,第35~42段。
(21)《非洲通史》第2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27页。
(24)张树栋:“古代西亚国家”,李纯武等主编,《简明世界通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25)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集》第4卷,第114页。
(2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4页。
(28)引自沈宗美《作为一种世界史观的“非洲中心论”》,《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3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4年04期第82~89,65页
【作者简介】张树栋,1932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唐舒澜,1970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地区史、国别史研究生。
过去的已经不可改变,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却不断地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人新著相继问世。本文将要讨论的仅限于三位美国学者的耀眼之作。他们的作品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体现了摒弃“欧洲中心论”的鲜明意向,使人感到活泼有趣,耳目一新。
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全球通史”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术语,起初被称为“总体史”或“整体历史”,是指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地区中,对一定时段的历史进行地理、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综合研究,以反映这一整体的历史全貌。按照年鉴学派的观点,“全球通史”有时与世界通史同义,或者等同于进行研究的历史。①
从全球的角度研究历史是当代史学的一股新潮流。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us)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 History)、《全球通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Mankind's Past and Present:A Global History)就是这股新潮的代表。
“全球通史”打破传统的地区分界线,按历史活动本身的空间来描述历史。作者认为:把地球划分为若干大陆这种传统的方法,对地理学也许有用,但对世界史却没有多大的意义。正如世界史的结构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一样,世界历史地理也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发生那些历史运动的区域。世界史不仅仅是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世界史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拼凑。②世界史在结构上需要以对人类进展造成重大影响之历史运动为中心,基于同样理由,世界史在地理上涵盖的范围也须以发生这些历史运动的地区为中心。③要把握世界史必须打破条条块块。由此出发,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欧亚大陆是人类世界的中心。④欧亚大陆往来方便,不断面临被同化的威胁,被迫前进。其它地区相对闭塞,发展缓慢。
社会集团的文化进步与否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它社会集团;彼此之间交流途径愈多,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其它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易接近性”(accessility),因为它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他们可以沿袭习惯来生存。欧亚大陆的优势是“易接近性”,其地理环境使生长于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它们日渐互相威胁,互相促进。在这种背景下,这里孕育了人类灿烂的古典文明。游牧部族的活动把这些分散的文明联成一体,那些非欧亚地区的文明根本不能与它们相提并论。现代文明肇始于欧亚大陆一隅,欧亚民族的活动使分散的世界走向整体。
非欧亚大陆世界由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散布在大洋中的岛屿组成。根据易接近性原则,它们没有建立稳定联系,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那里的文明之火始终未能形成燎原之势。后来在欧亚文明影响下,它们才逐渐被纳入世界体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深受本世纪美国学术风气的影响。本世纪中期美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术倾向:对知识进行重新组织和调整,开展综合领域的研究,以及对不同领域的比较研究等,增加了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知识的传统划分受到“统一论”、“整体论”的影响。学科之间要求进一步融合,这些注重整体统一的观点对当时的专业化垄断现象形成了压力。斯塔夫里阿诺斯无疑在这种新的学术气氛中充当了桥梁专家和多面手的角色。
“全球通史”真正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作者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一章开头就指出:“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1500年以前,人类文明象星星渔火散布在地球上,彼此隔绝,大多数文明自生自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新旧大陆汇合之前的漫长的数千年中,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微不足道的,但各种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确实已经存在,只不过其程度随着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接踵而来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人类通迅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改进,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活动方式日益增多,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民族之间的距离缩小,人类的“地球村”依稀可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愈将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缩小。”⑤人类的未来不再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然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发展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⑥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互相作用的方面:纵向发展指由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形态依次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横向发展指与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相适应的各民族、各地区交换、交往的增加,闭塞和隔绝状态的突破、文化的扩散和汇合,由此导致整个世界的形成。总之,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阿克顿勋爵曾说:“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体;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它将照亮人们的灵魂:世界历史朝着诸民族均附属于它的方向发展”。⑦世界历史最终将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历史研究就得探究其形成的过程、发展趋势以及形成动因。“易接近性”原则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此。世界史的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过程,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只有从全球而不是地区或民族的角度研究历史才能揭示世界史的真谛。
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对斯氏的治史方法给予高度评价:“近年来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⑧
此外,在写作方法上,斯氏继承了西方世界史著作中大量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优良传统,通过多层次,多因素的纵横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各种偏见,较客观地论述了各民族对世界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全球通史”大量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与作者从全球文明的客观历史角度研究世界史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中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在比较的基础上,“全球通史”融合了传统世界史编纂模式,探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各种有影响力量的冲突和交汇。
“全球通史”中也有粗糙之笔。就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旧框架而言,斯氏作出了努力,但仍然带着“欧洲中心论”的烙印:他提出人类的历史“几乎等于”“欧亚文明史”,1500年以后“欧洲的进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欧洲是变化之源”。事实上,各种文明以不同的方式为建构世界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责任不应该全部由作者一人承担,当今的史学家们在确立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哪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一基本问题上仍是人各异词。我们缺少一个恰当而又得到一致承认的体系以便把世界文明表达为一个完整的整体。⑨尽管如此,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所代表的研究方法——用全球的观点囊括全球文明,将对世界史理论的建设和世界通史的编纂产生有益的影响。
除了从全球的角度研究世界历史,还可以从吸收、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构筑世界史体系。这种新近出现的跨学科研究造就了一批史坛新人,麦克尼尔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二、麦克尼尔的“寄生物理论”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是继汤因比之后享有盛名的世界史家,1971年后担任《现代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主编至今。他勤奋治学,著述甚丰,至1980年已出书19种。重要者:《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1963)、《世界史》(A World History,1971)、《疾病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1976)、《追求实力》(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h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1980)、《用生态与历史观看人类的生存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View,1980,讲演集)。
麦克尼尔“以新的角度回顾过去,以新的答案展望未来”,是一位颇具智慧与创造力的学者,通过《疾病与人类》一书研究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将生态平衡概念引入史学。麦氏研究历史上的疾病,是为了探求西班牙人所以能够击败阿兹忒克人并征服墨西哥和印加帝国的原因。他发现,当时爆发的天花使阿兹忒克人大量死亡,西班牙人却安然无恙,致使迷信的土著把他们奉若天神。然而西班牙人为何不受天花之害?新的问题将他的研究引向深入,终于提出一套有传染病学根据的假说,即“微寄生物”和“巨型寄生物“理论。
所谓“微寄生物”理论旨在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和寄生虫、细菌等微生物一样也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例如,当人类从狩猎、采集食物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后,许多寄生虫以及鼠、蚤之类也会随粮食和人口的增加而大量繁殖。它们传播疾病,抑制人口增长。瘟疫和疾病有地区性。某些疫疾流行于某个地区,久而久之,当地居民有了免疫力。一旦病原被带入陌生地区,当地居民因缺少抵抗力而容易感染甚至死亡。毁灭阿兹忒克人的天花,就是西班牙人带去的。因此,各地区的相互接触,一方面促成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使疾病有了传播的机会。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与东方接触,麻疹、天花便渐渐的流行于地中海世界。十三世纪,蒙古征服欧亚两洲,建立起欧亚接触的通道,欧洲却在十四世纪爆发了一场黑死病。
所谓“巨型寄生物”理论旨在说明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二者类似寄生虫和寄主,保持着微妙的、相生相克的平衡关系。大致说来,二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1000年以前)以“命令强制结构”为特色。各主要文明社会依据“权威原则”动员其经济与非经济资源。公前4000年,两河流域有了灌溉犁耕农业,进入定居生活。农产品的剩余,足以维持一个以祭司、战士为主的不事生产的寄生统治阶级。这是城市国家的初起。寄生的统治阶级以缓和的租税取代暴虐的掠夺,以稳定和寄主(广大农业人口)的关系。但基本上是以命令强制方式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这种动员是通过日益庞大的官僚组织进行的,两河流域的阿卡德王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秦、汉以及罗马帝国均为显例。大约在公元前后,各文明之间的远距离贸易日渐重要,统治者为了商业利益不得不依照市场价格原则调整强制命令的统治方式,这一原则在六、七世纪的阿拉伯世界表现得最清楚,穆罕默德就是商人出身。命令强制结构与市场结构并非单独存在、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寻求利益、创造财富上,市场商人远比强制结构下的官僚有效。于是,以“市场的结构”为特色的第二阶段(公元10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可以划分出来。此时,各主要国家依照市场原则行事。原来是世界上最都市化、工商最发达、技术最进步的中国,因官僚命令强制过于强大,市场自主性未能确立,市场结构的发展竟告夭折。西方自中古以来,命令强制结构就一直处于多元状态,城市商人得以在缝隙中不断成长。到1500年前后,统治者甚至要依靠商人和银行家的贷款维持军队和进行战争。市场结构达成自主,继而与强制的官僚结构相结合,使1500年以后的欧洲成为世界霸主,这种结合的典型代表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特点是权威原则再度复活,世界面临“权威服从”和“市场自由”的两难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命令强制结构又有凌驾市场结构的趋势。探讨这种原则的转变是《追求实力》的主要内容,此书即在剖析科技之进步以及军火生产的工业化、商业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大致言,十五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凭借船坚炮利主宰世界。十九世纪以后,军火生产走向工业化和商业化,各国在军备竞赛中实行计划经济,以期更能集中人力物力,得以求得生存,这种情形在两次大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至此,一种命令强制结构又逐渐超越市场结构。强有力的政府官僚组织以及庞大的工商组织,在现代化的交通和传播技术协助下,日益依照强制命令原则主宰着世界动向。1945年以后出现了原子武器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出路何在?麦克尼尔主张将命令强制结构发展到极限,组织世界政府或世界帝国,借此解散各国武器研究机构,控制核武器,将毁灭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至于人类终将建立世界帝国还是走向毁灭,非个人所能预料。麦氏只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使未来的决策者多少理智一点。⑩
运用自然科学知识进行人文学科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后期已颇为流行,不过由于简单照搬,致使人文学科过于强调科学化而失去自身的特点。虽然如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趋势却日渐明朗,尤其在战后自然科学持续超前的发展,给相对滞后的人文科学带来了新的气息。麦克尼尔的著作是这种趋势的反映,他在《疾病与人类》一书中第一次考察了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把自然科学的知识引入史学,从一个新的侧面考察人类历史,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可以预料,随着学科间更加密切的结合,“历史研究的范围不仅可以大大扩展与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11)
麦克尼尔所提出的“命令强制原则”不失为调动一切资源以确保统治稳固的强有力手段,但随着人类的进步,它的作用将不断弱化。麦氏基于数千年文明史而得出的强制原则与市场原则相辅相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权威原则再度复活,命令强制结构大有凌驾市场结构之上的趋势。为了追求实力,求得生存,各国竞相把科技力量投入杀伤性毁灭性武器的生产研究、使麦克尼尔深以为忧。此前,汤因比已就此作了深入研究,认为一个社会控制外部环境的力量增强后,环境的挑战减轻了,会产生新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控制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本身。科技进步不等于文明在生长,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技术进步、地理扩张而文明却在衰落的例证。麦克尼尔继承了汤因比的力量有效控制与文明延续之间关系的思想,尽管对这种力量的产物——核武器的威胁深感恐惧,但他仍然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就是文明生长的显例。可以说,庞大的官僚组织实际上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产物,各类组织机构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发挥科技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管理控制它的使用。因此宠大的组织本身就有抑制这种力量偏离正轨发展的潜在功能。尽管现状可忧,两人对西方文明的延续均有信心,不同的是汤因比把延续寄托在基督教上,认为它能调动人的精神道德的自觉;麦克尼尔则把希望寄托在“由一个愿意并能够单一控制核武器的世界帝国”身上,通过它来“解散武器研究机构和解除所有核弹头”。
麦克尼尔的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自我的层面,构建了新的世界史体系。同样地,一反“欧洲中心论”的伯纳尔,以其惊动西方史学界的“非洲中心论”重新解释希腊文明的起源。
三、所谓“非洲中心论”
近年来,西方产生了一种与“欧洲中心论”迥然相异的论断——“非洲中心论”。这种史观认为,源远流长的非洲文明是人类历史的发端和西方文明之母。至今见诸于教科书上的关于古希腊的一切辉煌创造,包括哲学、艺术、政治理论和法律观念等,都是古希腊人从“黑皮肤”的埃及人那里窃取的。当前的任务是建立以非洲人(或许还可以加上小亚细亚的古代闪米特人)为中心的世界史观,重建以“非洲中心论”为主题的世界史体系,以彻底推翻欧洲学者二百年来所经营的以“欧洲中心论”为框架的世界史体系。
“非洲中心论”出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其著名代表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Matin Bernal)。自1983年以来,他就陆续推出计划中的五卷本巨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12)在古希腊众人供奉的神——雅典娜前面前加上“黑色”这一修饰语,证明他笃信希腊文明的“黑色”血统。他指出:正是由于受到埃及文明的影响,希腊才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伯纳尔称这种真正的历史发展模式为“古代模式”,以区别于欧洲学者“捏造”的“雅里安模式”。一系列爆炸性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震动,(13)自然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埃及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她那辉煌灿烂的文化曾经吸引了许多希腊名流。希罗多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看一看他的希腊、埃及观,对于了解当代“非洲中心论”的思想渊源是大有帮助的。
1、传播说
古人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不过我认为,至少“较大的一部分是起源于埃及的”。(14)
海拉克列斯(埃及12神之一)之名不是源于希腊,是希腊人从埃及得到的,根据是此神的双亲均出身埃及。(15)
皮拉司吉人首先从埃及学到其他诸神的名字,此后希腊人又从皮拉司吉人学到这些名字。(16)
希腊人的“许多风习”是从埃及学来的。(17)埃及人好象是第一个举行庄严宗教集会、游行行列和法事的民族,“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切事物。”(18)
2、黑人说
埃及人是黑人。
多多那的女祭司说,两只黑鸽子,一只从埃及飞到利比亚,一只飞到多多那。其实它们是两位妇女。这里的人把这些妇女称为鸽子,她们是埃及人,所以是“黑”鸽子。底比斯(埃及的)和多多那的神托方式相似,而且从牺牲来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及学来的。”(19)
科尔启斯人是埃及人。根据之一,他们的皮肤是黑的,毛发是卷曲的。(20)
亚里士多德说:太黑的人是懦夫,比如说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21)
3、偷窃说
埃及人第一次教给人们说,人类灵魂是不朽的。当肉体死去,灵魂就进入正在生下的其他生物里面。希腊人也采用此说,就好象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我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但是不把他们记在这里。(22)
4、差异说
不但埃及的气候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而且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和他人相反。妇女去市场做买卖,男人在家里纺织;妇女用肩挑东西,男人用头顶东西;他们用脚和面,用手和泥;他族是人畜分开,埃及人和畜类住在一起;别国祭司留长发,埃及祭司要剃发。他们只吃牛肉、鹅肉,饮葡萄酒,不能吃鱼和蚕豆(因为不洁),埃及人绝不吃动物的头;写算时,希腊人从左到右运笔,埃及人从右到左。他们使用两种不同的文字,一种是圣体文,一种是俗体文。(23)
可见,希罗多德是一位朴素的文化传播论者:只要希腊与埃及存在相似之处,那就是来自埃及,因为后者比希腊古老得多,这个文化游动公式显示,原来他是当代“非洲中心论”的原祖。不过有一点对伯纳尔先生十分不利,这就是“差异说”。埃及人是黑人,所以”窃”自埃及的希腊文明是“黑色”文明,可是在希罗多德的公式中并没有这个要素。在他的看来,埃及是埃及,希腊是希腊,不但气候、习俗不同,甚至文字也不相同。
希腊文明深受埃及文明影响,已是公认的事实。在文化的互动中,每个民族不但有吸收力,同时也有改铸力,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仅举文字为例。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多数字母文字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埃及象形文字→西奈字母文字(塞姆人对象形文字的吸收与改铸)→腓尼基字母文字(对西奈文字的吸收与改铸)→希腊字母文字(希腊人对腓尼基文字的吸收与改铸)→拉丁字母文字(拉丁人对腓尼基和希腊文字的吸收与改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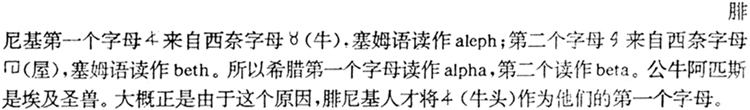 后来,拉丁人将(牛头)竖起来写作A(又一次改铸),于是成为许多字母文字的第一个字母。(24)由此可见,不但希腊字母实实在在具有“黑色”血统,其他字母文字也是如此,能不能说都是从埃及窃得的?
后来,拉丁人将(牛头)竖起来写作A(又一次改铸),于是成为许多字母文字的第一个字母。(24)由此可见,不但希腊字母实实在在具有“黑色”血统,其他字母文字也是如此,能不能说都是从埃及窃得的?文明究竟是从一个中心向外辐射,还是不同的文明可以互动互补?这是伯纳尔先生面临的第二个不易超越的障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指出东方没有私人土地所有制存在,这是我们了解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以及实行君主专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埃及人利用尼罗河河水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共同用水是其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在埃及需要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古代埃及是一个实行等级制度的国家,僧侣位居第一等级。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和农民,受着经济、思想等的多重剥削和压迫,以至对现实世界丧失信心。“在埃及,凡是看不见的东西越来越被认为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东西。”(25)因此,以死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举不胜举。
在希腊,尽管有斯巴达的贵族政体,但是希腊的发展情况一般是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然后又过渡到僭主制与民主制。国王并没有很大的权力,他们须听从元老院的劝告,违背了习俗便不会不受惩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雅典国家“是由十个部落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的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26)雅典的民主自由思想由此产生,其政治社会的标准也深深地扎根于这种理性结构之中。雅典所以能在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海战中以少胜多,正是因为民主政治起了作用。民主政治鼓励着雅典公民多方面的积极性,公民对城邦的忠诚使社会团结受益匪浅。古希腊造就了大批先贤圣哲,他们博大精深的思想,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希腊翻开了古代历史新的一页,迸发着新兴文明的火花。
不难发现,部分吸收了埃及文明成果的希腊文明与埃及文明在总框架上似有天壤之别。“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释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27)没有理由认为希腊文明是黑人文明,更没有理由认为希腊文明窃自埃及。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和民族都不可能固步自封。愈是辉煌灿烂的文明,愈是能在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从异族吸取文化精华,以减少文化碰撞中的能量流失,达到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希腊文明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将“偷窃”理解为“改铸”。
“非洲中心论”给本来相对平衡的古代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迫使历史学家在已有的知识范围内对古代史中的重大问题作一次更深刻的反思和审视,这无疑有利于史学的发展。马丁·伯纳尔通过大量考古资料以及深入的鉴别、校勘,断定古代希腊和埃及文明具有子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勾勒了一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图,进一步展示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紧密联系,对批驳“欧洲中心论”具有积极意义。诚如剑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约翰·莱伊所言:“如果完全赞同伯纳尔的理论,那或许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但如果史学家们根本不理会伯纳尔的观点,那就证明他们是地道的外行。”(28)
但是,“非洲中心论”毕竟是以“黑人至上”为基点,企图以黑人这一种族为中心来构建世界历史的框架。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其学术性是可疑的。
每一代人都怀着当代的感受重新解释过去,只要人类生存一日,历史学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生存意义、前景目标的关注而不断在往昔典籍中探微索隐的精神就会继续一时。现实世界愈是纷繁复杂,人类文明愈是高度发达,就愈需要历史学家不失个人的立场,构建新的世界史观,以加深对人类自身的研究。斯塔夫里阿诺斯、威廉·麦克尼尔、马丁·伯纳尔等人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百家争鸣,百舸争流,通过大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古代史研究一定会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注释:
①②⑤⑦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页,第46页,第576页,第2页。
③邢义田:《西洋古代史参与资料》,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90页。
④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欧亚大陆不能只看成是包含欧、亚两洲,而是包含五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域: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⑧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5页,第248页。
⑩本节根据邢义田的两篇文章写成,见邢义田译著《西洋古代史参考资料》(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487页以下。
(11)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0页。
(12)第一卷《捏造古希腊(1785-1985)》(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ee 1785-1985)和第二卷《考古和文献证据》(The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分别于1987年和1991年问世,均由罗杰思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关于“非洲中心论”,沈宗美先生已有详细介绍,见《作为一种世界史观的“非洲中心论”》,《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14)(15)(16)(17)(18)(19)(20)(22)(23)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50段,第43段,第52段,第51段,第58段,第50段,第104段,第123段,第35~42段。
(21)《非洲通史》第2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27页。
(24)张树栋:“古代西亚国家”,李纯武等主编,《简明世界通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25)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集》第4卷,第114页。
(2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4页。
(28)引自沈宗美《作为一种世界史观的“非洲中心论”》,《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