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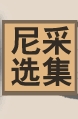
|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十四 ANAXAGORAS Ⅱ运动之谜 |
|
14.1 运动的真实性 为了好好地评估巴门尼德假设的非同寻常 的优点,不得不看看埃利亚派的对手们。如果向阿那克萨哥拉以及一切相信多基质统一的人提出"有多少基质"这个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困窘啊(巴门尼德却是不会遭此困窘的)。阿那克萨哥拉闭眼一跳,说:"无限多"。这样,他至少逃脱了一个困难得不堪想象的任务,即证明基质的确切数目。因为这个无限多必须不增、不变、亘古以来就存在着,所以,在这个假定中已包含着一个矛盾,即有那么一个已封闭的并已完成了的无限。 简言之,多、运动、无限在遭到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可惊原理谴责之后,又从放逐中返回,向巴门尼德的对手发射炮弹,试图给他们以致命的创伤。这些对手却显然没有准确估计到埃利亚派下述思想的可怕威力:"时间、运动、空间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能把所有这些东西设想为无限的,而不管它是无限大的还是可以无限细分的,一切无限的东西都不具有一个存在,都不存在。"无论谁只要严格领会"存在"一词的含义,且确认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完成了的无限"不可能存在,就不会怀疑这个思想。如果现实只在完成了的无限的形式中向我们显示万物,则可见现实是自相矛盾的,因而不具有真正的实在性。 倘若这些对手想反驳说:"可是,在你们的思维中毕竟有接续交替,因而你们的思维也不可能是实在的,故不能证明任何东西。"那么,巴门尼德也许会象康德在类似场合答复同一指责那样答道:"虽然我可以说,我的意念是彼此接续交替的,但这仅仅是指,我是在一种时间次序中,即遵循内感官形式意识到它们的。这却并不表示时间是某种自在之物,或是客观地依附在事物上面的规定性。"因此,必须区分纯粹的思维——它象巴门尼德的存在一样是非时间性的——和对这种思维的意识;后者已经被思维翻译成了假象的形式,也就是交替、多、运动的形式。 巴门尼德很可能利用了这条出路,那么,斯皮尔(A.Spir)用来反驳康德的理由(《思维与现实》第1卷),想必也曾经被用来反驳他: 然而,现在很清楚,第一,如果我的意识中并不同时显现一种各个前后相继的交替环节,那么,我对这种交替本身只能一无所知。所以,交替这个观念本身完全不是交替的,因而完全不同于我们观念的交替。第二,康德的假设中所包含着的荒谬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要惊叹他如何能对此视而不见。按照这一假设,凯撒大帝和苏格拉底并没有真死,他们就象两千年前一样活得好好的,只是由于我的"内感官"的安排,才显得好象已经死了。未来的人们现在已经活着了,如果说他们现在尚未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也是"内感官"的安排的责咎。主要的问题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本身的开始和结束,连同它的全部内感官和外感官,如何能仅仅存在于内感官的领悟之中?事实恰恰是,变化的实在性根本无法否认。把它从窗口送走,它又从锁眼溜进。固然可以说:"状态和观念只是看起来在变化而已",但这个假象本身仍是某种客观现存的东西,其中的交替具有无可怀疑的客观实在性,实际上确有某种东西前后相继。——此外,应该看到,全部理性批判只有在下述前提下才有理由和依据:我们的意念本身如其所是地向我们显现。因为,如果意念并非如它实际所是地向我们显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提出有关它的有效主张,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认识论以及对客观有效性进行"先验"考察。现在,这一点已不容怀疑:我们的意念本身是作为接续交替的东西显现给我们的。 阿那克萨哥拉对这种确凿无疑的交替和运动作出沉思,这逼使他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假设。意念显然是自我运动的,它们并不是被移动,在自身之外并无动因。他说,因此存在着某种自身之内包含着运动的原因和开端的东西。但是,他又观察到,这些意念不仅自我运动,而且还推动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肉体。这样,他通过最直接的经验发现了意念对于有广延的物质的作用,这一作用作为后者的运动而得以辨认。他把这一点看作事实,其次才感觉到要对这一事实作出解说。 14.2 最初的运动 对于阿那克萨哥拉来说,有一个世界上运动的规范图式就足够了;现在,他或则把这种运动看作由意念机能(即古希腊哲学中所称的"奴斯"nous)所引致的那些真正的、隔绝的本质的运动,或则把它看作由已被推动之物所引起的运动。 按他的基本假定,后一种情况,即运动和碰撞的机械传递,本身同样包含着一个问题,这一点他也许忽略了。碰撞作用的屡见不鲜大概钝化了他发现碰撞之谜的眼力。相反,他也许正确地感觉到了意念对于自在地存在着的基质的作用是大成问题的,甚至是荒谬的。因此他试图把这种作用归结为他认为显然行得通的机械移动和碰撞。 "奴斯"无论如何也是这样一种自在地存在着的基质,他把它描述为具有特殊"思维"属性的极其精细的物质。按照如此假定的性质,这种物质对于另一种物质的作用,与另一种基质施于第三种基质的作用,——即机械的、因压力和碰撞而产生运动的,也就得完全同属一类。现在他总算有了一种自我运动并且使他物运动的基质,其运动并非来自外界,也不依赖于他物。这样,现在这种自我运动该被如何设想,看来差不多是无所谓的了;也许就象极其精细的水银珠子的来回滚动吧。 在涉及运动的所有问题中,没有比运动的开端更棘手的问题了。我们虽则可以把其他一切运动设想为因果作用,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对最初的、开端的运动作出解释。对于机械运动来说,不管怎样,链上的最初一环决不可能是一种机械运动,因为这无非是意味着求助于"自因"(causa sui)这个荒谬概念。另一方面,一开始就把自我运动当作一笔终身嫁妆添加到永恒绝对之物身上,同样也无济于事。因为不能设想运动没有何去何从的方向,一定得把它设想为关系和条件。而倘若一物按其本性必然关涉到存在于它之外的某物,该物就不再是自在地存在的和绝对的。 面对这一困境,阿那克萨哥拉以为在那个自我运动的、一向无所依赖的"奴斯"身上找到了特别的救星。"奴斯"的本质是那么含糊不清,恰好足以掩饰对于它的假设实质上已包含着那个得被禁止的"自因"。经验观察表明,意念无疑不是一个自因,而是大脑的产物;把"精神"这种大脑的产物同它的起因分离开来,并且更妄断它在分离后仍然延续地存在着,实在是流于怪诞了。但这正是阿那克萨哥拉所做的;他忘记了大脑及其惊人的精微复杂,大脑结构的迂回精妙,而宣告所谓"自在的精神"。这个"自在的精神"可以自作抉择——这真是一个精彩的发现!它可以随时叫它之外的事物立刻开始运动,相反,涉及到它自己它却可以耗费极其漫长的时间。 总之,阿那克萨哥拉可以假定一个最初的运动时刻,作为一切所谓生成的起点,也就是永恒基质及其成分的一切变化(即一切移动和换位)的起点。虽则精神本身也是永恒的,但它不会被迫亘古以来就来回移动物质和物体,如此的折磨自己。不论长短,总必有过一个时间和一种状态,当时"奴斯"尚未施作用于物质,物质尚未运动。这就是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混乱时期。 |
|
□ 作者:尼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