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
万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1年02期第119~134页
【作者简介】万明(女),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 键 词】万历朝/援朝/战争/政治/态势
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朝鲜称为壬辰、丁酉之战,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是一场关系中、朝、日三国,规模空前的国际战争;是16世纪西方东来后,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明后期对外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一般说来,明亡于万历,亡于党争,大抵已成一种定论,但论明朝党争,历来主要集中于国本、三案等内部事务,往往忽略从当时重大对外事务反映出的明朝政治实态进行考察。实际上,外交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内政与外交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万历朝政治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援朝之战,在万历朝是作为军事三大功绩之一而载入史册的,迄今为止,关于这场战争,中国、日本、韩国学者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然而,主要聚焦于战争过程及其性质意义的考察,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明朝政治因素,没有将这一重大事件与明后期政治态势结合分析,对这场战争作为明后期政治的一个转折关键,鲜有揭示,也影响了深入剖析这场战争。本文的目的,是着意于党争以外的一个特定视角,从战争发展过程考察明朝政治实态,剖析其中透视出的明朝政治的诸多问题和明后期的政治态势,进而探讨这场对外战争在明朝政治以至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意蕴。
一、援朝之战与朝廷争议
援朝御倭之战,是以中国和朝鲜为一方,日本为另一方的一场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战争的意义,是应当完全肯定的。从国际背景来说,16世纪初,葡萄牙人扩张东来,占据了印度果阿,又强占了马来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打破了亚洲原有的格局,对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形成了冲击。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宿务登陆,不久占据了马尼拉,成为西方海外扩张对东方楔入的又一个钉子。此时东亚内部的关系结构也在酝酿发生变化。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日本平秀吉成为关白,次年,拜为太政大臣,赐姓丰臣。丰臣秀吉的上台,意味着东亚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对明朝在亚洲的朝贡体系构成新的威胁。丰臣秀吉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在基本统一了日本全国后,野心不断膨胀,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出兵近16万,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朝战争。诸多文献充分表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欲侵明,而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日本在亚洲的霸权,或者说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新的朝贡体系。(注:丰臣秀吉的侵华野心早就有所显露,并在战争发生前后多次表述。可参见〔日〕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役》,村田书店1927年版,第10-11页;《续本朝通鉴》卷二○六,见〔日〕池内宏《文禄庆长の役》正编第一,吉川弘文馆1987年版,第29页;《朝鲜征伐记》,见〔日〕池内宏《文禄庆长の役》正编第一,第79页;丰臣秀吉于天正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写给葡萄牙印度总督的信,见〔日〕池内宏《文禄庆长の役》正编第一,第130页;Blair,E.H.and Robertson,J.A.eds.:Philippine lsland 1493-1898,Cleveland,Ohio,1903-1909,Vol.IX,p.43;〔日〕中村荣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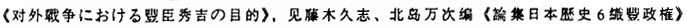 ,有精堂1974年版,第278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于是,一场关系中、日、朝三国,以朝鲜为战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由此爆发。
,有精堂1974年版,第278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于是,一场关系中、日、朝三国,以朝鲜为战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由此爆发。
为了探讨从战争折射出的明朝政治实态,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战前明朝政治情况。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重整朝政,取得了相当成效,给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张死后,改革终止,万历帝也在声色私欲方面,越走越远;张居正改革时所倾心任用的有所作为的官员,大都遭到贬斥,此后的政局中,从君到臣,自君臣之间至同僚之间,不谐和成为常态,严重侵蚀了朝廷政治。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七月,战争尚未正式开始,明朝刚刚得到日本即将进犯的报告,大学士许国等人即上本曰:
昨得浙江、福建抚臣共报日本倭奴招诱琉球入犯。盖缘顷年达虏猖獗于北,番戎蠢动于西,缅夷侵扰于南,未经大创,以致岛夷生心,乘间窃发中外。小臣争务攻击始焉,以卑凌尊继焉。以外制内,大臣纷纷求去,谁敢为国家任事者,伏乞大奋乾刚,申谕诸臣各修职业,勿恣胸臆。(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三八,万历十九年七月癸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
本中所述,正是援朝之战前夕,明朝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北部自俺答封贡,保持和平几二十年,但俺答死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扯力克袭顺义王封号,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夏,发生扯力克、火落赤等攻掠甘青地区的事件,被明朝革除了市赏;此后不久,爆发了宁夏哱拜叛乱和播州杨应龙反叛;更在此前,南部自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就有缅甸入犯云南。周边地区的动荡,给本不平静的朝廷掀起波澜,在对火落赤事件的处置上,辅臣间出现分歧,申时行主“款贡”,许国主“大创之”,于是均为对方门生所攻。(注:《明史》卷二一九《许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因此,大学士许国等疏中出现“大臣纷纷求去”,“谁敢为国家任事者”的忧愤之言。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拉开了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序幕。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战阶段,二是和谈阶段,三是再战阶段。每一阶段都伴随有激烈争议。无休止的纷争,构成了当时政局的鲜明特色。现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一)议出援
得知日本侵朝后,援与不援首先成为明廷争论的中心。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序》,《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影印出版。)。朝鲜国王不断派遣使臣到明廷求救。初得报告,兵部即上本报告,言日本侵朝“情形已真”,认为声东击西是“倭奴故态”,提醒“分道入犯,难免必无”,沿海一带必须加强防范。(注: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首《部垣台谏条议疏略》,台北学生书局据万历间原刊本1986年影印本。)此后,面对战争,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两种比较对立的反映,一是许多人清醒地看到了日本的野心所在,积极出谋划策。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认为:日本“以劲悍之贼,起倾国之兵,度其意料必置朝鲜于度外,而实欲坐收中国以自封也,然不遽寇中国而先寇朝鲜者,惧蹑其后也”,提出“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注:《经略复国要编》卷首《部垣台谏条议疏略》。)。兵科给事中刘道隆奏称:“宜急从台臣之请,召募勇敢之士万人以分布沿海要害之地……”(注:《经略复国要编》卷首《部垣台谏条议疏略》。)二是对出兵援朝提出异议,主要有兵科给事中许弘纲的上奏:“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蓠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请兵则赴援,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逃窜,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即欲立功异域,又臣等所大惑矣。”(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万历二十年七月庚申。)
吕坤在《忧危疏》中,曾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全面论述了出援的合理性:
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鲜之众为兵,就朝鲜之地为食,生聚训练,窥伺天朝,进则断漕运,据通仓,而绝我饷道;退则营全庆,守平壤,而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师坐困,此国家之大忧也。夫我合朝鲜,是为两我,两我尚怀胜负之忧;倭取朝鲜,是为两倭,两倭益费支持之力。臣以为朝鲜一失,其势必争。与其争于既亡之后,孰若救于未破之前;与其以单力而敌两倭,孰若并两力而敌一倭乎?乃朝鲜请兵而二三其说,许兵而延缓其期,或言为属国远戍,或言兵饷难图,谚曰:“小费偏惜;大费无益”。今朝鲜危在旦夕矣,而我计必须岁月。愿陛下早决大计,并力东征。(注:吕坤:《吕新吾先生文集》卷一,《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对于明朝内部的争论,朝鲜文献中也有记录。朝鲜陈奏使郑昆龙自北京回朝报告:
臣行到帝京,则朝廷论议尚不定,或以为当御于境上,或以为两夷之斗不必救。当初许弘刚上本力陈不可救之意,今则石尚书锐意征剿矣。(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二。)
在争议中,明朝最终决定出援。表面上看,朝鲜是与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属国,因此“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蓠,必争之地”(注: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倭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事实上,正如大学士王锡爵所言:“倭奴本情实欲占朝鲜以窥中国,中国兵之救朝鲜,实所以自救,非得已也。”(注: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明经世文编》卷三九四。)明朝出兵,是清楚地了解日本意图“谋犯中国”的结果。由于朝鲜通中国的道路,陆上只有辽东一路,而海上则有七路可达天津、山东等处,日军“可以旦夕渡鸭绿,内窥畿辅,外扞山东,皆举手之易”(注: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三九《占度载·度·四夷十七》,《中国兵书集成》据天启本影印。)。所以明朝出兵的直接目的,是“务以一倭不入为功”(注:《经略复国要编》卷首《万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敕》。)。也就是说,不仅具有道义上援助的意义,而且是为了本身安全势在必行。进一步考察,明朝对传统关系的质疑,实际构成了争议的关节点,援与不援,包含有维护还是放弃朝贡体制的问题,即直接关系到明朝外交体系的存亡,也正因为如此,明朝出援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议封贡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初,明军平壤大捷继之小挫后,即在朝鲜息战,当时朝廷内部对“讲和”未取得一致意见,疑虑重重,争议纷纭,争议中心是封与贡的问题。
接替经略宋应昌之职的顾养谦上疏,请封贡并许,即允许日本册封和通贡。他谈到兵部尚书石星派遣沈惟敬初入朝鲜和谈,就已经应许日方封贡,并提出:“贡道宜在宁波,关白宜封为日本王,请择才力武臣为使,以惟敬从,谕行长部倭尽归,与封贡如约”(注:《万历三大征考·倭上》。)。
事实是,自沈惟敬从日营回来,就有“和亲之说”,而仪制郎中何乔远等“忿请罢封”;给事中林材上本参“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鹏劾李如松“开封衅”;辽镇都御史韩取善疏言“倭情无定,请封贡并绝”。兵部尚书石星态度“亦张皇,恐关白不能就羁縻”(注:《万历三大征考·倭上》。)。顾养谦以宁波为贡道之议,遭到大学士沈一贯从乡土观念出发的坚决反对:“贡市一成,臣恐数十年后无宁波矣。”(注:沈一贯:《沈蛟门文集》卷一《论倭贡市事不可许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五。)争议持续,直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四月仍无结果,其间论争激烈。石星上疏辩,万历帝逮参劾者诸龙光下镇抚司狱,顾兼谦以封贡议请罢免,帝以孙鑛代之,并下旨:“这封贡都着罢了”(注:《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四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五月,帝命九卿、科道会议,在一片纷争中,也仅决定“以罢款议守为主,不得已而与款,犹当遵明旨,守部议”(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三,万历二十二年五月戊寅。)。
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究竟是封贡并许,还是只许封不许贡,这是关系到外交和平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日本侵略朝鲜,除了领土野心以外,达到通贡,即贸易,也是其重要的目的。朝鲜史籍记载日本人曾言:“中国久绝日本,不通朝贡,平秀吉以此心怀愤耻,欲起兵端。”(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卷一。)针对许不许通贡,明朝有人指出:“倭之求封者,因何岂图空名哉,终而为求贡也;其求贡者,因何岂真犯中国哉,不过利中国之货物而有无相易也,此其情也。”(注:张位:《张洪阳文集》,卷一《论东倭事情揭贴》,《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也有人进一步主张开贡市,请求委官到对马岛接受贡物,“许闽、浙、辽东大贾通市舶矣”。但是,多数大臣对嘉靖年间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恶行记忆深刻,因此,“在廷诸臣无虑数十人,皆力言其不可”(注:王德完:《王都谏奏疏》卷一《目击东倭衅隙专备御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就这样,拒绝许贡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当时就有人指出,沈惟敬和谈之初已答允日本人封与贡,因此不是一封就可以了事,于是提出加强备战(注:《王都谏奏疏》卷一《目击东倭衅隙专备御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应该说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
七月,在总督顾养谦的要求下,朝鲜国王也疏请许贡保国。此后,情形急转直下,万历帝下旨切责阻挠封贡的诸臣,将先前得罪的御史郭实等削职为民,诏日使小西飞入朝。明朝向小西飞提出三点:一是勒令日军全部返国;二是只给册封,不许通贡;三是要日本发誓不再侵犯朝鲜(注:《万历三大征考·倭上》。)。至这一年年底,通贡被否决,封议也才得到了确定。
(三)再议出援与撤兵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二月,册封失败,丰臣秀吉派兵大举侵朝,明朝不得已再议东征。然而,援与不援再度成为争议中心,而战争受挫时,又出现了撤兵之议。
当时,明朝不仅“连岁用兵,国计频绌”,而且“奈何封事一起,已将东征士马尽撤回籍”,当初南兵撤离时,还因没有给赏,发生了士兵鼓噪被杀1300人的事件,所以此时“人心迄愤惋,故召募鲜有应者”(注: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日本上》,《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本。)。朝中厌战情绪强烈。侍郎周思敬上疏,提出朝鲜之役“劳敝中国”,倡不救朝鲜之说。针对此说,御史周孔教提出“盖朝鲜与辽东接壤,乃我卧榻之侧也”,“若关系国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费”(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卷一《邪谋误国乞赐昭察以保长治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又一次为明朝必战争辩。当时朝廷任命兵部尚书邢玠为经略,发兵出援。到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明军中路败报传来,朝中大臣又开始了新一轮争论:有的以师久无功,提出撤兵;有的坚决主张进剿,夺取战争胜利。“其议撤兵者,抱虚内事外之忧,欲息肩而省耗费;其不欲撤兵者,执攘外安内之议,期灭贼以图全胜。”正值此时,福建巡抚金学曾奏报丰臣秀吉已死,日本国内将发生内乱,建议乘机征讨(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二八,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兵部上奏说,往年碧蹄馆之败是一次失误,“止兵之令一下,遂致不可收拾,而封议起”,比时“自失转败为胜之机”,而此时虽有败报,但“天下事尚可为”(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二八,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己酉。)。于是,明廷总结了初战阶段教训,决议乘势再战。
(四)议功罪
战争帷幕落下时有一段插曲,争议重心是功罪的判定,而实际上成为官员互相攻击的口实,而且争议愈演愈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正月,兵部赞画主事丁应泰论总督经略邢玠等“赂倭卖国”、尚书萧大亨与科道张辅之、姚文蔚等“朋谋欺罔”(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丙午。)。邢玠上《奏辩东征始末疏》,对丁应泰与左给事中徐观澜说他贿赂“倭酋”以讲和的诋毁做了辩解,并详述东征将士在战争最后阶段的功绩。疏中说明,直至战争最后一刻,朝中以首辅赵志皐为首,仍有讲和的想法;并揭露丁应泰“当临敌之时,一时欲斥总督斥巡抚斥监军斥总兵斥偏将,夫临敌易将且不可,泰乃举朝廷东征救属保邦之臣一网打尽”(注: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六《奏辩东征始末疏》,明刻本。)。而因丁疏中有“朝鲜阴结日本”之语,连朝鲜国王也上疏辩。此后,吏科给事中陈维春疏论丁应泰“党倭误国”,《明神宗实录》记:“乃应泰既以赂倭诋诸将,维春又以党倭诋应泰,嘻亦甚矣!”(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一,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对这种达到极端的互相攻击大不以为然。
研究政治的变化,不能不考虑在战争过程中的各种争议,聚讼难解之处,恰恰蕴涵了深刻的政治原因。自战事起,明朝议出援——议封贡——议再援——议撤兵——议功罪,大臣章疏数十百上,“聚讼无已时”构成了当时政治的鲜明特色。根据战事的演进,在战争不同发展阶段中,明朝先后争论的焦点不一,然而战与和始终是其核心,初战阶段表面看是以战为主,实际上和战并行;和谈阶段和议占上风,轻易撤军,放弃战备;再战阶段虽以战为主,进入相持后撤兵之议又起,直至出现偶然因素,促成了战争向有利明朝和朝鲜的方向发展。由于战争的复杂性,朝廷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将士以力击贼于外,议论者以舌击任事之臣于内”(注: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与宋桐冈论撤兵》,《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五。)的情况却是不正常的。这种政治纷争失去了是非的判断,使朝廷决策受到阻碍,政局混乱,更直接影响了对外战争的战局发展。
二、从战争过程看明朝政治的诸多问题
以这场战争为线索,考察万历中叶以后的政治实态,可以看到,明朝在战争中暴露出了政治的诸多问题。
(一)对外政策的游移性
在重大对外战争中,政策的确定,对战争胜败有着关键作用。如上所述,明朝出兵不仅具有道义上援助的意义,而且是为了本身安全,势在必行,更有维护朝贡体系的意义,那么战争理应进行得很坚决,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自战争一开始,虽然明朝决策出兵援朝,和谈却在政治秤盘上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相持,朝鲜战场和谈若明若暗,战和踯躅,充分表现出政策的游移性。
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战初似乎也曾同意出兵,但其实一直对和谈心存幻想,是朝中力主和平谈判解决的主和派代表。他首先派遣市井游客沈惟敬,到朝鲜“宣谕倭营”,寻机进行和谈(注:《两朝平攘录·日本上》。)。《朝鲜李朝实录》中记:
(六月)丁巳,时贼势日炽,天朝深忧之。兵部尚书石星密遣沈惟敬假称京营添住游击,托以探贼,实欲挺入贼营,与贼相见,啗贼讲和。惟敬简其驺从,疾驰渡江,言语张皇,是日馆于义州。(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二。)
由此可知,明朝大兵未到,和谈之使先行。确切地说,宋应昌受命为经略在万历二十年九月,而沈惟敬“始封议入倭”在二十年七月(注:黄汝亨:《寓林集》卷一七《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经略复国要编》附。),当沈惟敬在朝鲜进行和谈活动时,宋应昌正在辽东集结兵力。当时,沈惟敬与日方商定六十日内,不攻朝鲜(注:《经略复国要编》卷一○《讲明封贡疏》。)。经略宋应昌坚决主战,反对和谈,对沈惟敬说:“我奉命讨贼,知有血战耳,汝毋以身试法”,将沈系于军中,不许他再入倭营,同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注:焦竑:《献征录》卷五七,王锡爵《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冈宋公应昌神道碑铭》,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此后,虽然宋应昌与曾利用沈氏和议烟幕,争取时间调兵歼敌,但事实说明,明朝虽然决策出兵,内部主和派却实际干预了战争具体运作,使战与和在初战阶段成为并行的两条线索,而这两条线索决非是完全和谐的。
政策游移,后果十分恶劣,不仅造成朝鲜战场上和战并行,号令不一;更影响到明军遇有小挫即议撤兵,不能激励将士英勇作战,反而助长了畏敌情绪;而轻易撤兵,遗患无穷。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自宁夏平定哱拜回师奔赴朝鲜的提督李如松告捷于平壤,但不久,以轻敌败于碧蹄馆。碧蹄馆之败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其后明朝官军中士气低落,以李如松为首的主战派,也发生了变化。有学者指出,碧蹄馆之败从损失来说,并不算是大败。然而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实际影响确实很大。据朝鲜大臣柳成龙报告:“自碧蹄不利之后,天将之意,一向退缩,每委以天晴路干则当进,而犹疑京贼之多”(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七,《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三。)。更据明朝大臣王德完上疏“无奈碧蹄大败,魄散胆破,乃悚心坚意,惟封贡是图,不复言战斗事矣”(注:《王都谏奏疏》卷一《目击东倭衅隙专备御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战和并行,一旦战事遇有挫折,主和派势力就完全占据了上风,息兵和谈成为明朝统治层的决策。在李如松四月自平壤还兵开城前,沈惟敬已“再入京城,诱敌退兵”(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卷三。)。当时朝中大学士王锡爵等认为:“抑恐远追穷寇,全胜难期”(注:《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丙子。),提议撤兵(注:《献征录》卷五七,王锡爵在为宋应昌所作墓志铭中,曾为其辩冤,明确说请封与撤兵都与宋应昌无涉,是作为大学士的自己“议撤还”。);兵科右给事中侯庆远的疏中表述更为明确:“我与倭何仇,为属国勤数道之师,力争平壤,以权收王京,挈两都授之,存亡兴灭,义声赫海外矣。全师而归,所获实多”(注:《万历三大征考·倭上》。),都是认为战争应到此为止的论调。万历帝也错误地认为已到撤兵和谈的时机,并基本否决了宋应昌派兵留守的建议(注:《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三《慎留撤酌经权疏》:“以封以贡以羁縻之,有何不可?但留守,经也;封贡,权也;守经方可行权,无经则无权矣”,说明了留守对于封贡,也即对和谈的重要作用。但后来留守不成,不仅在明廷,也有其他原因,如在朝鲜保留军队的条件等方面原因。),下令让朝鲜国王还都王京,整兵自守,明军“以次撤归”。就这样,明朝不但没有抓住战机,反而“一意主款”,撤兵回国,给了日本人以喘息机会,遂使战争无限延长。至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军再次大举在朝鲜登陆,明朝以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为经略,出兵朝鲜,遇到的是“兵已尽撤,募者不至”,在三月,辽东总督孙鑛“所征南北官兵止一万九千余名”(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八,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这个数字只及先前宋应昌集结兵马的1/3。初战阶段轻易撤兵的恶果完全显示了出来。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再战阶段的明朝政策也仍具有游移不定的特征,稍有败报,就出现新的摇摆(注:这从兵科给事中姚文蔚言“东事结局无期,和议潜行未息”,以及蔚山之战后,日军气焰嚣张,朝中撤兵减饷议论又起,适可得到证明。更好的证明,是邢玠《奏辩东征始末疏》中揭露直至战争最后一刻,首辅“志 以密勿大臣,不为请兵请饷,亦附合抗章欲减兵退守”。)。
以密勿大臣,不为请兵请饷,亦附合抗章欲减兵退守”。)。
政策的游移,深刻影响了战局发展,贻误了战机,造成战与和都不能成功的严重后果,更拖长了战争过程,加大了战争耗费。由此反映出明朝从皇帝到中枢决策大臣,都始终对外交和平解决寄托希望,随时准备妥协,说明了此时明王朝对外关系的被动保守状态,已经完全丧失了明初外交上的恢宏气魄,只是勉强维护朝贡体制而已。
(二)和谈中不辨真相
在这场战争中,和谈时期远过于战争状态是一大特点。主和派以石星为首、以沈惟敬为中心的和谈活动,实际贯穿了援朝之战的前两个阶段,即初战与和谈阶段。碧蹄馆之役以后,和议形成主流,此后,明朝在和谈中不辨真相,不能知己知彼,决策失当在所难免,根本达不到和平的目的。
首先,明朝对敌情不明。如前所述,经过激烈的争议,明朝决定册封丰臣秀吉。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二月,万历帝以“临淮侯勋卫署都督佥事”李宗城、“五军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杨方亨为正副使,前往日本,对丰臣秀吉“封以日本国王,赐以冠服、金印、诰命”(注:《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三年二月辛亥,中华书局1958年版。)。然而,确切地说,此时丰臣秀吉意欲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朝贡体系,明朝朝贡体系已被破坏殆尽,明朝仍然运用传统的册封方式,甚至不许通贡而试图羁縻日本,当然不能满足丰臣秀吉野心,因此不能解决问题。但兵部尚书石星一味听信沈惟敬,天真地以为只要册封成功,就可得到和平。直至此时,明朝不清楚沈惟敬早已答应日本的不仅是册封一桩,对日本方面在和谈期间提出的七个条件也懵然无知,处于被动的地位(注:参见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623页。)。使团出使后滞留朝鲜,一直拖延不能渡海去日本,日本在朝鲜的军队也迟迟不撤,明朝不知所以,朝堂之上空发议论。于慎行曾评论当时统治层对日外交无知的状况:
关白封贡之议,一时台谏部司上疏力谏,月无虚牍。争之诚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消化泛论事理,至于日本沿革,绝不考究。有谓祖训绝其朝贡,二百年来不与相通者,览之为失笑……四夷封略,在礼部验封司,大司马石公徒欲取效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为何国,关白为若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啽呓。(注:《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四年五月丙子。)
明朝册封之事归礼部掌管,不归兵部,石星不了解日本与中国的既往关系,甚至对日本是什么国家,关白是什么人都弄不清,就独揽封事;而朝中大臣只凭揣摩,不知底里,就事论事,大谈封贡,这种对外交事务的无知,直接影响到战争过程的决策,难怪于慎行发出“以此御难,何以为国”的慨叹。
就这样,和谈使团一去无音讯,明朝在空洞理论的氛围中,一直对传来的消息将信将疑。直到正使逃去,明朝改由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使团才终于在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六月渡海进入日本,此时距首次任命派遣使团已有一年多了。九月,使团在日本完成了对丰臣秀吉的册封。当狂妄的丰臣秀吉得知明朝仅封他为日本国王时大怒,直云:“明主册封不满我意,然姑忍之,朝鲜和讲,我决不许。册使亦不可留,明日速发遣。再起大兵,以灭朝鲜。”(注:〔日〕《秀吉谱》,见〔日〕川口长孺《征韩伟略》卷四,《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本。)日本不能达到目的,自然不肯罢休,和谈破裂不可避免,战争再起成为必然,丰臣秀吉迅速策划新一轮战事。而明朝使节杨方亨回国后,只言册封成功,明廷直至战报到来,方知和谈失败。
其次,明朝对己情也不明。在重大外交活动中,不仅任人不当,而且偏听偏信,以致误国。“国家托付非人”(注:《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明朝先后派出的使节沈惟敬、李宗城,就是两个典型。
在与日本的和谈中,明朝重用的沈惟敬来历不明(注:一说沈是浙江平湖人,本名家支属,少年曾从军,后入京师,喜好炼丹,与方士和无赖交游,由于石星妾父也好炼丹,故相识荐于石星;一说出身浙江嘉兴或平湖,客游北京,与妓吴澹如相通,澹如仆郑四曾去日本,了解日本情况,石星妾父袁茂到澹如家玩时,听沈惟敬谈论时事,就如去过日本一样,于是推荐给石星。前说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沈惟敬》,中华书局1959年版;后说见《两朝平攘录·日本上》。),他至多只是听到过一些有关日本的传闻,却得到兵部尚书石星的完全信任,委以使节重任,且言听计从。明朝时人云:“司马既以封贡事委之,言无不合。言路交攻,不为动”(注:《万历野获编》卷一七《沈惟敬》。)。就连朝鲜大臣都知道,石星一向偏听沈惟敬,“虽朝议多异,而星奋然以身当之”(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卷三。)。明朝大军未行,石星先遣他入朝,借机和谈,而他一到朝鲜,就给了朝鲜大臣吴亿龄“其人貌寝而口如悬河,盖辩士也。且言与平义智、平秀吉相知云矣”的印象(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二。)。他对日本人夸下“不云和亲,辄曰乞降”之海口不能兑现,于是一直“时露时藏”,不断蒙骗朝廷,隐瞒日方意图,使明朝相信可以和平解决战争,从朝鲜战场撤兵,并派出册封使团。使团出使后,沈惟敬因未被任为册使,大失所望,而册封使李宗城不把他放在眼里,更使他心生怨恨。使团被拖延渡海去日本,“不曰风潮不顺,则曰宫殿未成;不曰礼节未备,则曰不可不加慎重”(注:《两朝平攘录·日本上》。)。在此期间,沈惟敬在内倚仗石星,在外密令人扬言封事失败,促使李宗城畏惧逃跑,使自己得以被任为使团副使,并先行渡海赴日。他教杨方亨谨记“支吾中国,奉承日本而已”之语(注:《两朝平攘录·日本上》。),充分暴露了卖国的丑恶面目。册封失败后,沈惟敬妄图再次欺瞒朝廷,“乃私市珍异为秀吉物以诡报”,打算像以往那样私购物品假作国礼,但日军已开始陆续渡海,他继续蒙骗不成,又欲投降日军,最终伏法。总之,沈惟敬根本不熟悉外交事务,只知尔虞我诈的伎俩,明朝却让他担负外交重任,并对他偏听偏信,以致以私害公,两边欺瞒,误国不浅。
李宗城是临淮侯长子,系朱元璋外甥曹国公李文忠的后裔(注:《明史》卷一○五《功臣世表》一:“李宗城以使朝鲜逃归,论死,不得袭。”)。他以祖上功勋署五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五军都督府官员的贵族化和素质的低下,在明中叶以后已引起朝廷正直官员的注意,这批人平时无事,恬不知兵,遇有战事,束手无策。李宗城正是这样一个纨绔子弟。他以石星推荐,出任册封使。出使后,他本性难移,昏昏终日,溺于酒色,以致陷入日本人圈套。日军迟迟不撤兵,“遂羁二使于倭营一载,度其窘,以危言惕之”(注:《武备志》卷二三九《占度载·度·四夷十七》。),而李宗城竟“日夜涕泣思归”,后听沈惟敬营千总谢隆传言,日本20万大兵将至,信以为真,夜弃印信诏敕,变服逃跑(注:《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乙卯;《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杨方亨疏曰:“正使李宗城又被谢隆之惑,蓦然潜出”;而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记:“封日本册使李宗城自倭营逃。山东巡按李思孝报沈惟敬被关白缚绑,李宗城闻知,夜即弃印逃出。”说明李宗城听到的传闻还有沈惟敬先行渡海被缚的内容。)。消息传至京师,御史周孔教言:“奈何当时儿戏视之,而以一竖子辱命,取轻外国,如是尚为中国有人乎?”(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卷一《东封误国亟赐议处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一语点破了明朝外交用人之不明。
(三)出援大臣的掣肘状态
战争初起,明朝先期入援的3000骑兵兵败平壤,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举朝震动,京师戒严。明朝决定以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出师征讨。据称:当时“中外汹汹,计画无所出,朝廷悬赏格,有能复朝鲜者,赏银万两,封伯爵世袭。朝臣举股战舌虩虩无应者,乃稽首推公往”(注:黄汝亨:《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宋应昌受命于危难之际,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计划出战时,已有御史郭实上疏,“虑远道颠危,劾司马尝试国事,指陈切直”(注:宋懋澄:《九龠集·别集》卷四《东师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宋应昌不得已,上《辞经略疏》。
出援后,宋应昌受到多方面的牵制,束缚住了手脚,曾叹:“夫国家亦时常用兵矣,曳襟掣肘未有若今日。”(注:《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二《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事实上,明朝内部争议纷纭,延伸于外,在外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行其是,文臣与武将、南兵与北兵的矛盾尖锐,严重削弱了明朝军力,也暴露了明朝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初战阶段,不仅有沈惟敬直接受命于中枢、与日军的单独媾和活动,而且李如松以总兵提督军务,也“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史载他谒见宋应昌时不按规矩礼节,“以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注:《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传》。)。这说明了战争中文臣与武将关系的紧张状态。明朝历来是以文臣出掌军务,武将地位在文臣之下,李如松是镇守辽东多年的李成梁之子,手握重兵,骄横抗礼,根本不把宋应昌放在眼里。王锡爵曾述经略宋应昌的难处有六,其中有“边臣伸缩自由,而经略则空名客寄,俯仰随人”,“李氏盛满,人心不附,而又立万金之赏,悬封拜之格,忌宁远者并以忌公”等等(注:《献征录》卷五七,王锡爵:《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冈宋公应昌神道碑铭》。)。此外,据朝鲜史籍记载,由于李如松是北将,在首战平壤这样关键的战役中,曾“痛抑南军,恐其成功”;当碧蹄之败,李如松轻敌冒进,“所领皆北骑,无火器,只持短剑钝劣”(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卷三。)。后来顾养谦疏中谈到宋李二人之功,言问题出在“南北将领分为二心,彼此媒孽”(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一,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壬辰。)。不和谐的将帅、将领关系自然会影响到战争中的配合,并直接影响到战事成败。
最重要的牵制,是来自中枢。息战以后,不少朝中大臣指责援军统帅宋应昌和李如松。兵科给事中吴文梓攻李如松等“不能相机决策,以彰天威”,反而纷然讲和无已,畏缩退怯,并攻宋应昌“款贡未奉明旨”(注:《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六,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己巳。)。实际上,宋应昌自有难言之隐。鲜为人知的是,在息战撤兵问题上,作为主和派首脑的兵部尚书石星曾利用手中权力,对朝鲜战场兵力调动作了釜底抽薪,他“密令惟敬议款,忌公转战,所调兵悉令支解”。于是,中枢的掣肘,使在外统帅实际不可能再战,“一意主战守之事,封贡一着,置之不论”(注:《经略复国要编》卷一四《奏缴敕谕符验疏》。)的宋应昌,不得不慨叹:“令我以疲卒当锐师,抑徒手杀贼耶?!”(注:黄汝亨:《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当时他这个经略的所能,只有上疏力图留兵戍守,以保已有战争胜利果实了。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年底,朝廷下令宋应昌、李如松回国。宋应昌在四次上疏乞归后,于次年回故里,从此“绝口不谭东事”(注:黄汝亨:《寓林集》卷一五《明兵部左侍郎经略桐冈宋公配顾淑人墓志铭》。)。这不仅是宋应昌个人的悲剧,也是明朝政治的悲剧。
初战的经略如此,再战的经略邢玠又如何呢?邢玠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进击以失败报闻,受到攻击,诸葛元声评论说:“邢公之计虑是矣,其调度则未也。”(注:《两朝平攘录·日本下》。)认为邢玠不等水兵来到,进行水陆夹攻,轻易出战是完全错误的。然邢玠自有难处,他曾上疏自辩道:
堂堂天朝于岛夷何有,但倭之人情一,我之人情二。一则始终不挠,可以持久;二则自相攻击,能不摇撼?恐久不得战,哄然群议,不曰师老则曰财匮,不曰进迟则曰退速,或忌妒之口又从而飞语流谤,其间人情忧讥,畏罪之不暇,又何镇静观成之可望,此我所以持久不如倭也。(注: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二《申明进止机宜疏》。)
直接道出了朝中官员互相攻扞,纷乱异常,不仅使决策受到障碍,更形成对具体运作的动辄掣肘状态,出援大臣顾虑重重,不能进退自如,甚至无所措手足。
军事上战场瞬息万变,在外统帅最忌多方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即使有抱负,也不可能得到施展。当时人冯琦曰:“嗟嗟世议何极之有,功之未成,则曰是固不可成也;既成,即曰是不难,非但不难,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且以退罪之。”(注:冯琦:《冯北海文集》卷三《赠大司马邢昆田平倭奏凯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二。)这道出了任事者的艰难处境。整个战争过程里,战争指挥层发生多次重大人事调整,造成“七易岁,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将,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的局面(注:《冯北海文集》卷三《赠大司马邢昆田平倭奏凯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二。),出现既无良臣、又无良将的恶性循环。数度更换大臣,影响战局发展,更是明朝政策过程不能顺畅的表现。
(四)朝廷中枢的改组
作为决策群体,难解难分的内部冲突,深刻影响了皇帝与大臣的关系逐渐向不可逆转的恶化方向发展,在战争进程中,明朝政治上层的重组也在进行中,战争实际体现了明朝政治深层结构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万历帝明显厌倦了政治,对内阁和言官失去信任,章奏留中不报。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首辅赵志臯等上疏说:“迩年以来,章奏有留中不下者,而近日为甚”(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丙午。)。当时十多个本章,推补二十余员大臣,皆留中不报。此后赵志臯多次奏请,都如泥牛入海。这是皇帝与内阁及群臣矛盾加深,上下日益隔阂的结果。不仅如此,万历帝更转而信任宦官,将兴趣移到了搜刮财宝上面。一年以后,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上疏,指出部院科道之职渐轻的趋势,具体而言,部院缺位不补,且“争正事则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则十人而九不点”;科道情况也大体相同:“五科都给事中久虚不补”,“西台东省列署半空”;而为了开矿之事,抚按上奏被阻隔,千户、中官反参奏抚按,纲纪为之倒置(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万历二十四年十月戊寅。)。万历帝怠政,造成了君臣相猜,上下不交,政事荒废的局面,出现近乎瘫痪的政治状况。
皇帝怠政,中枢又如何呢?自册封使出,迟迟不见动静,力主册封的兵部尚书石星,理所当然成为群臣指责的对象,而一直依违于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实际是主和派支持者的内阁,也一并受到攻击。李植上疏直指册封决策失误,指出“遣勘使,罢中枢”,指责辅臣赵志臯、枢臣石星“百计阻言战守”,一误再误,建议立即选官会同督抚、巡按“前往探勘”,并请皇上令赵志臯、石星致仕,回籍听勘(注:李植:《李中丞奏疏》卷一《东封失策选枢臣以图战守事》,《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五。)。御史周孔教也论石星误国,言词激烈,矛头直指内阁。他认为石星罪不容赦,“而罪之首者”是辅臣赵志臯,指责赵志臯“曲昵私交,引用同乡宋应昌”;因“语侵志臯”,贬逐郭实;纵容石星,许封日本。提出“勒令二臣致仕”(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卷一《东封误国亟赐议处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册封失败后,朝中更是“议者蜂起”,“劾星者必及志臯”(注:《明史》卷二一九《赵志臯传》。)。战事再起,大小九卿科道官会议的结论是“欲救朝鲜,须亟更枢管,石星前事多误,方寸已灰,军国机宜,岂堪再误”(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丙子。)。于是石星下狱,而弹劾赵志臯者不断。
战争进入再战的胶着状态,直接导致了明朝政治最高层的人事变动。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兵二十余万分五路入朝,七月,闲山要害失守,直接威胁到中国沿海,战争形势严峻。十一月,经略邢玠调集明军分为三协,在朝鲜军配合下,向日军发动攻击。这场战役“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结果却“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注:《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究其缘由,战争由胜转败,首先是经理杨镐“震惧”逃跑,随后“士皆奔窜”,造成明军损失过半(注:《武备志》卷二三九《占度载·度·四夷十七》。)。战后,杨镐隐瞒伤亡实情不报,“诡以捷闻”,于是赞画主事丁应泰疏劾杨镐“丧师党欺”,述及“当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三,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丁巳。)。所谓“党欺”,直指内阁大学士张位。他指责张位招权纳贿,接受杨镐贿赂,力荐杨镐经理朝鲜军务,夺情视事,并与杨镐密书来往(注:《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与此同时,还揭发大学士沈一贯也私下致书杨镐,甚至将御史汪先岸论杨镐的“拟票留中之旨”,也秘密给杨镐看,因此并劾张位与沈一贯“扶同作奸”(注:《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此疏道出了明朝吏治腐败,以及内阁贪污受贿的状况。万历帝得报大怒,罢免杨镐,令大学士张位免职闲住,沈一贯引咎得免。战争至此,导致了明朝政治最高层的人事变动。
战争进行七年中,统治上层政治分化重组也加速进行,明朝内阁组成主要是赵志臯、张位、沈一贯。其间王锡爵、陈于陛有短暂的在阁时间。赵与张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入阁,陈与沈于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入阁。值得注意的是,赵与张都是由申时行“密荐”入阁的,吏部尚书陆光祖曾为此上言,认为阁臣例由廷推,而二人由密荐而入,“恐开徇私植党之门”(注:《国榷》卷七五,万历十九年九月壬午。)。二十二年,由吏部会推阁臣,推举了王家屏、孙丕扬等七人,当时在阁的王锡爵与赵志臯、张位,不愿孙丕扬等正直大臣入阁,以违制将这次会推作废,主持此事的文选郎中顾宪成由此削籍,而入阁的是陈于陛和沈一贯,陈入阁不久即去世。赵志臯为首辅的内阁,实际是主和派的支持者,因此,内阁因援朝之战成为论争对象,自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赵养病,张削职闲住,沈告罪后为万历所挽留,自从张居正死后,至此,可以说内阁衰微到了极点。
以上事实说明,在战争过程中暴露出明朝政治的诸多问题:皇帝怠政,内阁衰微,大僚空署,上下乖离;士大夫丧失伦理道德,受贿谋私,朝廷之上,各不相谋,争端迭起,务实乏人;面对燃眉的军政大事,中枢运转失常,影响决策过程以及具体政策运行,致使对外战争战和不力,数年无功;凡此种种,无一不表明明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折射出的是明朝政治的一种自在的衰落过程和政治危机。
三、战争与明后期的政治态势
明朝出兵援救朝鲜,中朝联合打败了入侵朝鲜的日本侵略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应当充分肯定。
当时人冯琦曾从对外政治意义的角度,评论这场战争:
古人通西域以制虏,今日救属国以制倭。倭自南,虏自北,即使偶发而畸至,彼谋不合,我力不分,于中国自疥癣耳……载籍以来,亦有出师大海外救人者否?主上之于朝鲜,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国,摧一强国,以风示四夷之君长,莫不稽首内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译之朝,国势强,国体尊。(注:冯琦:《冯北海文集》卷三《赠大司马邢昆田平倭奏凯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二。)
战争胜利者是中国与朝鲜,但胜利又给了万历朝什么呢?显然是明朝威信的提高,重要的还有在明朝朝贡体系中,始终被认为是异己的日本终于被战败,从而使困扰明朝自开国以来200多年的倭寇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历史表层下深藏的事实,就会发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清楚地反映出了明后期的政治态势。明朝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可以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战争胜利后远不是升平有望,事实上,这场战争成为明朝衰落的标志。作为明后期政治的一个关键转折,体现在内外两方面。
(一)在外交上,援朝之战是明朝与日、朝关系,也即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标志着明朝朝贡体系的破坏殆尽。
明初建立的朝贡体系在历史上规模空前,而明朝遭遇的外扰也是史无前例的。对朝贡体制下明朝与属国的关系,明太祖在祖训中曾有明确的不征规定,而万历时面临战祸,明朝不得已加入了战争。明朝大臣于慎行在一篇贺功叙中说:“圣上为华夷共主,宠绥四方……故知今日出师之名义而后上之威德益弘明。”(注:于慎行:《于文定公文集》卷一《贺中丞丘泽万公征倭功成叙》,《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九。)援朝之战是维护明朝朝贡体系之战,也即具有维护明朝君主在东亚的“华夷共主”形象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在外国土地上作战的事例,体现了明朝对外政策与以往王朝政策的历史继承性。在唐朝时期,唐与朝鲜的关系中,出兵是为了自卫,“守在四夷”,同时也是为了“兴亡继绝”,负有道义的使命;到了明朝,仍然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出兵援朝。战后,明朝遵循对朝鲜无寸土要求,就这一意义上说,万历朝继承了历史上传统对外政策,也遵循了明太祖的祖训。
根据文献记载分析,领土扩张是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主要动机,吞并朝鲜,灭亡明朝,将中、朝领土纳入日本版图,在亚洲内陆建立日本帝国,这一野心前所未有,是日本侵华的嚆矢,并在以后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实施。进一步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其背后显示出的是国际贸易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日本丰臣秀吉的兴起,与西方东来引起亚洲内部格局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说明初已受到日本倭寇的骚扰,那只是非国家组织的小规模侵扰,那么这一次战争是西方东来后日本的国家行为;日本活跃的国际贸易活动的背后,是经济需求的巨大驱动,而日本发动战争,丰臣秀吉的侵华野心,可以视为世界性的连锁运动。西方东来,亚洲旧有的国际关系体系被破坏殆尽,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尚未建立,日本乘机逸出朝贡体系,成为东亚侵略扩张的因素,向明朝挑战。可以说,16世纪的明朝不仅面临西方东来的挑战,而且同时遭遇到东亚的挑战,换言之,明朝遭遇的是东西侵略扩张的风暴。不仅朝贡体系受到致命冲击,而且本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就这一意义而言,援朝御倭之战,不仅是维护明朝朝贡体系之战,也是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形势下的国土保卫战。
总之,这是一场全新意义的战争,既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挑战,又是西方东来以后东西方贸易大炽,经济需求增长的反映。经历东西两面夹击的外在挑战,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已被破坏殆尽。
(二)在内政上,援朝之战多方面显示了明朝政治弱点,昭示了王朝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更是明后期由治及乱政治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成为明亡的重要契机。
政治衰退是一种长期的过程,而内外矛盾的互动,全面酝酿了明朝的统治危机。战后,明朝国力大减,危机日重,迅速走向灭亡。
1.这场战争,将整个中国都不同程度的卷入了其中,战争的旷日持久,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所谓万历三大征(注:即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实际上三者性质、规模并不相同,宁夏、播州均是平叛战争,涉及范围、进行时间相对狭少。),惟有援朝之战是出援外国,参与国际战争,耗费也最大。据时人估计:“朝鲜要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余万两”(注:王德完:《王都谏奏疏》卷一《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另据记载,仅再战阶段邢玠出任经略的四年间,就“用饷银八百余万两,军资不与焉”(注:《武备志》卷二三九《占度载·度·四夷十七》。)。正如退居山林的大学士王家屏所揭露的:“远迩绎骚,公私靡敝如是,曾未闻其出一奇,当一队,收一战之功,而山人游客尽拜官矣;厮养隶卒尽富贵矣。车骑戈甲,连数镇之师,半委山谷矣;金钱刍粟,倾数百万之积,尽填沟壑矣;兵老财殚,智穷计绌,乃始听用狎邪无赖之辈,往来倭营,哀求和好,今日议贡,明日议封,外坠狡夷之牢笼,而内坐守寸步难移之困局……今时势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注:王家屏:《王文端公文集》卷一《答顾冲庵论东事》,《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三。)。又如谈迁所云:“越国救邻,自昔所难,况海外乎?东征之役,苍皇七载,民力殚竭。”(注:《国榷》卷七八,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己巳。)明朝为了这场战争转饷半天下,其间国家财政日绌,为此除加重赋税以外,令官吏捐俸,大臣出钱助工以救缓急。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吏部以东事告急,鬻爵开事例(注:《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四年五月辛巳。)。同年,万历帝派遣中官开矿于畿内,榷税于通州,从此矿监税使四出,多方搜刮,民穷财尽,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混乱状态。援朝之战结束不到半年,就出现了民变,导致了王朝的统治危机。
2.“征师索饷,远迩震动,夷狄盗贼,莫不生心”(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三,万历二十七年四月辛未。),是战争的直接后果。从此时起,明朝来自辽东的威胁日甚一日。
在援朝之战中,明朝将辽东兵力大都抽调到朝鲜,投入援朝之战,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乘机发展,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打败叶赫九部,攻下了讷颜部。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他被晋封为龙虎将军。援朝之战后,为战争胜利冲昏头脑的明朝统治者认为辽东已安,因此更放松了警惕。明朝君臣深深陷入内部纠纷,对努尔哈赤的蚕食坐大毫不注意,看不到努尔哈赤的日益强大将成为与明朝抗衡的力量。正是在这种疏于防范的情况下,努尔哈赤逐渐控制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势力发展迅速,以致尾大不掉,无法控制,最终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成为明朝统治的重要威胁。
综上所述,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卓有成效;中叶以后,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统治阶级上层的纷争,既是政治分裂的表现,又是政治腐败的结果。而改革后明朝走向衰亡的明显标志正是此战。
四、结束语
这场战争是日本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朝联合反侵略取得胜利。时至今日,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侵略者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规律长存,援朝之战体现出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然而,这场战争表明的明朝政治实态,透视出明后期的政治态势,反映出明朝内外关系的变化,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对晚明政治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如果说党争亡国,还不如说以这场战争为分水岭,标志着明朝政治、军事、财政等全面危机,揭开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帷幕更为确切。
以对外重大政治事件为透视点,沿着不同以往的党争与内部事务的路径展开,考察明后期的政治实态,从中可得出重要启示:明亡于万历,万历朝是重要转折时期。但是,明亡于党争这一司空见惯的定论,却不足以说明问题。在援朝之战如此重大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明朝政治机制的低能和政治的腐败暴露无遗,说明在世界发展变化的背景下,即使在东林与齐、楚、浙党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明朝政治已显示出衰败的态势。一言以概之,明朝以制度化存在的政治机制问题已凸显了出来。进一步探析,明后期无论是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都会引起无休止的纷争,这完全是因为政治机制本身的失衡,而党争只是一个表现形式,是政治分化改组进一步加剧的结果,而并非是原因。自张居正改革后,至援朝之战,明朝政治的保守与腐败已掩盖了活力,政治的一种自在的衰亡过程清晰可见。^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1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1年02期第119~134页
【作者简介】万明(女),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援朝之战,是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也是中朝第一次联合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世界变化背景下中、日、朝关系,即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本文从战争的视角,对明朝的政治实态进行考察,剖析诸多政治问题,并以此为枢纽,透视明朝后期政治走向衰败的态势。 |
一般说来,明亡于万历,亡于党争,大抵已成一种定论,但论明朝党争,历来主要集中于国本、三案等内部事务,往往忽略从当时重大对外事务反映出的明朝政治实态进行考察。实际上,外交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内政与外交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万历朝政治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援朝之战,在万历朝是作为军事三大功绩之一而载入史册的,迄今为止,关于这场战争,中国、日本、韩国学者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然而,主要聚焦于战争过程及其性质意义的考察,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明朝政治因素,没有将这一重大事件与明后期政治态势结合分析,对这场战争作为明后期政治的一个转折关键,鲜有揭示,也影响了深入剖析这场战争。本文的目的,是着意于党争以外的一个特定视角,从战争发展过程考察明朝政治实态,剖析其中透视出的明朝政治的诸多问题和明后期的政治态势,进而探讨这场对外战争在明朝政治以至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意蕴。
一、援朝之战与朝廷争议
援朝御倭之战,是以中国和朝鲜为一方,日本为另一方的一场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战争的意义,是应当完全肯定的。从国际背景来说,16世纪初,葡萄牙人扩张东来,占据了印度果阿,又强占了马来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打破了亚洲原有的格局,对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形成了冲击。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宿务登陆,不久占据了马尼拉,成为西方海外扩张对东方楔入的又一个钉子。此时东亚内部的关系结构也在酝酿发生变化。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日本平秀吉成为关白,次年,拜为太政大臣,赐姓丰臣。丰臣秀吉的上台,意味着东亚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对明朝在亚洲的朝贡体系构成新的威胁。丰臣秀吉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在基本统一了日本全国后,野心不断膨胀,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出兵近16万,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朝战争。诸多文献充分表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欲侵明,而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日本在亚洲的霸权,或者说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新的朝贡体系。(注:丰臣秀吉的侵华野心早就有所显露,并在战争发生前后多次表述。可参见〔日〕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役》,村田书店1927年版,第10-11页;《续本朝通鉴》卷二○六,见〔日〕池内宏《文禄庆长の役》正编第一,吉川弘文馆1987年版,第29页;《朝鲜征伐记》,见〔日〕池内宏《文禄庆长の役》正编第一,第79页;丰臣秀吉于天正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写给葡萄牙印度总督的信,见〔日〕池内宏《文禄庆长の役》正编第一,第130页;Blair,E.H.and Robertson,J.A.eds.:Philippine lsland 1493-1898,Cleveland,Ohio,1903-1909,Vol.IX,p.43;〔日〕中村荣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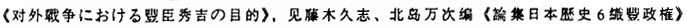 ,有精堂1974年版,第278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于是,一场关系中、日、朝三国,以朝鲜为战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由此爆发。
,有精堂1974年版,第278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于是,一场关系中、日、朝三国,以朝鲜为战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由此爆发。为了探讨从战争折射出的明朝政治实态,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战前明朝政治情况。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重整朝政,取得了相当成效,给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张死后,改革终止,万历帝也在声色私欲方面,越走越远;张居正改革时所倾心任用的有所作为的官员,大都遭到贬斥,此后的政局中,从君到臣,自君臣之间至同僚之间,不谐和成为常态,严重侵蚀了朝廷政治。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七月,战争尚未正式开始,明朝刚刚得到日本即将进犯的报告,大学士许国等人即上本曰:
昨得浙江、福建抚臣共报日本倭奴招诱琉球入犯。盖缘顷年达虏猖獗于北,番戎蠢动于西,缅夷侵扰于南,未经大创,以致岛夷生心,乘间窃发中外。小臣争务攻击始焉,以卑凌尊继焉。以外制内,大臣纷纷求去,谁敢为国家任事者,伏乞大奋乾刚,申谕诸臣各修职业,勿恣胸臆。(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三八,万历十九年七月癸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
本中所述,正是援朝之战前夕,明朝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北部自俺答封贡,保持和平几二十年,但俺答死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扯力克袭顺义王封号,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夏,发生扯力克、火落赤等攻掠甘青地区的事件,被明朝革除了市赏;此后不久,爆发了宁夏哱拜叛乱和播州杨应龙反叛;更在此前,南部自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就有缅甸入犯云南。周边地区的动荡,给本不平静的朝廷掀起波澜,在对火落赤事件的处置上,辅臣间出现分歧,申时行主“款贡”,许国主“大创之”,于是均为对方门生所攻。(注:《明史》卷二一九《许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因此,大学士许国等疏中出现“大臣纷纷求去”,“谁敢为国家任事者”的忧愤之言。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拉开了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序幕。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战阶段,二是和谈阶段,三是再战阶段。每一阶段都伴随有激烈争议。无休止的纷争,构成了当时政局的鲜明特色。现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一)议出援
得知日本侵朝后,援与不援首先成为明廷争论的中心。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序》,《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影印出版。)。朝鲜国王不断派遣使臣到明廷求救。初得报告,兵部即上本报告,言日本侵朝“情形已真”,认为声东击西是“倭奴故态”,提醒“分道入犯,难免必无”,沿海一带必须加强防范。(注: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首《部垣台谏条议疏略》,台北学生书局据万历间原刊本1986年影印本。)此后,面对战争,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两种比较对立的反映,一是许多人清醒地看到了日本的野心所在,积极出谋划策。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认为:日本“以劲悍之贼,起倾国之兵,度其意料必置朝鲜于度外,而实欲坐收中国以自封也,然不遽寇中国而先寇朝鲜者,惧蹑其后也”,提出“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注:《经略复国要编》卷首《部垣台谏条议疏略》。)。兵科给事中刘道隆奏称:“宜急从台臣之请,召募勇敢之士万人以分布沿海要害之地……”(注:《经略复国要编》卷首《部垣台谏条议疏略》。)二是对出兵援朝提出异议,主要有兵科给事中许弘纲的上奏:“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蓠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请兵则赴援,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逃窜,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即欲立功异域,又臣等所大惑矣。”(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万历二十年七月庚申。)
吕坤在《忧危疏》中,曾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全面论述了出援的合理性:
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鲜之众为兵,就朝鲜之地为食,生聚训练,窥伺天朝,进则断漕运,据通仓,而绝我饷道;退则营全庆,守平壤,而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师坐困,此国家之大忧也。夫我合朝鲜,是为两我,两我尚怀胜负之忧;倭取朝鲜,是为两倭,两倭益费支持之力。臣以为朝鲜一失,其势必争。与其争于既亡之后,孰若救于未破之前;与其以单力而敌两倭,孰若并两力而敌一倭乎?乃朝鲜请兵而二三其说,许兵而延缓其期,或言为属国远戍,或言兵饷难图,谚曰:“小费偏惜;大费无益”。今朝鲜危在旦夕矣,而我计必须岁月。愿陛下早决大计,并力东征。(注:吕坤:《吕新吾先生文集》卷一,《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对于明朝内部的争论,朝鲜文献中也有记录。朝鲜陈奏使郑昆龙自北京回朝报告:
臣行到帝京,则朝廷论议尚不定,或以为当御于境上,或以为两夷之斗不必救。当初许弘刚上本力陈不可救之意,今则石尚书锐意征剿矣。(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二。)
在争议中,明朝最终决定出援。表面上看,朝鲜是与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属国,因此“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蓠,必争之地”(注: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倭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事实上,正如大学士王锡爵所言:“倭奴本情实欲占朝鲜以窥中国,中国兵之救朝鲜,实所以自救,非得已也。”(注: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明经世文编》卷三九四。)明朝出兵,是清楚地了解日本意图“谋犯中国”的结果。由于朝鲜通中国的道路,陆上只有辽东一路,而海上则有七路可达天津、山东等处,日军“可以旦夕渡鸭绿,内窥畿辅,外扞山东,皆举手之易”(注: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三九《占度载·度·四夷十七》,《中国兵书集成》据天启本影印。)。所以明朝出兵的直接目的,是“务以一倭不入为功”(注:《经略复国要编》卷首《万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敕》。)。也就是说,不仅具有道义上援助的意义,而且是为了本身安全势在必行。进一步考察,明朝对传统关系的质疑,实际构成了争议的关节点,援与不援,包含有维护还是放弃朝贡体制的问题,即直接关系到明朝外交体系的存亡,也正因为如此,明朝出援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议封贡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初,明军平壤大捷继之小挫后,即在朝鲜息战,当时朝廷内部对“讲和”未取得一致意见,疑虑重重,争议纷纭,争议中心是封与贡的问题。
接替经略宋应昌之职的顾养谦上疏,请封贡并许,即允许日本册封和通贡。他谈到兵部尚书石星派遣沈惟敬初入朝鲜和谈,就已经应许日方封贡,并提出:“贡道宜在宁波,关白宜封为日本王,请择才力武臣为使,以惟敬从,谕行长部倭尽归,与封贡如约”(注:《万历三大征考·倭上》。)。
事实是,自沈惟敬从日营回来,就有“和亲之说”,而仪制郎中何乔远等“忿请罢封”;给事中林材上本参“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鹏劾李如松“开封衅”;辽镇都御史韩取善疏言“倭情无定,请封贡并绝”。兵部尚书石星态度“亦张皇,恐关白不能就羁縻”(注:《万历三大征考·倭上》。)。顾养谦以宁波为贡道之议,遭到大学士沈一贯从乡土观念出发的坚决反对:“贡市一成,臣恐数十年后无宁波矣。”(注:沈一贯:《沈蛟门文集》卷一《论倭贡市事不可许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五。)争议持续,直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四月仍无结果,其间论争激烈。石星上疏辩,万历帝逮参劾者诸龙光下镇抚司狱,顾兼谦以封贡议请罢免,帝以孙鑛代之,并下旨:“这封贡都着罢了”(注:《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四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五月,帝命九卿、科道会议,在一片纷争中,也仅决定“以罢款议守为主,不得已而与款,犹当遵明旨,守部议”(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三,万历二十二年五月戊寅。)。
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究竟是封贡并许,还是只许封不许贡,这是关系到外交和平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日本侵略朝鲜,除了领土野心以外,达到通贡,即贸易,也是其重要的目的。朝鲜史籍记载日本人曾言:“中国久绝日本,不通朝贡,平秀吉以此心怀愤耻,欲起兵端。”(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卷一。)针对许不许通贡,明朝有人指出:“倭之求封者,因何岂图空名哉,终而为求贡也;其求贡者,因何岂真犯中国哉,不过利中国之货物而有无相易也,此其情也。”(注:张位:《张洪阳文集》,卷一《论东倭事情揭贴》,《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也有人进一步主张开贡市,请求委官到对马岛接受贡物,“许闽、浙、辽东大贾通市舶矣”。但是,多数大臣对嘉靖年间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恶行记忆深刻,因此,“在廷诸臣无虑数十人,皆力言其不可”(注:王德完:《王都谏奏疏》卷一《目击东倭衅隙专备御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就这样,拒绝许贡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当时就有人指出,沈惟敬和谈之初已答允日本人封与贡,因此不是一封就可以了事,于是提出加强备战(注:《王都谏奏疏》卷一《目击东倭衅隙专备御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应该说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
七月,在总督顾养谦的要求下,朝鲜国王也疏请许贡保国。此后,情形急转直下,万历帝下旨切责阻挠封贡的诸臣,将先前得罪的御史郭实等削职为民,诏日使小西飞入朝。明朝向小西飞提出三点:一是勒令日军全部返国;二是只给册封,不许通贡;三是要日本发誓不再侵犯朝鲜(注:《万历三大征考·倭上》。)。至这一年年底,通贡被否决,封议也才得到了确定。
(三)再议出援与撤兵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二月,册封失败,丰臣秀吉派兵大举侵朝,明朝不得已再议东征。然而,援与不援再度成为争议中心,而战争受挫时,又出现了撤兵之议。
当时,明朝不仅“连岁用兵,国计频绌”,而且“奈何封事一起,已将东征士马尽撤回籍”,当初南兵撤离时,还因没有给赏,发生了士兵鼓噪被杀1300人的事件,所以此时“人心迄愤惋,故召募鲜有应者”(注: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日本上》,《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本。)。朝中厌战情绪强烈。侍郎周思敬上疏,提出朝鲜之役“劳敝中国”,倡不救朝鲜之说。针对此说,御史周孔教提出“盖朝鲜与辽东接壤,乃我卧榻之侧也”,“若关系国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费”(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卷一《邪谋误国乞赐昭察以保长治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又一次为明朝必战争辩。当时朝廷任命兵部尚书邢玠为经略,发兵出援。到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明军中路败报传来,朝中大臣又开始了新一轮争论:有的以师久无功,提出撤兵;有的坚决主张进剿,夺取战争胜利。“其议撤兵者,抱虚内事外之忧,欲息肩而省耗费;其不欲撤兵者,执攘外安内之议,期灭贼以图全胜。”正值此时,福建巡抚金学曾奏报丰臣秀吉已死,日本国内将发生内乱,建议乘机征讨(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二八,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兵部上奏说,往年碧蹄馆之败是一次失误,“止兵之令一下,遂致不可收拾,而封议起”,比时“自失转败为胜之机”,而此时虽有败报,但“天下事尚可为”(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二八,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己酉。)。于是,明廷总结了初战阶段教训,决议乘势再战。
(四)议功罪
战争帷幕落下时有一段插曲,争议重心是功罪的判定,而实际上成为官员互相攻击的口实,而且争议愈演愈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正月,兵部赞画主事丁应泰论总督经略邢玠等“赂倭卖国”、尚书萧大亨与科道张辅之、姚文蔚等“朋谋欺罔”(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丙午。)。邢玠上《奏辩东征始末疏》,对丁应泰与左给事中徐观澜说他贿赂“倭酋”以讲和的诋毁做了辩解,并详述东征将士在战争最后阶段的功绩。疏中说明,直至战争最后一刻,朝中以首辅赵志皐为首,仍有讲和的想法;并揭露丁应泰“当临敌之时,一时欲斥总督斥巡抚斥监军斥总兵斥偏将,夫临敌易将且不可,泰乃举朝廷东征救属保邦之臣一网打尽”(注: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六《奏辩东征始末疏》,明刻本。)。而因丁疏中有“朝鲜阴结日本”之语,连朝鲜国王也上疏辩。此后,吏科给事中陈维春疏论丁应泰“党倭误国”,《明神宗实录》记:“乃应泰既以赂倭诋诸将,维春又以党倭诋应泰,嘻亦甚矣!”(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一,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对这种达到极端的互相攻击大不以为然。
研究政治的变化,不能不考虑在战争过程中的各种争议,聚讼难解之处,恰恰蕴涵了深刻的政治原因。自战事起,明朝议出援——议封贡——议再援——议撤兵——议功罪,大臣章疏数十百上,“聚讼无已时”构成了当时政治的鲜明特色。根据战事的演进,在战争不同发展阶段中,明朝先后争论的焦点不一,然而战与和始终是其核心,初战阶段表面看是以战为主,实际上和战并行;和谈阶段和议占上风,轻易撤军,放弃战备;再战阶段虽以战为主,进入相持后撤兵之议又起,直至出现偶然因素,促成了战争向有利明朝和朝鲜的方向发展。由于战争的复杂性,朝廷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将士以力击贼于外,议论者以舌击任事之臣于内”(注: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与宋桐冈论撤兵》,《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五。)的情况却是不正常的。这种政治纷争失去了是非的判断,使朝廷决策受到阻碍,政局混乱,更直接影响了对外战争的战局发展。
二、从战争过程看明朝政治的诸多问题
以这场战争为线索,考察万历中叶以后的政治实态,可以看到,明朝在战争中暴露出了政治的诸多问题。
(一)对外政策的游移性
在重大对外战争中,政策的确定,对战争胜败有着关键作用。如上所述,明朝出兵不仅具有道义上援助的意义,而且是为了本身安全,势在必行,更有维护朝贡体系的意义,那么战争理应进行得很坚决,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自战争一开始,虽然明朝决策出兵援朝,和谈却在政治秤盘上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相持,朝鲜战场和谈若明若暗,战和踯躅,充分表现出政策的游移性。
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战初似乎也曾同意出兵,但其实一直对和谈心存幻想,是朝中力主和平谈判解决的主和派代表。他首先派遣市井游客沈惟敬,到朝鲜“宣谕倭营”,寻机进行和谈(注:《两朝平攘录·日本上》。)。《朝鲜李朝实录》中记:
(六月)丁巳,时贼势日炽,天朝深忧之。兵部尚书石星密遣沈惟敬假称京营添住游击,托以探贼,实欲挺入贼营,与贼相见,啗贼讲和。惟敬简其驺从,疾驰渡江,言语张皇,是日馆于义州。(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二。)
由此可知,明朝大兵未到,和谈之使先行。确切地说,宋应昌受命为经略在万历二十年九月,而沈惟敬“始封议入倭”在二十年七月(注:黄汝亨:《寓林集》卷一七《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经略复国要编》附。),当沈惟敬在朝鲜进行和谈活动时,宋应昌正在辽东集结兵力。当时,沈惟敬与日方商定六十日内,不攻朝鲜(注:《经略复国要编》卷一○《讲明封贡疏》。)。经略宋应昌坚决主战,反对和谈,对沈惟敬说:“我奉命讨贼,知有血战耳,汝毋以身试法”,将沈系于军中,不许他再入倭营,同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注:焦竑:《献征录》卷五七,王锡爵《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冈宋公应昌神道碑铭》,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此后,虽然宋应昌与曾利用沈氏和议烟幕,争取时间调兵歼敌,但事实说明,明朝虽然决策出兵,内部主和派却实际干预了战争具体运作,使战与和在初战阶段成为并行的两条线索,而这两条线索决非是完全和谐的。
政策游移,后果十分恶劣,不仅造成朝鲜战场上和战并行,号令不一;更影响到明军遇有小挫即议撤兵,不能激励将士英勇作战,反而助长了畏敌情绪;而轻易撤兵,遗患无穷。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自宁夏平定哱拜回师奔赴朝鲜的提督李如松告捷于平壤,但不久,以轻敌败于碧蹄馆。碧蹄馆之败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其后明朝官军中士气低落,以李如松为首的主战派,也发生了变化。有学者指出,碧蹄馆之败从损失来说,并不算是大败。然而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实际影响确实很大。据朝鲜大臣柳成龙报告:“自碧蹄不利之后,天将之意,一向退缩,每委以天晴路干则当进,而犹疑京贼之多”(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七,《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三。)。更据明朝大臣王德完上疏“无奈碧蹄大败,魄散胆破,乃悚心坚意,惟封贡是图,不复言战斗事矣”(注:《王都谏奏疏》卷一《目击东倭衅隙专备御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战和并行,一旦战事遇有挫折,主和派势力就完全占据了上风,息兵和谈成为明朝统治层的决策。在李如松四月自平壤还兵开城前,沈惟敬已“再入京城,诱敌退兵”(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卷三。)。当时朝中大学士王锡爵等认为:“抑恐远追穷寇,全胜难期”(注:《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丙子。),提议撤兵(注:《献征录》卷五七,王锡爵在为宋应昌所作墓志铭中,曾为其辩冤,明确说请封与撤兵都与宋应昌无涉,是作为大学士的自己“议撤还”。);兵科右给事中侯庆远的疏中表述更为明确:“我与倭何仇,为属国勤数道之师,力争平壤,以权收王京,挈两都授之,存亡兴灭,义声赫海外矣。全师而归,所获实多”(注:《万历三大征考·倭上》。),都是认为战争应到此为止的论调。万历帝也错误地认为已到撤兵和谈的时机,并基本否决了宋应昌派兵留守的建议(注:《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三《慎留撤酌经权疏》:“以封以贡以羁縻之,有何不可?但留守,经也;封贡,权也;守经方可行权,无经则无权矣”,说明了留守对于封贡,也即对和谈的重要作用。但后来留守不成,不仅在明廷,也有其他原因,如在朝鲜保留军队的条件等方面原因。),下令让朝鲜国王还都王京,整兵自守,明军“以次撤归”。就这样,明朝不但没有抓住战机,反而“一意主款”,撤兵回国,给了日本人以喘息机会,遂使战争无限延长。至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军再次大举在朝鲜登陆,明朝以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为经略,出兵朝鲜,遇到的是“兵已尽撤,募者不至”,在三月,辽东总督孙鑛“所征南北官兵止一万九千余名”(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八,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这个数字只及先前宋应昌集结兵马的1/3。初战阶段轻易撤兵的恶果完全显示了出来。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再战阶段的明朝政策也仍具有游移不定的特征,稍有败报,就出现新的摇摆(注:这从兵科给事中姚文蔚言“东事结局无期,和议潜行未息”,以及蔚山之战后,日军气焰嚣张,朝中撤兵减饷议论又起,适可得到证明。更好的证明,是邢玠《奏辩东征始末疏》中揭露直至战争最后一刻,首辅“志
 以密勿大臣,不为请兵请饷,亦附合抗章欲减兵退守”。)。
以密勿大臣,不为请兵请饷,亦附合抗章欲减兵退守”。)。政策的游移,深刻影响了战局发展,贻误了战机,造成战与和都不能成功的严重后果,更拖长了战争过程,加大了战争耗费。由此反映出明朝从皇帝到中枢决策大臣,都始终对外交和平解决寄托希望,随时准备妥协,说明了此时明王朝对外关系的被动保守状态,已经完全丧失了明初外交上的恢宏气魄,只是勉强维护朝贡体制而已。
(二)和谈中不辨真相
在这场战争中,和谈时期远过于战争状态是一大特点。主和派以石星为首、以沈惟敬为中心的和谈活动,实际贯穿了援朝之战的前两个阶段,即初战与和谈阶段。碧蹄馆之役以后,和议形成主流,此后,明朝在和谈中不辨真相,不能知己知彼,决策失当在所难免,根本达不到和平的目的。
首先,明朝对敌情不明。如前所述,经过激烈的争议,明朝决定册封丰臣秀吉。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二月,万历帝以“临淮侯勋卫署都督佥事”李宗城、“五军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杨方亨为正副使,前往日本,对丰臣秀吉“封以日本国王,赐以冠服、金印、诰命”(注:《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三年二月辛亥,中华书局1958年版。)。然而,确切地说,此时丰臣秀吉意欲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朝贡体系,明朝朝贡体系已被破坏殆尽,明朝仍然运用传统的册封方式,甚至不许通贡而试图羁縻日本,当然不能满足丰臣秀吉野心,因此不能解决问题。但兵部尚书石星一味听信沈惟敬,天真地以为只要册封成功,就可得到和平。直至此时,明朝不清楚沈惟敬早已答应日本的不仅是册封一桩,对日本方面在和谈期间提出的七个条件也懵然无知,处于被动的地位(注:参见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623页。)。使团出使后滞留朝鲜,一直拖延不能渡海去日本,日本在朝鲜的军队也迟迟不撤,明朝不知所以,朝堂之上空发议论。于慎行曾评论当时统治层对日外交无知的状况:
关白封贡之议,一时台谏部司上疏力谏,月无虚牍。争之诚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消化泛论事理,至于日本沿革,绝不考究。有谓祖训绝其朝贡,二百年来不与相通者,览之为失笑……四夷封略,在礼部验封司,大司马石公徒欲取效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为何国,关白为若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啽呓。(注:《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四年五月丙子。)
明朝册封之事归礼部掌管,不归兵部,石星不了解日本与中国的既往关系,甚至对日本是什么国家,关白是什么人都弄不清,就独揽封事;而朝中大臣只凭揣摩,不知底里,就事论事,大谈封贡,这种对外交事务的无知,直接影响到战争过程的决策,难怪于慎行发出“以此御难,何以为国”的慨叹。
就这样,和谈使团一去无音讯,明朝在空洞理论的氛围中,一直对传来的消息将信将疑。直到正使逃去,明朝改由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使团才终于在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六月渡海进入日本,此时距首次任命派遣使团已有一年多了。九月,使团在日本完成了对丰臣秀吉的册封。当狂妄的丰臣秀吉得知明朝仅封他为日本国王时大怒,直云:“明主册封不满我意,然姑忍之,朝鲜和讲,我决不许。册使亦不可留,明日速发遣。再起大兵,以灭朝鲜。”(注:〔日〕《秀吉谱》,见〔日〕川口长孺《征韩伟略》卷四,《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本。)日本不能达到目的,自然不肯罢休,和谈破裂不可避免,战争再起成为必然,丰臣秀吉迅速策划新一轮战事。而明朝使节杨方亨回国后,只言册封成功,明廷直至战报到来,方知和谈失败。
其次,明朝对己情也不明。在重大外交活动中,不仅任人不当,而且偏听偏信,以致误国。“国家托付非人”(注:《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明朝先后派出的使节沈惟敬、李宗城,就是两个典型。
在与日本的和谈中,明朝重用的沈惟敬来历不明(注:一说沈是浙江平湖人,本名家支属,少年曾从军,后入京师,喜好炼丹,与方士和无赖交游,由于石星妾父也好炼丹,故相识荐于石星;一说出身浙江嘉兴或平湖,客游北京,与妓吴澹如相通,澹如仆郑四曾去日本,了解日本情况,石星妾父袁茂到澹如家玩时,听沈惟敬谈论时事,就如去过日本一样,于是推荐给石星。前说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沈惟敬》,中华书局1959年版;后说见《两朝平攘录·日本上》。),他至多只是听到过一些有关日本的传闻,却得到兵部尚书石星的完全信任,委以使节重任,且言听计从。明朝时人云:“司马既以封贡事委之,言无不合。言路交攻,不为动”(注:《万历野获编》卷一七《沈惟敬》。)。就连朝鲜大臣都知道,石星一向偏听沈惟敬,“虽朝议多异,而星奋然以身当之”(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卷三。)。明朝大军未行,石星先遣他入朝,借机和谈,而他一到朝鲜,就给了朝鲜大臣吴亿龄“其人貌寝而口如悬河,盖辩士也。且言与平义智、平秀吉相知云矣”的印象(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二。)。他对日本人夸下“不云和亲,辄曰乞降”之海口不能兑现,于是一直“时露时藏”,不断蒙骗朝廷,隐瞒日方意图,使明朝相信可以和平解决战争,从朝鲜战场撤兵,并派出册封使团。使团出使后,沈惟敬因未被任为册使,大失所望,而册封使李宗城不把他放在眼里,更使他心生怨恨。使团被拖延渡海去日本,“不曰风潮不顺,则曰宫殿未成;不曰礼节未备,则曰不可不加慎重”(注:《两朝平攘录·日本上》。)。在此期间,沈惟敬在内倚仗石星,在外密令人扬言封事失败,促使李宗城畏惧逃跑,使自己得以被任为使团副使,并先行渡海赴日。他教杨方亨谨记“支吾中国,奉承日本而已”之语(注:《两朝平攘录·日本上》。),充分暴露了卖国的丑恶面目。册封失败后,沈惟敬妄图再次欺瞒朝廷,“乃私市珍异为秀吉物以诡报”,打算像以往那样私购物品假作国礼,但日军已开始陆续渡海,他继续蒙骗不成,又欲投降日军,最终伏法。总之,沈惟敬根本不熟悉外交事务,只知尔虞我诈的伎俩,明朝却让他担负外交重任,并对他偏听偏信,以致以私害公,两边欺瞒,误国不浅。
李宗城是临淮侯长子,系朱元璋外甥曹国公李文忠的后裔(注:《明史》卷一○五《功臣世表》一:“李宗城以使朝鲜逃归,论死,不得袭。”)。他以祖上功勋署五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五军都督府官员的贵族化和素质的低下,在明中叶以后已引起朝廷正直官员的注意,这批人平时无事,恬不知兵,遇有战事,束手无策。李宗城正是这样一个纨绔子弟。他以石星推荐,出任册封使。出使后,他本性难移,昏昏终日,溺于酒色,以致陷入日本人圈套。日军迟迟不撤兵,“遂羁二使于倭营一载,度其窘,以危言惕之”(注:《武备志》卷二三九《占度载·度·四夷十七》。),而李宗城竟“日夜涕泣思归”,后听沈惟敬营千总谢隆传言,日本20万大兵将至,信以为真,夜弃印信诏敕,变服逃跑(注:《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乙卯;《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杨方亨疏曰:“正使李宗城又被谢隆之惑,蓦然潜出”;而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记:“封日本册使李宗城自倭营逃。山东巡按李思孝报沈惟敬被关白缚绑,李宗城闻知,夜即弃印逃出。”说明李宗城听到的传闻还有沈惟敬先行渡海被缚的内容。)。消息传至京师,御史周孔教言:“奈何当时儿戏视之,而以一竖子辱命,取轻外国,如是尚为中国有人乎?”(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卷一《东封误国亟赐议处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一语点破了明朝外交用人之不明。
(三)出援大臣的掣肘状态
战争初起,明朝先期入援的3000骑兵兵败平壤,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举朝震动,京师戒严。明朝决定以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出师征讨。据称:当时“中外汹汹,计画无所出,朝廷悬赏格,有能复朝鲜者,赏银万两,封伯爵世袭。朝臣举股战舌虩虩无应者,乃稽首推公往”(注:黄汝亨:《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宋应昌受命于危难之际,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计划出战时,已有御史郭实上疏,“虑远道颠危,劾司马尝试国事,指陈切直”(注:宋懋澄:《九龠集·别集》卷四《东师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宋应昌不得已,上《辞经略疏》。
出援后,宋应昌受到多方面的牵制,束缚住了手脚,曾叹:“夫国家亦时常用兵矣,曳襟掣肘未有若今日。”(注:《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二《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事实上,明朝内部争议纷纭,延伸于外,在外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行其是,文臣与武将、南兵与北兵的矛盾尖锐,严重削弱了明朝军力,也暴露了明朝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初战阶段,不仅有沈惟敬直接受命于中枢、与日军的单独媾和活动,而且李如松以总兵提督军务,也“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史载他谒见宋应昌时不按规矩礼节,“以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注:《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传》。)。这说明了战争中文臣与武将关系的紧张状态。明朝历来是以文臣出掌军务,武将地位在文臣之下,李如松是镇守辽东多年的李成梁之子,手握重兵,骄横抗礼,根本不把宋应昌放在眼里。王锡爵曾述经略宋应昌的难处有六,其中有“边臣伸缩自由,而经略则空名客寄,俯仰随人”,“李氏盛满,人心不附,而又立万金之赏,悬封拜之格,忌宁远者并以忌公”等等(注:《献征录》卷五七,王锡爵:《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冈宋公应昌神道碑铭》。)。此外,据朝鲜史籍记载,由于李如松是北将,在首战平壤这样关键的战役中,曾“痛抑南军,恐其成功”;当碧蹄之败,李如松轻敌冒进,“所领皆北骑,无火器,只持短剑钝劣”(注:〔朝〕柳成龙:《惩毖录》卷三。)。后来顾养谦疏中谈到宋李二人之功,言问题出在“南北将领分为二心,彼此媒孽”(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一,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壬辰。)。不和谐的将帅、将领关系自然会影响到战争中的配合,并直接影响到战事成败。
最重要的牵制,是来自中枢。息战以后,不少朝中大臣指责援军统帅宋应昌和李如松。兵科给事中吴文梓攻李如松等“不能相机决策,以彰天威”,反而纷然讲和无已,畏缩退怯,并攻宋应昌“款贡未奉明旨”(注:《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六,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己巳。)。实际上,宋应昌自有难言之隐。鲜为人知的是,在息战撤兵问题上,作为主和派首脑的兵部尚书石星曾利用手中权力,对朝鲜战场兵力调动作了釜底抽薪,他“密令惟敬议款,忌公转战,所调兵悉令支解”。于是,中枢的掣肘,使在外统帅实际不可能再战,“一意主战守之事,封贡一着,置之不论”(注:《经略复国要编》卷一四《奏缴敕谕符验疏》。)的宋应昌,不得不慨叹:“令我以疲卒当锐师,抑徒手杀贼耶?!”(注:黄汝亨:《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当时他这个经略的所能,只有上疏力图留兵戍守,以保已有战争胜利果实了。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年底,朝廷下令宋应昌、李如松回国。宋应昌在四次上疏乞归后,于次年回故里,从此“绝口不谭东事”(注:黄汝亨:《寓林集》卷一五《明兵部左侍郎经略桐冈宋公配顾淑人墓志铭》。)。这不仅是宋应昌个人的悲剧,也是明朝政治的悲剧。
初战的经略如此,再战的经略邢玠又如何呢?邢玠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进击以失败报闻,受到攻击,诸葛元声评论说:“邢公之计虑是矣,其调度则未也。”(注:《两朝平攘录·日本下》。)认为邢玠不等水兵来到,进行水陆夹攻,轻易出战是完全错误的。然邢玠自有难处,他曾上疏自辩道:
堂堂天朝于岛夷何有,但倭之人情一,我之人情二。一则始终不挠,可以持久;二则自相攻击,能不摇撼?恐久不得战,哄然群议,不曰师老则曰财匮,不曰进迟则曰退速,或忌妒之口又从而飞语流谤,其间人情忧讥,畏罪之不暇,又何镇静观成之可望,此我所以持久不如倭也。(注: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二《申明进止机宜疏》。)
直接道出了朝中官员互相攻扞,纷乱异常,不仅使决策受到障碍,更形成对具体运作的动辄掣肘状态,出援大臣顾虑重重,不能进退自如,甚至无所措手足。
军事上战场瞬息万变,在外统帅最忌多方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即使有抱负,也不可能得到施展。当时人冯琦曰:“嗟嗟世议何极之有,功之未成,则曰是固不可成也;既成,即曰是不难,非但不难,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且以退罪之。”(注:冯琦:《冯北海文集》卷三《赠大司马邢昆田平倭奏凯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二。)这道出了任事者的艰难处境。整个战争过程里,战争指挥层发生多次重大人事调整,造成“七易岁,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将,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的局面(注:《冯北海文集》卷三《赠大司马邢昆田平倭奏凯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二。),出现既无良臣、又无良将的恶性循环。数度更换大臣,影响战局发展,更是明朝政策过程不能顺畅的表现。
(四)朝廷中枢的改组
作为决策群体,难解难分的内部冲突,深刻影响了皇帝与大臣的关系逐渐向不可逆转的恶化方向发展,在战争进程中,明朝政治上层的重组也在进行中,战争实际体现了明朝政治深层结构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万历帝明显厌倦了政治,对内阁和言官失去信任,章奏留中不报。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首辅赵志臯等上疏说:“迩年以来,章奏有留中不下者,而近日为甚”(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丙午。)。当时十多个本章,推补二十余员大臣,皆留中不报。此后赵志臯多次奏请,都如泥牛入海。这是皇帝与内阁及群臣矛盾加深,上下日益隔阂的结果。不仅如此,万历帝更转而信任宦官,将兴趣移到了搜刮财宝上面。一年以后,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上疏,指出部院科道之职渐轻的趋势,具体而言,部院缺位不补,且“争正事则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则十人而九不点”;科道情况也大体相同:“五科都给事中久虚不补”,“西台东省列署半空”;而为了开矿之事,抚按上奏被阻隔,千户、中官反参奏抚按,纲纪为之倒置(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万历二十四年十月戊寅。)。万历帝怠政,造成了君臣相猜,上下不交,政事荒废的局面,出现近乎瘫痪的政治状况。
皇帝怠政,中枢又如何呢?自册封使出,迟迟不见动静,力主册封的兵部尚书石星,理所当然成为群臣指责的对象,而一直依违于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实际是主和派支持者的内阁,也一并受到攻击。李植上疏直指册封决策失误,指出“遣勘使,罢中枢”,指责辅臣赵志臯、枢臣石星“百计阻言战守”,一误再误,建议立即选官会同督抚、巡按“前往探勘”,并请皇上令赵志臯、石星致仕,回籍听勘(注:李植:《李中丞奏疏》卷一《东封失策选枢臣以图战守事》,《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五。)。御史周孔教也论石星误国,言词激烈,矛头直指内阁。他认为石星罪不容赦,“而罪之首者”是辅臣赵志臯,指责赵志臯“曲昵私交,引用同乡宋应昌”;因“语侵志臯”,贬逐郭实;纵容石星,许封日本。提出“勒令二臣致仕”(注:周孔教:《周中丞奏疏》卷一《东封误国亟赐议处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册封失败后,朝中更是“议者蜂起”,“劾星者必及志臯”(注:《明史》卷二一九《赵志臯传》。)。战事再起,大小九卿科道官会议的结论是“欲救朝鲜,须亟更枢管,石星前事多误,方寸已灰,军国机宜,岂堪再误”(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丙子。)。于是石星下狱,而弹劾赵志臯者不断。
战争进入再战的胶着状态,直接导致了明朝政治最高层的人事变动。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兵二十余万分五路入朝,七月,闲山要害失守,直接威胁到中国沿海,战争形势严峻。十一月,经略邢玠调集明军分为三协,在朝鲜军配合下,向日军发动攻击。这场战役“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结果却“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注:《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究其缘由,战争由胜转败,首先是经理杨镐“震惧”逃跑,随后“士皆奔窜”,造成明军损失过半(注:《武备志》卷二三九《占度载·度·四夷十七》。)。战后,杨镐隐瞒伤亡实情不报,“诡以捷闻”,于是赞画主事丁应泰疏劾杨镐“丧师党欺”,述及“当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三,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丁巳。)。所谓“党欺”,直指内阁大学士张位。他指责张位招权纳贿,接受杨镐贿赂,力荐杨镐经理朝鲜军务,夺情视事,并与杨镐密书来往(注:《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与此同时,还揭发大学士沈一贯也私下致书杨镐,甚至将御史汪先岸论杨镐的“拟票留中之旨”,也秘密给杨镐看,因此并劾张位与沈一贯“扶同作奸”(注:《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此疏道出了明朝吏治腐败,以及内阁贪污受贿的状况。万历帝得报大怒,罢免杨镐,令大学士张位免职闲住,沈一贯引咎得免。战争至此,导致了明朝政治最高层的人事变动。
战争进行七年中,统治上层政治分化重组也加速进行,明朝内阁组成主要是赵志臯、张位、沈一贯。其间王锡爵、陈于陛有短暂的在阁时间。赵与张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入阁,陈与沈于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入阁。值得注意的是,赵与张都是由申时行“密荐”入阁的,吏部尚书陆光祖曾为此上言,认为阁臣例由廷推,而二人由密荐而入,“恐开徇私植党之门”(注:《国榷》卷七五,万历十九年九月壬午。)。二十二年,由吏部会推阁臣,推举了王家屏、孙丕扬等七人,当时在阁的王锡爵与赵志臯、张位,不愿孙丕扬等正直大臣入阁,以违制将这次会推作废,主持此事的文选郎中顾宪成由此削籍,而入阁的是陈于陛和沈一贯,陈入阁不久即去世。赵志臯为首辅的内阁,实际是主和派的支持者,因此,内阁因援朝之战成为论争对象,自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赵养病,张削职闲住,沈告罪后为万历所挽留,自从张居正死后,至此,可以说内阁衰微到了极点。
以上事实说明,在战争过程中暴露出明朝政治的诸多问题:皇帝怠政,内阁衰微,大僚空署,上下乖离;士大夫丧失伦理道德,受贿谋私,朝廷之上,各不相谋,争端迭起,务实乏人;面对燃眉的军政大事,中枢运转失常,影响决策过程以及具体政策运行,致使对外战争战和不力,数年无功;凡此种种,无一不表明明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折射出的是明朝政治的一种自在的衰落过程和政治危机。
三、战争与明后期的政治态势
明朝出兵援救朝鲜,中朝联合打败了入侵朝鲜的日本侵略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应当充分肯定。
当时人冯琦曾从对外政治意义的角度,评论这场战争:
古人通西域以制虏,今日救属国以制倭。倭自南,虏自北,即使偶发而畸至,彼谋不合,我力不分,于中国自疥癣耳……载籍以来,亦有出师大海外救人者否?主上之于朝鲜,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国,摧一强国,以风示四夷之君长,莫不稽首内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译之朝,国势强,国体尊。(注:冯琦:《冯北海文集》卷三《赠大司马邢昆田平倭奏凯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二。)
战争胜利者是中国与朝鲜,但胜利又给了万历朝什么呢?显然是明朝威信的提高,重要的还有在明朝朝贡体系中,始终被认为是异己的日本终于被战败,从而使困扰明朝自开国以来200多年的倭寇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历史表层下深藏的事实,就会发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清楚地反映出了明后期的政治态势。明朝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可以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战争胜利后远不是升平有望,事实上,这场战争成为明朝衰落的标志。作为明后期政治的一个关键转折,体现在内外两方面。
(一)在外交上,援朝之战是明朝与日、朝关系,也即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标志着明朝朝贡体系的破坏殆尽。
明初建立的朝贡体系在历史上规模空前,而明朝遭遇的外扰也是史无前例的。对朝贡体制下明朝与属国的关系,明太祖在祖训中曾有明确的不征规定,而万历时面临战祸,明朝不得已加入了战争。明朝大臣于慎行在一篇贺功叙中说:“圣上为华夷共主,宠绥四方……故知今日出师之名义而后上之威德益弘明。”(注:于慎行:《于文定公文集》卷一《贺中丞丘泽万公征倭功成叙》,《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九。)援朝之战是维护明朝朝贡体系之战,也即具有维护明朝君主在东亚的“华夷共主”形象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在外国土地上作战的事例,体现了明朝对外政策与以往王朝政策的历史继承性。在唐朝时期,唐与朝鲜的关系中,出兵是为了自卫,“守在四夷”,同时也是为了“兴亡继绝”,负有道义的使命;到了明朝,仍然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出兵援朝。战后,明朝遵循对朝鲜无寸土要求,就这一意义上说,万历朝继承了历史上传统对外政策,也遵循了明太祖的祖训。
根据文献记载分析,领土扩张是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主要动机,吞并朝鲜,灭亡明朝,将中、朝领土纳入日本版图,在亚洲内陆建立日本帝国,这一野心前所未有,是日本侵华的嚆矢,并在以后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实施。进一步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其背后显示出的是国际贸易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日本丰臣秀吉的兴起,与西方东来引起亚洲内部格局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说明初已受到日本倭寇的骚扰,那只是非国家组织的小规模侵扰,那么这一次战争是西方东来后日本的国家行为;日本活跃的国际贸易活动的背后,是经济需求的巨大驱动,而日本发动战争,丰臣秀吉的侵华野心,可以视为世界性的连锁运动。西方东来,亚洲旧有的国际关系体系被破坏殆尽,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尚未建立,日本乘机逸出朝贡体系,成为东亚侵略扩张的因素,向明朝挑战。可以说,16世纪的明朝不仅面临西方东来的挑战,而且同时遭遇到东亚的挑战,换言之,明朝遭遇的是东西侵略扩张的风暴。不仅朝贡体系受到致命冲击,而且本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就这一意义而言,援朝御倭之战,不仅是维护明朝朝贡体系之战,也是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形势下的国土保卫战。
总之,这是一场全新意义的战争,既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挑战,又是西方东来以后东西方贸易大炽,经济需求增长的反映。经历东西两面夹击的外在挑战,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已被破坏殆尽。
(二)在内政上,援朝之战多方面显示了明朝政治弱点,昭示了王朝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更是明后期由治及乱政治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成为明亡的重要契机。
政治衰退是一种长期的过程,而内外矛盾的互动,全面酝酿了明朝的统治危机。战后,明朝国力大减,危机日重,迅速走向灭亡。
1.这场战争,将整个中国都不同程度的卷入了其中,战争的旷日持久,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所谓万历三大征(注:即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实际上三者性质、规模并不相同,宁夏、播州均是平叛战争,涉及范围、进行时间相对狭少。),惟有援朝之战是出援外国,参与国际战争,耗费也最大。据时人估计:“朝鲜要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余万两”(注:王德完:《王都谏奏疏》卷一《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另据记载,仅再战阶段邢玠出任经略的四年间,就“用饷银八百余万两,军资不与焉”(注:《武备志》卷二三九《占度载·度·四夷十七》。)。正如退居山林的大学士王家屏所揭露的:“远迩绎骚,公私靡敝如是,曾未闻其出一奇,当一队,收一战之功,而山人游客尽拜官矣;厮养隶卒尽富贵矣。车骑戈甲,连数镇之师,半委山谷矣;金钱刍粟,倾数百万之积,尽填沟壑矣;兵老财殚,智穷计绌,乃始听用狎邪无赖之辈,往来倭营,哀求和好,今日议贡,明日议封,外坠狡夷之牢笼,而内坐守寸步难移之困局……今时势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注:王家屏:《王文端公文集》卷一《答顾冲庵论东事》,《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三。)。又如谈迁所云:“越国救邻,自昔所难,况海外乎?东征之役,苍皇七载,民力殚竭。”(注:《国榷》卷七八,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己巳。)明朝为了这场战争转饷半天下,其间国家财政日绌,为此除加重赋税以外,令官吏捐俸,大臣出钱助工以救缓急。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吏部以东事告急,鬻爵开事例(注:《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四年五月辛巳。)。同年,万历帝派遣中官开矿于畿内,榷税于通州,从此矿监税使四出,多方搜刮,民穷财尽,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混乱状态。援朝之战结束不到半年,就出现了民变,导致了王朝的统治危机。
2.“征师索饷,远迩震动,夷狄盗贼,莫不生心”(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三,万历二十七年四月辛未。),是战争的直接后果。从此时起,明朝来自辽东的威胁日甚一日。
在援朝之战中,明朝将辽东兵力大都抽调到朝鲜,投入援朝之战,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乘机发展,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打败叶赫九部,攻下了讷颜部。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他被晋封为龙虎将军。援朝之战后,为战争胜利冲昏头脑的明朝统治者认为辽东已安,因此更放松了警惕。明朝君臣深深陷入内部纠纷,对努尔哈赤的蚕食坐大毫不注意,看不到努尔哈赤的日益强大将成为与明朝抗衡的力量。正是在这种疏于防范的情况下,努尔哈赤逐渐控制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势力发展迅速,以致尾大不掉,无法控制,最终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成为明朝统治的重要威胁。
综上所述,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卓有成效;中叶以后,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统治阶级上层的纷争,既是政治分裂的表现,又是政治腐败的结果。而改革后明朝走向衰亡的明显标志正是此战。
四、结束语
这场战争是日本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朝联合反侵略取得胜利。时至今日,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侵略者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规律长存,援朝之战体现出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然而,这场战争表明的明朝政治实态,透视出明后期的政治态势,反映出明朝内外关系的变化,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对晚明政治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如果说党争亡国,还不如说以这场战争为分水岭,标志着明朝政治、军事、财政等全面危机,揭开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帷幕更为确切。
以对外重大政治事件为透视点,沿着不同以往的党争与内部事务的路径展开,考察明后期的政治实态,从中可得出重要启示:明亡于万历,万历朝是重要转折时期。但是,明亡于党争这一司空见惯的定论,却不足以说明问题。在援朝之战如此重大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明朝政治机制的低能和政治的腐败暴露无遗,说明在世界发展变化的背景下,即使在东林与齐、楚、浙党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明朝政治已显示出衰败的态势。一言以概之,明朝以制度化存在的政治机制问题已凸显了出来。进一步探析,明后期无论是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都会引起无休止的纷争,这完全是因为政治机制本身的失衡,而党争只是一个表现形式,是政治分化改组进一步加剧的结果,而并非是原因。自张居正改革后,至援朝之战,明朝政治的保守与腐败已掩盖了活力,政治的一种自在的衰亡过程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