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库伦办事大臣”的考查
冈洋树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蒙古学信息》(呼和浩特)1997年02期第29-36页
【作者简介】〔日〕冈洋树
清朝在统治喀尔喀蒙古之际,在乌里雅苏台设置定边左副将军〔1 〕,在大库伦(Yeke Küriye今乌兰巴托)设置了办事大臣。定边左副将军是为了准噶尔战争的顺利进行而设置的,因此18世纪中叶准噶尔被打败后,逐渐失去了其作为军官的意义,与此同时,大库伦以集尊重于一身的喀尔喀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地,还以在喀尔喀的汉族商人的活动据点,在清末作为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超过了乌里雅苏台,而驻在本地的办事大臣随着本地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其政治作用也增强了〔2〕。
这样,大库伦办事大臣在清朝对喀尔喀统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意外的是,以往对此缺少专门研究,只能举出李毓澍的《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3〕、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而已〔4〕。特别是关于其设置时期及情况,除上述二人,几乎没有全面概述,只是在另外题目的论文当中有所提及。连李氏也认为,大臣职务不是一时形成,而是从设置的初期乾隆中叶开始至嘉庆年间逐渐完善的。且在这里,大臣职务在政治上的形成过程,也未必达到明确。因此本稿试图弄清楚办事大臣的设置和设置时喀尔喀的政治形势,以及设置大臣的政治意义。
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四三(原文为卷四三○,经核对应该是卷五四三——译者)兵部、官制载:
办事大臣二员。雍正九年,库伦互市处,驻司员经理。后改驻办事大臣一人。乾隆四十九年奉旨,增派大臣二人,同办库伦事务。系出特简,不为额缺。今设办事大臣二人。内一人系蒙古王公台吉兼任。
如上记载,至少于嘉庆年间,在大库伦设置了满洲大臣和蒙古大臣二人。其职责主要是:①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涉事务、国境防备(卡伦—国境哨所)管理;②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大库伦及沙比那尔( abinar呼图克图的属民)的事务;③管理大库伦、恰克图(Kiyaγtu)的汉商(乾隆四十二年以后);④喀尔喀东部二盟(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的事务(乾隆五十一年以后)。当初,在四项事务中前二者为其主要职责。自喀尔喀归附清朝以来,这些职责一直是由土谢图汗及其近族担任的,但历来被理解为由于库伦办事大臣的设置,这些职责被转移到大臣的职责内。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有错误的。因此,下文就所谓“蒙古大臣”、满洲大臣的形成过程逐个加以多方面的探讨。
abinar呼图克图的属民)的事务;③管理大库伦、恰克图(Kiyaγtu)的汉商(乾隆四十二年以后);④喀尔喀东部二盟(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的事务(乾隆五十一年以后)。当初,在四项事务中前二者为其主要职责。自喀尔喀归附清朝以来,这些职责一直是由土谢图汗及其近族担任的,但历来被理解为由于库伦办事大臣的设置,这些职责被转移到大臣的职责内。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有错误的。因此,下文就所谓“蒙古大臣”、满洲大臣的形成过程逐个加以多方面的探讨。
一、关于“蒙古大臣”
根据通常说法,蒙古大臣是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七日的谕旨里任命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王公桑斋多尔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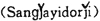 开始的〔5〕。其根据是道光二十年(1841)成书的噶尔丹(γaldan)所著喀尔喀编年史《宝贝念珠》(Erdeni—Yin Erike,以下略作EE )里所记载的下述事情〔6〕。
开始的〔5〕。其根据是道光二十年(1841)成书的噶尔丹(γaldan)所著喀尔喀编年史《宝贝念珠》(Erdeni—Yin Erike,以下略作EE )里所记载的下述事情〔6〕。
乾隆二十三年寅年,春末月初七日下达了谕旨。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在大库伦虽有商卓特巴逊都布多尔济从行佛事,但对众多沙比那尔的管理,只有一个人是不够的。于是派遣喀尔喀副将军桑斋多尔济,守备库伦,管理呼图克图的沙比那尔,并协助处理和俄罗斯之间的边境事务。于是由Kiya—bkin(Kiyabsa夹子?)上奏, 在大库伦驻大臣是从此开始的。
EE的著者噶尔丹是土谢图汗部左翼后旗人,在旗印务处和盟长、副将军衙门担任书记。可以想象他自会接触过各处的公文之类〔7〕。 实际上,在这部编年史中,有许多记载引自公文。这就是本书作为清代喀尔喀史研究史料而被重视的理由。波兹德涅耶夫等许多研究者利用这部编年史的记载,认为蒙古大臣设置于乾隆二十三年,是有很大问题的〔8〕。
首先需要注意,在这段记载中,把派遣桑斋多尔济前往大库伦当作任命其为“大臣”这段值得重视的记载,并不是出自引用公文(在此为谕旨)的部分,而是出自噶尔丹自己的记述部分这个事实。就是说这个记载是事情发生90年后的记载。谕旨里只记载派桑斋多尔济前往大库伦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事务,却没有记载任命他为大臣。同样的记载可以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九,传三三,扎萨克多罗贝勒西第什哩列传以及以此为根据的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七、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五中看到,都均只记载派遣他的事实,却没有记载任命他为大臣〔9〕。
确认这个事实之后,查阅其它汉文史料,特别是查看《高宗实录》,在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条里没能看到EE所记载的上述谕旨,却发现了能够说明在此之前桑斋多尔济已经在大库伦处理事务的记载。例如,《高宗实录》卷五三五,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戊午(二十七日)条里载:
谕军机大臣等,据桑斋多尔济奏称,俄罗斯边界事务,每年照例派员会办。前所派侍郎瑚图灵阿,未经会办而归。今准彼处毕尔噶底尔雅古毕文称,今年会办时,仍否出派官员,上年前来之大臣,仍来与否等因。或由桑斋多尔济派本部落扎萨克等,或另出派大臣官员,请旨定夺等语。(中略)桑斋多尔济,乃喀尔喀副将军,且系承办俄罗斯事务人员。著即派伊前往会办,不必另行出派。
于是桑斋多尔济不仅可以奏报俄罗斯毕尔噶底尔雅古毕的询问,而且皇帝也针对所奏称他为“承办俄罗斯事务人员”,准其可以和俄罗斯进行协议。
另外乾隆针对桑斋多尔济在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于四月十五日的谕旨里说:
……还有,关于施恩逊都布多尔济一事,最近朕已经赐给逊都布多尔济以绢布。桑斋多尔济只须指示他,使他处理事务就足够了。朕允准上奏。在其他方面应施恩时,还要适当施恩。把这个命令通知给桑斋多尔济。此后桑斋多尔济处理盟内事务时,只须遵从朕的谕旨,既要通情达理,又要深思熟虑,迅速处理,不准丝毫软弱〔10〕。
从此可得知同时期桑斋多尔济已被任命监督大库伦事务。在《高宗实录》卷五五四、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己亥(十二日)的谕旨里有进一步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据桑斋多尔济奏称,商卓特巴逊都布多尔济等,请将扎木巴勒多尔济,掌管经教,众心悦服等语。著照所请,将堪布诺门汗之印,给与扎木巴勒多尔济掌管,勤宣黄教,约束喇嘛。其商卓特巴逊都布多尔济,著协办事务。
从这一点可以得知他也参与了大库伦堪布诺门汗的人事工作。
这样就明确了桑斋多尔济在EE所记载的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以前已驻在大库伦,处理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涉及大库伦管理事务。那么,他在什么时候担任该职务的呢?有关桑斋多尔济就任时间,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月折档》当中他本人的奏折能够确定。即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奏折载:
臣桑斋多尔济谨请谕旨。正月十五日从京师出发,因公琳丕勒多尔济处理库伦事务,于二月初八到达库伦,拜受喀尔喀左翼兵管掌副将军印。臣将如何处理俄罗斯和汉商事务,由臣处通知了定边左副将军印务代理郡王车布登扎布〔11〕。
可以判断他就任于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但这是否即蒙古大臣设置的时间呢?仍然留下疑问。因为上述奏折中桑斋多尔济到达大库伦后接受了喀尔喀副将军印信,而有关大臣之事却丝毫没有提到。从上述奏折可以明白,他从这时期开始处理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涉及汉商事务。因此是否可以认为他不是作为大臣,而是作为喀尔喀副将军处理这些事务的呢?使这个疑问更为强烈的是下面的事实。
如在上述桑斋多尔济的奏折里所提到的那样,当时土谢图汗部辅国公琳丕勒多尔济(Limpildorji)已经在大库伦担当着事务。 该人物有同部副将军参赞头衔。 桑斋多尔济的副将军任命是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闰九月〔12〕,但此后由于处理青衮扎布( inggünjab)之乱善后,不能够赴任大库伦。因此也可以认为琳丕勒多尔济以副将军参赞,代理着桑斋多尔济的职务。然而参考《王公表传》卷五一、传三五、扎萨克一等台吉班珠尔多尔济列传,琳丕勒多尔济于乾隆二十二年被任命为副将军参赞,而前一年即二十一年就开始在大库伦“协理”和俄罗斯之间的事务。所谓“协理”指的是协助当时处理这些事务的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如果认为他在副将军任命以前,在大库伦已有职务,那么该职务和副将军参赞没有关系,因此也就可以认为该职务和副将军职务也没有关系。由于这种事实,不能说大库伦的事务属于副将军权限之内。
inggünjab)之乱善后,不能够赴任大库伦。因此也可以认为琳丕勒多尔济以副将军参赞,代理着桑斋多尔济的职务。然而参考《王公表传》卷五一、传三五、扎萨克一等台吉班珠尔多尔济列传,琳丕勒多尔济于乾隆二十二年被任命为副将军参赞,而前一年即二十一年就开始在大库伦“协理”和俄罗斯之间的事务。所谓“协理”指的是协助当时处理这些事务的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如果认为他在副将军任命以前,在大库伦已有职务,那么该职务和副将军参赞没有关系,因此也就可以认为该职务和副将军职务也没有关系。由于这种事实,不能说大库伦的事务属于副将军权限之内。
说来,喀尔喀副将军是从雍正二年(1724)准噶尔战争中作为喀尔喀兵2000人的指挥,由土谢图汗部郡王丹津多尔济(Danjindorji)、和赛音诺颜部(当时仍属于土谢图汗部)亲王策凌( ering)、 扎萨克图汗部贝勒博贝(Bübei)三人被任命开始的。后来车臣汗部也有被任命的,所以到赛音诺颜部独立,便形成了各盟设一名副将军的情况。从副将军的性质考虑,该职务没有监督和俄罗斯的交涉、以及恰克图事务的必要性。
ering)、 扎萨克图汗部贝勒博贝(Bübei)三人被任命开始的。后来车臣汗部也有被任命的,所以到赛音诺颜部独立,便形成了各盟设一名副将军的情况。从副将军的性质考虑,该职务没有监督和俄罗斯的交涉、以及恰克图事务的必要性。
副将军在大库伦的任务,是以什么样的权限为基础的呢?有一重要的事实可以参考。即乾隆三十年(1765)由桑斋多尔济等进行的有关和俄罗斯之间的秘密贸易事件。同年四月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发现往来于乌里雅苏台的商人拥有大量的通过当时已被停止的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才能购入的皮革制品,于是就奏报了。以此为开端由桑斋多尔济、满洲大臣丑达等进行的和俄罗斯的秘密贸易被发现,桑斋多尔济被削爵,而且被软禁在北京〔13〕。为调查这件事情而赴大库伦的理藩院额外侍郎、内蒙古喀喇沁左(原文为右,经查阅应该是左——译者)翼旗扎萨克瑚图灵阿(Hütüringga)被留在当地,以副将军代理处理事务。
同年十月继桑斋多尔济后,任为土谢图汗的车登多尔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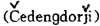 ,被任命为本部副将军, 此时瑚图灵阿上奏请示自己是继续留任,还是回去。即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他的奏折里说:
,被任命为本部副将军, 此时瑚图灵阿上奏请示自己是继续留任,还是回去。即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他的奏折里说:
……由理藩院发送,十一月二十五日到达的文书里,有对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副将军缺位,任命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的谕旨。臣把(该文书)直接送到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处,而车登多尔济于十二月十一日来到库伦,拜受了由臣和尚书阜乃(Funai)授与的副将军印玺和箭证。 ……经查看以前的谕旨,命臣瑚图灵阿代理副将军。现在则把印玺交给了车登多尔济,因此臣是继续驻在库伦,和他们一起处理事务,还是归还京师呢?等候圣主陛下下达谕旨,敬谨遵行。……对此,所奏有误,故朝中下达了谕旨〔14〕。
由此可以明确,瑚图灵阿理解大库伦的事务归属副将军职务内。因此,当车登多尔济正式被任命为副将军时,他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已完成,应该回去。针对这一点乾隆认为瑚图灵阿的奏报有误解。遂在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谕旨里说道:
他(瑚图灵阿—冈)是朕专门派往库伦承办事务的,诸多俄罗斯边境大事和呼图克图沙比那尔的事务,均应由他承办。喀尔喀副将军,最多不过处理其盟内的事情,而处理如此重大的事情能行吗?不仅如此,车登多尔济尚幼,能有什么经验呢?任命他为副将军,是根据当时形势而决定的,并不是信赖他而使他处理事务。任命他,只是想使他学会处理事务。对处理库伦事务和俄罗斯边境诸大事,则由瑚图灵阿等指挥处理。副将军印玺仍旧交给车登多尔济,使他随瑚图灵阿等学习处理事务。瑚图灵阿等上奏各种事情和送往文书时,则使用副将军印。还有,以前桑斋多尔济承办库伦事务时,他又是御前行走,所以上奏时把他名字写在前面,完全不是因为他是副将军就把名字写在前面。从此以后,上奏时把瑚图灵阿的名字写在前面,然后写阜乃、 车登多尔济的名字〔15〕。
总之,乾隆皇帝所说的桑斋多尔济在大库伦的职务并不归属土谢图汗副将军权限,而是基于皇帝对桑斋多尔济的信赖。所以尽管车登多尔济被任命为副将军,但并不意味使他自动承担库伦事务。而且车登多尔济尚幼,不足信用。所以使瑚图灵阿继续留在大库伦,处理事务。然而皇帝接着又说使车登多尔济学习处理大库伦事务,而且来往文书时使用副将军印,这只能说前后有矛盾。
看来,乾隆皇帝要说的大概是桑斋多尔济在大库伦的办事,不是根据清朝官制范围内的官职,而和这个分别开,派遣值得依赖的桑斋多尔济承办大库伦事务。那么我不得不想起下面的事实。即开头时说的那样,喀尔喀部归附清朝以来,和俄罗斯的交涉事务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大库伦的管理,无非是一直由土谢图汗家族及其近族王公承担的。世代的土谢图汗和丹津多尔济等王公一直在管理这些事情,但去并没有被授予清朝官制内的某种官职。他们作为代表喀尔喀的有力王公,的确是由于这种资格,被清朝委任处理和俄罗斯的交涉事务,还有因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和二世出于本家族而担任呼图克图及大库伦的管理事务。派遣桑斋多尔济到大库伦只能理解为这种政策的继续。对清朝来说重要的在于他是代表喀尔喀的有力王公。从他的家族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喀尔喀归附清朝时立过功的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弟弟西第什哩就是他的祖辈,而他祖父丹津多尔济是在准噶尔战争中有战功的人,桑斋多尔济本人是由其母宗室公主在北京带大的,而且他自己也是亲清派,对抗由三汗家族代表的喀尔喀既成权威,他是最合适的人物〔16〕。
这样的间接统治体制,此后也在继续着。乾隆三十六年(1771)桑斋多尔济恢复该职务时,不但没有被任命为大臣的特别迹象,连副将军也没有被任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桑斋多尔济死后,继承他的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仍没有被任命为大臣的迹象。这件事情表明了乾隆皇帝至少在形式上维持间接统治体制的企图。然而桑斋多尔济由于其过份露骨的亲情态度,和其他王公,尤其是和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及土谢图汗家族的众多王公发生了冲突。针对由此而发生的政治不安,清朝被迫采取某些对策。
如上所述,一直被认为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设置的蒙古大臣,实际上一直由土谢图汗家族承担的,和俄罗斯的交涉事务以及对哲布尊丹巴、大库伦的监督事务,只不过是由桑斋多尔济承担了而已,这丝毫不意味大臣职务的新设。
二、满洲大臣的派遣及其意义
第一任满洲大臣是诺木珲(Nomhon),根据波兹德涅耶夫等所依据的EE,他是按照乾隆二十六年(1761)冬中月二十二日的谕旨,被派往大库伦的。即:
二十六年冬中月二十三日,下达了谕旨。桑斋多尔济现有建设寺庙(的任务),他一个人不能够处理事务,上奏请求派一位大臣来共同处理事务,现派遣诺木珲让他与桑斋多尔济共同处理事务。几年替换一次、如何分给粮食等,由军机大臣协议上奏。库伦满洲大臣是从此开始的〔17〕。
一方面《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七四六,理藩院·俄罗斯互市、松筠《绥服纪略》、何秋涛《北徼喀伦考》·《北徼事迹表》下、《清史稿》卷五二六,列传三○七,藩部列传四,土谢图汗部列传、张穆《俄罗斯事补辑》均记载是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的。不过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上谕档》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条里,发现和EE完全相同的谕旨,因此认为任命谕旨下达于乾隆二十六年是正确的。只是受皇帝的命令后,经军机大臣通过协议作出答复已是进入乾隆二十七年的事了。《会典事例》等记为乾隆二十七年大概是这个原因〔18〕。
而问题则是其设置的理由。如在上述谕旨里所说那样,设置满洲大臣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给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建新寺庙而事情繁多,但其背后在喀尔喀内部存在着桑斋多尔济派王公和其他王公,特别是和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等之间的对立和抗争〔19〕。大约一年后的乾隆二十七年冬天,诺木珲被青衮扎布告发而被解任。从当时的谕旨可以看到下述情况。
……派诺木珲到库伦,正是因为前据青衮扎布所奏桑斋多尔济驻在库伦处理事务当中,有诸多不正之处,而被哈尔哈齐控告。朕因其身系蒙古人,没给处分。念其虽有错误,若从内地派大臣,随同办事,自可得以匡正。因命诺木珲前往。现诺木珲在当地狂妄胡乱不能容忍。应当派遣人员,调查处理〔20〕。
所谓哈尔哈齐是库伦喇嘛官位,直译为门卫,可能是商卓特巴等库伦高官的类似侍卫的官职〔21〕。当时向青衮扎布告发诺木珲的哈尔哈齐似乎接受了大库伦商卓特巴逊都布多尔济的指示。据桑斋多尔济说这个人物是当时的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的叔父,在喀尔喀内部居于长老地位。桑斋多尔济在他的奏折里控告逊都布多尔济,与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和土谢图汗部亲王达喜丕勒等勾结,在每件事情上和桑斋多尔济作对,企图夺取他的地位。而且逊都布多尔济在父亲血缘上虽和青衮扎布没有关系,但在母亲血缘上有亲近关系。从而明确了在喀尔喀王公内部存在着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反对桑斋多尔济派别的事实,桑斋多尔济在喀尔喀内部处于孤立地位〔22〕。
这种事情就清朝对当时喀尔喀政策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利用喀尔喀王公统治喀尔喀的间接统治,若该王公没有一定的声望,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被孤立起来,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这样反而会使其他王公以反对傀儡立场聚集在一起。那么这就意味着喀尔喀王公的反清结合的形成。桑斋多尔济本人没有做到和喀尔喀内部其他王公协调一致,反而以大库伦为中心聚集了自己的亲近人员,并直接联系清朝权力,与反对派对立。清朝如果希望维持其历史的间接统治体制,必须由更稳当的王公来代替桑斋多尔济或使桑斋多尔济改变态度,乾隆皇帝选择了后者。可是从北京又不可能直接监视他,所以派遣满洲大臣,其意义就在这里。因此这时的满洲大臣被禁止过深介入喀尔喀内部事情,诺木珲被告发时皇帝说道:
由青衮扎布处上奏,为准备来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化身)赐给受戒喇嘛的物品,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等和诺木珲协议,从喀尔喀四部征收了一千两银子,诺木珲竟然检查呼图克图的物品并拿走了水獭等毛皮。这是很可笑的事情〔23〕。
诺木珲系驻库伦之人,所有招请呼图克图化身、因受戒征收银两等事,即使伊所应管,亦不过共同与闻而已,乃竟从中任性滋事,并少给商卓特巴价值,勒买如许绢布、毛皮,复借贷银两,至于修理伊住房一节,理应奏闻官给办理,伊又擅用喇嘛工价并纵容领催及家人恣意索银甚属无耻,卑鄙不堪〔24〕。
皇帝除了责备诺木珲乱用权力搜刮钱财外,还责备他参加有关大库伦问题的协议和检查呼图克图物品。
代替由于这件事情而被解任的诺木珲,派往库伦的是福德(Fude)。这个人物上任半年后又被解任了,其理由据说是因为对待喀尔喀王公态度傲慢。福德在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上任后,向皇帝建议要把喀尔喀归附时的谕旨重新读给王公们听。然而受到了皇帝的指责:
这是应由所有喀尔喀王公协议处理的事情,桑斋多尔济系喀尔喀人,他自己会见大家解决这件事情即可。福德为什么要参与呢?命令福德不要参与这件事情〔25〕。
在这里皇帝明言喀尔喀事情应由系喀尔喀王公的桑斋多尔济来管理,并不属于福德管辖内。但是福德并没有从这里吸取教训,又想把内地礼制强加于喀尔喀王公,致使皇帝愤怒,被解任。
就这样,满洲大臣的任命不是以夺取桑斋多尔济所主管的权力为目的的,而是为了阻止他的暴行,以维持旧制。但被派遣的大臣们没有能够理解这个目的,再三干涉喀尔喀内部事情,乱用权力,不正当搜刮钱财,强制实行内地礼仪。桑斋多尔济被解任后代替他上任的瑚图灵阿把大库伦的任命理解为属于副将军权限内,也是因为没能理解乾隆皇帝所意图的喀尔喀政策。满洲大臣本来是以对应管理大库伦事务的桑斋多尔济给与辅佐、监视为目的被派遣的,由于这种性质,没有定额,而是临时职务。可是喀尔喀的形势没有向皇帝所想象的方向发展,反而王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桑斋多尔济乱用权力,和俄罗斯进行秘密贸易,最终失势。由于喀尔喀的这种政治危机,满洲大臣在此以后仍继续被任命着。
结语
综上所述,历来被认为的由桑斋多尔济被派遣到大库伦而开始的大库伦蒙古大臣的设置,不是EE里所记载的乾隆二十三年三月的事,而在前一年他已在大库伦承担处理事务,但那也不是以大臣的资格进行的。派遣他,只不过是一直由土谢图汗部有力王公委任的,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涉事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大库伦管理政策的继续,并不意味任何新官职的设置。但是对由于过份的亲清立场在喀尔喀内部被孤立起来的桑斋多尔济,产生了以某种形式从中央给予支持的必要,因而被派遣的是大臣诺木珲。所以满洲派遣大臣不是象以往理解的那样,以夺取蒙古大臣的权力为目的,而是要辅佐桑斋多尔济并阻止他的暴行。确实从那以后大库伦实权移到了满洲大臣的手里,但那是桑斋多尔济死后进入乾隆四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像我曾经研讨的那样,乾隆四十年间通过《将军、参赞大臣、盟长、副将军办理事务章程》的制定和划定牧地,在制度上强化了对喀尔喀的统治。继桑斋多尔济之后上任的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在乾隆四十九年被解任,从此,实权名副其实地移入了满洲大臣的手里。乾隆二三十年间,乾隆仍继续其对喀尔喀的间接统治,而且企图宁可维持它。任命派遣满洲大臣也正是反映了清朝对喀尔喀的这种政策,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够取得和其它政策的整体性的理解。本稿确认了以上问题,暂时停笔。
(附记)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览史料期间,提供帮助的鞠德源先生和同馆的诸位,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杜荣坤先生深表谢意。
(说明)原稿注释当中的俄文、新蒙文由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翻译——译者。
乌云格日勒 佟双喜 译自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清朝与东亚细亚》山川出版社 1992年3月
注释:
〔1〕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蒙Qola dakin i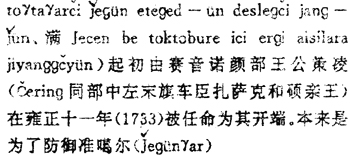 而设立的军官,同时带有行政官的性质。作为对其设置过程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有李毓澍的《定边左副将军制度考》(《外蒙政教制度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九六二年,台北,一—一○三页)。在该任中,继策凌之后有其子成衮扎布
而设立的军官,同时带有行政官的性质。作为对其设置过程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有李毓澍的《定边左副将军制度考》(《外蒙政教制度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九六二年,台北,一—一○三页)。在该任中,继策凌之后有其子成衮扎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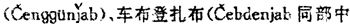 右旗代钦扎萨克多罗郡王)相继被任命该职务。对此可以参考Veronika Veit :《十八世纪喀尔喀蒙古乌里雅苏台将军》(《国立政治大学国际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一九八五年,台北,六二九一六四六页)。在策凌的经历当中有和桑斋多尔济的经历极其相似的地方。我认为对策凌和当时清朝对喀尔喀政策有必要再考证。笔者已在拙稿《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和他的立场——作为清朝对喀尔喀蒙古政策研究的导论》(《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哲学、史学编、别册第十三集,一九八七年一月,一六七—一八○页)。论述了任命青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的清朝对喀尔喀间接统治的性质。一方面同样的性质在策凌任职时更为明显,同时有必要考虑和准噶尔临战乃至临战形势下喀尔喀军事协力的必要性以及特殊性。换言之,如何理解对准噶尔战争要动员喀尔喀,却不依靠已形成的汗权威,敢于创立定边
右旗代钦扎萨克多罗郡王)相继被任命该职务。对此可以参考Veronika Veit :《十八世纪喀尔喀蒙古乌里雅苏台将军》(《国立政治大学国际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一九八五年,台北,六二九一六四六页)。在策凌的经历当中有和桑斋多尔济的经历极其相似的地方。我认为对策凌和当时清朝对喀尔喀政策有必要再考证。笔者已在拙稿《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和他的立场——作为清朝对喀尔喀蒙古政策研究的导论》(《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哲学、史学编、别册第十三集,一九八七年一月,一六七—一八○页)。论述了任命青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的清朝对喀尔喀间接统治的性质。一方面同样的性质在策凌任职时更为明显,同时有必要考虑和准噶尔临战乃至临战形势下喀尔喀军事协力的必要性以及特殊性。换言之,如何理解对准噶尔战争要动员喀尔喀,却不依靠已形成的汗权威,敢于创立定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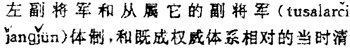 朝政策的特点是个问题。在这里把它作为今后的课题提出,待于考究。
朝政策的特点是个问题。在这里把它作为今后的课题提出,待于考究。
〔2〕有关大库伦概说有A.A.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 第一卷,圣彼德堡,1896;普·都古尔苏隆《乌兰巴托市历史》首都,库伦,乌兰巴托,1956;(札奇斯钦中文翻译《库伦城小史》,《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四,一九七三年)还有关于作为寺院的大库伦,参考斯·普日布扎布《革命前的大库伦》(历史—财政编)乌兰巴托,1961。
〔3〕李毓澍《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一○五—一八四页。
〔4〕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弘文堂, 一九二六年)五二一六三页。
〔5〕A.A.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67页;И.Я. 兹拉特金《近现代蒙古历史论集》,莫斯科,1957,124—125页;策·索德诺木达格巴《满洲统治之下的外蒙古行政组织》(1691—1911),乌兰巴托,1964,33页;斯·普日布扎布《革命前的大库伦》,47—48页;策·那顺巴勒珠尔《外蒙古向满清进纳的贡品》(1691—1911年),乌兰巴托,1964,187页;G.C. 戈罗和娃《满族统治下的蒙古历史论集》,莫斯科,1980,39—40页;A.奥其尔《1911年蒙古人民为民族自由、独立的战争》(资料汇编)(1900—1914),解释298页,乌兰巴托,1982;李毓澍《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
〔6〕噶尔丹《额尔德尼额日克》(γaldan Erdeni yin erikekemek ü te üke bolai )Monumenta Histories Tamus Ⅱ, Fasciculus 1,乌兰巴托,1960,127页a—b面。
〔7〕同上策·那顺巴勒珠尔的序文。
〔8〕注〔5〕所举出的文献几乎都没有对大臣设置的时期加以考证。只不过根据EE的记载加以叙述。但是李毓澍把波兹德涅耶夫引用EE所叙述的部分和陈箓的《蒙古逸史》相对照,“辞句之间虽与逸史略有出入,但时间与内容,则均与逸史相符”(一二九页),因此认为乾隆二十三年设置了蒙古大臣。然而象石纯滨太郎早已叙述的那样《蒙古逸史》是否和EE属同一系统史料,或是抄译呢?不能否定这一可能性,因而李氏所采取的方法有问题(石滨纯太郎《蒙古逸史原本》,《艺文》第十年第七号,1919年7月)九○—九六页。另外, 可以参考中见立夫《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史料价值——博格多汗制蒙古国时代中国方面若干史料的考察》(《史学杂志》八五—八,1976年8 月)五一—六八页;石滨纯太郎《蒙古逸史考》(《龙谷史坛》二九,1942 年7月)三三—四○页。
〔9〕两书记载完全相同, 即“二十三年赴库伦协理俄罗斯边境事”。
〔10〕《由青衮扎布领导的外蒙古独立斗争(1756—1758)》(手稿汇编)齐木德编,乌兰巴托,1963,36号88—91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全宗三、编号八七(二)。
〔12〕《高宗实录》卷五二三,页三上一下,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癸丑(十八日)条。
〔13〕关于该事件概要参考拙稿《乾隆中叶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统治的强化和桑斋多尔济》(《东洋学报》,六九一三、四,1988年)。
〔14〕满文《月折档》全宗三、编号一五三(二)。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寄信档》全宗三、编号一三一(三)。
〔16〕关于桑斋多尔济参考注〔13〕拙稿。
〔17〕EE128页b面。
〔18〕中国方面的史料重要的是一贯把乾隆二十六年乃至二十七年的诺木珲的派遣认为办事大臣的初设,例如何秋涛在《北徼喀伦考》里叙述“是时库伦尚未派驻大臣,凡喀伦事务,俱系办理夷务之喀尔喀王统辖,至乾隆二十七年,始设钦差大臣驻库伦,专理恰克图贸易事。”还有矢野仁一认为比此文更为可靠的松筠《绥服纪略》里写道:“先是库伦所属边卡戌守年久凋散。乾隆二十二年,有前办夷务喀尔喀王丹津多尔济之孙桑斋多尔济,遵旨统理。因竭力整顿,安设卡伦,始克完善。迨后,夷务繁多,始驻钦差大臣,同桑斋多尔济总理其事,一切仰遵圣训,自是永为定例。”把满洲大臣派遣认为是“始驻钦差大臣”。换言之中国方面的史料没有记载桑斋多尔济为大臣。
〔19〕关于在乾隆二十年代展开的两者抗争的原委,俟在其它稿子里详细论述。
〔20〕满文《寄信档》全宗三、编号一二九(五)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谕旨。《高宗实录》卷六七九、页四上,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戊寅(二十日)条。
〔21〕汉文史料中有“哈尔哈齐”,大概是蒙语的哈戈勒戈其(qaγalγa i),参考田山茂《蒙古法典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7年)二九八页、注。
i),参考田山茂《蒙古法典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7年)二九八页、注。
〔22〕满文《月折档》全宗三、编号一三六(二),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桑斋多尔济的奏折。
〔23〕满文《寄信档》全宗三、编号一二九(五),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谕旨。
〔24〕满文《上谕档》全宗三,编号一一○七(一),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谕旨,《高宗实录》卷六七九,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戊寅(二十日)条。
〔25〕满文《寄信档》全宗三、编号一三○(二),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谕旨。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蒙古学信息》(呼和浩特)1997年02期第29-36页
【作者简介】〔日〕冈洋树
这样,大库伦办事大臣在清朝对喀尔喀统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意外的是,以往对此缺少专门研究,只能举出李毓澍的《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3〕、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而已〔4〕。特别是关于其设置时期及情况,除上述二人,几乎没有全面概述,只是在另外题目的论文当中有所提及。连李氏也认为,大臣职务不是一时形成,而是从设置的初期乾隆中叶开始至嘉庆年间逐渐完善的。且在这里,大臣职务在政治上的形成过程,也未必达到明确。因此本稿试图弄清楚办事大臣的设置和设置时喀尔喀的政治形势,以及设置大臣的政治意义。
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四三(原文为卷四三○,经核对应该是卷五四三——译者)兵部、官制载:
办事大臣二员。雍正九年,库伦互市处,驻司员经理。后改驻办事大臣一人。乾隆四十九年奉旨,增派大臣二人,同办库伦事务。系出特简,不为额缺。今设办事大臣二人。内一人系蒙古王公台吉兼任。
如上记载,至少于嘉庆年间,在大库伦设置了满洲大臣和蒙古大臣二人。其职责主要是:①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涉事务、国境防备(卡伦—国境哨所)管理;②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大库伦及沙比那尔(
 abinar呼图克图的属民)的事务;③管理大库伦、恰克图(Kiyaγtu)的汉商(乾隆四十二年以后);④喀尔喀东部二盟(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的事务(乾隆五十一年以后)。当初,在四项事务中前二者为其主要职责。自喀尔喀归附清朝以来,这些职责一直是由土谢图汗及其近族担任的,但历来被理解为由于库伦办事大臣的设置,这些职责被转移到大臣的职责内。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有错误的。因此,下文就所谓“蒙古大臣”、满洲大臣的形成过程逐个加以多方面的探讨。
abinar呼图克图的属民)的事务;③管理大库伦、恰克图(Kiyaγtu)的汉商(乾隆四十二年以后);④喀尔喀东部二盟(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的事务(乾隆五十一年以后)。当初,在四项事务中前二者为其主要职责。自喀尔喀归附清朝以来,这些职责一直是由土谢图汗及其近族担任的,但历来被理解为由于库伦办事大臣的设置,这些职责被转移到大臣的职责内。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有错误的。因此,下文就所谓“蒙古大臣”、满洲大臣的形成过程逐个加以多方面的探讨。一、关于“蒙古大臣”
根据通常说法,蒙古大臣是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七日的谕旨里任命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王公桑斋多尔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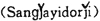 开始的〔5〕。其根据是道光二十年(1841)成书的噶尔丹(γaldan)所著喀尔喀编年史《宝贝念珠》(Erdeni—Yin Erike,以下略作EE )里所记载的下述事情〔6〕。
开始的〔5〕。其根据是道光二十年(1841)成书的噶尔丹(γaldan)所著喀尔喀编年史《宝贝念珠》(Erdeni—Yin Erike,以下略作EE )里所记载的下述事情〔6〕。乾隆二十三年寅年,春末月初七日下达了谕旨。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在大库伦虽有商卓特巴逊都布多尔济从行佛事,但对众多沙比那尔的管理,只有一个人是不够的。于是派遣喀尔喀副将军桑斋多尔济,守备库伦,管理呼图克图的沙比那尔,并协助处理和俄罗斯之间的边境事务。于是由Kiya—bkin(Kiyabsa夹子?)上奏, 在大库伦驻大臣是从此开始的。
EE的著者噶尔丹是土谢图汗部左翼后旗人,在旗印务处和盟长、副将军衙门担任书记。可以想象他自会接触过各处的公文之类〔7〕。 实际上,在这部编年史中,有许多记载引自公文。这就是本书作为清代喀尔喀史研究史料而被重视的理由。波兹德涅耶夫等许多研究者利用这部编年史的记载,认为蒙古大臣设置于乾隆二十三年,是有很大问题的〔8〕。
首先需要注意,在这段记载中,把派遣桑斋多尔济前往大库伦当作任命其为“大臣”这段值得重视的记载,并不是出自引用公文(在此为谕旨)的部分,而是出自噶尔丹自己的记述部分这个事实。就是说这个记载是事情发生90年后的记载。谕旨里只记载派桑斋多尔济前往大库伦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事务,却没有记载任命他为大臣。同样的记载可以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九,传三三,扎萨克多罗贝勒西第什哩列传以及以此为根据的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七、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五中看到,都均只记载派遣他的事实,却没有记载任命他为大臣〔9〕。
确认这个事实之后,查阅其它汉文史料,特别是查看《高宗实录》,在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条里没能看到EE所记载的上述谕旨,却发现了能够说明在此之前桑斋多尔济已经在大库伦处理事务的记载。例如,《高宗实录》卷五三五,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戊午(二十七日)条里载:
谕军机大臣等,据桑斋多尔济奏称,俄罗斯边界事务,每年照例派员会办。前所派侍郎瑚图灵阿,未经会办而归。今准彼处毕尔噶底尔雅古毕文称,今年会办时,仍否出派官员,上年前来之大臣,仍来与否等因。或由桑斋多尔济派本部落扎萨克等,或另出派大臣官员,请旨定夺等语。(中略)桑斋多尔济,乃喀尔喀副将军,且系承办俄罗斯事务人员。著即派伊前往会办,不必另行出派。
于是桑斋多尔济不仅可以奏报俄罗斯毕尔噶底尔雅古毕的询问,而且皇帝也针对所奏称他为“承办俄罗斯事务人员”,准其可以和俄罗斯进行协议。
另外乾隆针对桑斋多尔济在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于四月十五日的谕旨里说:
……还有,关于施恩逊都布多尔济一事,最近朕已经赐给逊都布多尔济以绢布。桑斋多尔济只须指示他,使他处理事务就足够了。朕允准上奏。在其他方面应施恩时,还要适当施恩。把这个命令通知给桑斋多尔济。此后桑斋多尔济处理盟内事务时,只须遵从朕的谕旨,既要通情达理,又要深思熟虑,迅速处理,不准丝毫软弱〔10〕。
从此可得知同时期桑斋多尔济已被任命监督大库伦事务。在《高宗实录》卷五五四、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己亥(十二日)的谕旨里有进一步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据桑斋多尔济奏称,商卓特巴逊都布多尔济等,请将扎木巴勒多尔济,掌管经教,众心悦服等语。著照所请,将堪布诺门汗之印,给与扎木巴勒多尔济掌管,勤宣黄教,约束喇嘛。其商卓特巴逊都布多尔济,著协办事务。
从这一点可以得知他也参与了大库伦堪布诺门汗的人事工作。
这样就明确了桑斋多尔济在EE所记载的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以前已驻在大库伦,处理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涉及大库伦管理事务。那么,他在什么时候担任该职务的呢?有关桑斋多尔济就任时间,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月折档》当中他本人的奏折能够确定。即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奏折载:
臣桑斋多尔济谨请谕旨。正月十五日从京师出发,因公琳丕勒多尔济处理库伦事务,于二月初八到达库伦,拜受喀尔喀左翼兵管掌副将军印。臣将如何处理俄罗斯和汉商事务,由臣处通知了定边左副将军印务代理郡王车布登扎布〔11〕。
可以判断他就任于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但这是否即蒙古大臣设置的时间呢?仍然留下疑问。因为上述奏折中桑斋多尔济到达大库伦后接受了喀尔喀副将军印信,而有关大臣之事却丝毫没有提到。从上述奏折可以明白,他从这时期开始处理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涉及汉商事务。因此是否可以认为他不是作为大臣,而是作为喀尔喀副将军处理这些事务的呢?使这个疑问更为强烈的是下面的事实。
如在上述桑斋多尔济的奏折里所提到的那样,当时土谢图汗部辅国公琳丕勒多尔济(Limpildorji)已经在大库伦担当着事务。 该人物有同部副将军参赞头衔。 桑斋多尔济的副将军任命是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闰九月〔12〕,但此后由于处理青衮扎布(
 inggünjab)之乱善后,不能够赴任大库伦。因此也可以认为琳丕勒多尔济以副将军参赞,代理着桑斋多尔济的职务。然而参考《王公表传》卷五一、传三五、扎萨克一等台吉班珠尔多尔济列传,琳丕勒多尔济于乾隆二十二年被任命为副将军参赞,而前一年即二十一年就开始在大库伦“协理”和俄罗斯之间的事务。所谓“协理”指的是协助当时处理这些事务的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如果认为他在副将军任命以前,在大库伦已有职务,那么该职务和副将军参赞没有关系,因此也就可以认为该职务和副将军职务也没有关系。由于这种事实,不能说大库伦的事务属于副将军权限之内。
inggünjab)之乱善后,不能够赴任大库伦。因此也可以认为琳丕勒多尔济以副将军参赞,代理着桑斋多尔济的职务。然而参考《王公表传》卷五一、传三五、扎萨克一等台吉班珠尔多尔济列传,琳丕勒多尔济于乾隆二十二年被任命为副将军参赞,而前一年即二十一年就开始在大库伦“协理”和俄罗斯之间的事务。所谓“协理”指的是协助当时处理这些事务的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如果认为他在副将军任命以前,在大库伦已有职务,那么该职务和副将军参赞没有关系,因此也就可以认为该职务和副将军职务也没有关系。由于这种事实,不能说大库伦的事务属于副将军权限之内。说来,喀尔喀副将军是从雍正二年(1724)准噶尔战争中作为喀尔喀兵2000人的指挥,由土谢图汗部郡王丹津多尔济(Danjindorji)、和赛音诺颜部(当时仍属于土谢图汗部)亲王策凌(
 ering)、 扎萨克图汗部贝勒博贝(Bübei)三人被任命开始的。后来车臣汗部也有被任命的,所以到赛音诺颜部独立,便形成了各盟设一名副将军的情况。从副将军的性质考虑,该职务没有监督和俄罗斯的交涉、以及恰克图事务的必要性。
ering)、 扎萨克图汗部贝勒博贝(Bübei)三人被任命开始的。后来车臣汗部也有被任命的,所以到赛音诺颜部独立,便形成了各盟设一名副将军的情况。从副将军的性质考虑,该职务没有监督和俄罗斯的交涉、以及恰克图事务的必要性。副将军在大库伦的任务,是以什么样的权限为基础的呢?有一重要的事实可以参考。即乾隆三十年(1765)由桑斋多尔济等进行的有关和俄罗斯之间的秘密贸易事件。同年四月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发现往来于乌里雅苏台的商人拥有大量的通过当时已被停止的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才能购入的皮革制品,于是就奏报了。以此为开端由桑斋多尔济、满洲大臣丑达等进行的和俄罗斯的秘密贸易被发现,桑斋多尔济被削爵,而且被软禁在北京〔13〕。为调查这件事情而赴大库伦的理藩院额外侍郎、内蒙古喀喇沁左(原文为右,经查阅应该是左——译者)翼旗扎萨克瑚图灵阿(Hütüringga)被留在当地,以副将军代理处理事务。
同年十月继桑斋多尔济后,任为土谢图汗的车登多尔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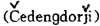 ,被任命为本部副将军, 此时瑚图灵阿上奏请示自己是继续留任,还是回去。即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他的奏折里说:
,被任命为本部副将军, 此时瑚图灵阿上奏请示自己是继续留任,还是回去。即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他的奏折里说:……由理藩院发送,十一月二十五日到达的文书里,有对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副将军缺位,任命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的谕旨。臣把(该文书)直接送到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处,而车登多尔济于十二月十一日来到库伦,拜受了由臣和尚书阜乃(Funai)授与的副将军印玺和箭证。 ……经查看以前的谕旨,命臣瑚图灵阿代理副将军。现在则把印玺交给了车登多尔济,因此臣是继续驻在库伦,和他们一起处理事务,还是归还京师呢?等候圣主陛下下达谕旨,敬谨遵行。……对此,所奏有误,故朝中下达了谕旨〔14〕。
由此可以明确,瑚图灵阿理解大库伦的事务归属副将军职务内。因此,当车登多尔济正式被任命为副将军时,他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已完成,应该回去。针对这一点乾隆认为瑚图灵阿的奏报有误解。遂在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谕旨里说道:
他(瑚图灵阿—冈)是朕专门派往库伦承办事务的,诸多俄罗斯边境大事和呼图克图沙比那尔的事务,均应由他承办。喀尔喀副将军,最多不过处理其盟内的事情,而处理如此重大的事情能行吗?不仅如此,车登多尔济尚幼,能有什么经验呢?任命他为副将军,是根据当时形势而决定的,并不是信赖他而使他处理事务。任命他,只是想使他学会处理事务。对处理库伦事务和俄罗斯边境诸大事,则由瑚图灵阿等指挥处理。副将军印玺仍旧交给车登多尔济,使他随瑚图灵阿等学习处理事务。瑚图灵阿等上奏各种事情和送往文书时,则使用副将军印。还有,以前桑斋多尔济承办库伦事务时,他又是御前行走,所以上奏时把他名字写在前面,完全不是因为他是副将军就把名字写在前面。从此以后,上奏时把瑚图灵阿的名字写在前面,然后写阜乃、 车登多尔济的名字〔15〕。
总之,乾隆皇帝所说的桑斋多尔济在大库伦的职务并不归属土谢图汗副将军权限,而是基于皇帝对桑斋多尔济的信赖。所以尽管车登多尔济被任命为副将军,但并不意味使他自动承担库伦事务。而且车登多尔济尚幼,不足信用。所以使瑚图灵阿继续留在大库伦,处理事务。然而皇帝接着又说使车登多尔济学习处理大库伦事务,而且来往文书时使用副将军印,这只能说前后有矛盾。
看来,乾隆皇帝要说的大概是桑斋多尔济在大库伦的办事,不是根据清朝官制范围内的官职,而和这个分别开,派遣值得依赖的桑斋多尔济承办大库伦事务。那么我不得不想起下面的事实。即开头时说的那样,喀尔喀部归附清朝以来,和俄罗斯的交涉事务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大库伦的管理,无非是一直由土谢图汗家族及其近族王公承担的。世代的土谢图汗和丹津多尔济等王公一直在管理这些事情,但去并没有被授予清朝官制内的某种官职。他们作为代表喀尔喀的有力王公,的确是由于这种资格,被清朝委任处理和俄罗斯的交涉事务,还有因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和二世出于本家族而担任呼图克图及大库伦的管理事务。派遣桑斋多尔济到大库伦只能理解为这种政策的继续。对清朝来说重要的在于他是代表喀尔喀的有力王公。从他的家族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喀尔喀归附清朝时立过功的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弟弟西第什哩就是他的祖辈,而他祖父丹津多尔济是在准噶尔战争中有战功的人,桑斋多尔济本人是由其母宗室公主在北京带大的,而且他自己也是亲清派,对抗由三汗家族代表的喀尔喀既成权威,他是最合适的人物〔16〕。
这样的间接统治体制,此后也在继续着。乾隆三十六年(1771)桑斋多尔济恢复该职务时,不但没有被任命为大臣的特别迹象,连副将军也没有被任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桑斋多尔济死后,继承他的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仍没有被任命为大臣的迹象。这件事情表明了乾隆皇帝至少在形式上维持间接统治体制的企图。然而桑斋多尔济由于其过份露骨的亲情态度,和其他王公,尤其是和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及土谢图汗家族的众多王公发生了冲突。针对由此而发生的政治不安,清朝被迫采取某些对策。
如上所述,一直被认为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设置的蒙古大臣,实际上一直由土谢图汗家族承担的,和俄罗斯的交涉事务以及对哲布尊丹巴、大库伦的监督事务,只不过是由桑斋多尔济承担了而已,这丝毫不意味大臣职务的新设。
二、满洲大臣的派遣及其意义
第一任满洲大臣是诺木珲(Nomhon),根据波兹德涅耶夫等所依据的EE,他是按照乾隆二十六年(1761)冬中月二十二日的谕旨,被派往大库伦的。即:
二十六年冬中月二十三日,下达了谕旨。桑斋多尔济现有建设寺庙(的任务),他一个人不能够处理事务,上奏请求派一位大臣来共同处理事务,现派遣诺木珲让他与桑斋多尔济共同处理事务。几年替换一次、如何分给粮食等,由军机大臣协议上奏。库伦满洲大臣是从此开始的〔17〕。
一方面《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七四六,理藩院·俄罗斯互市、松筠《绥服纪略》、何秋涛《北徼喀伦考》·《北徼事迹表》下、《清史稿》卷五二六,列传三○七,藩部列传四,土谢图汗部列传、张穆《俄罗斯事补辑》均记载是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的。不过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上谕档》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条里,发现和EE完全相同的谕旨,因此认为任命谕旨下达于乾隆二十六年是正确的。只是受皇帝的命令后,经军机大臣通过协议作出答复已是进入乾隆二十七年的事了。《会典事例》等记为乾隆二十七年大概是这个原因〔18〕。
而问题则是其设置的理由。如在上述谕旨里所说那样,设置满洲大臣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给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建新寺庙而事情繁多,但其背后在喀尔喀内部存在着桑斋多尔济派王公和其他王公,特别是和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等之间的对立和抗争〔19〕。大约一年后的乾隆二十七年冬天,诺木珲被青衮扎布告发而被解任。从当时的谕旨可以看到下述情况。
……派诺木珲到库伦,正是因为前据青衮扎布所奏桑斋多尔济驻在库伦处理事务当中,有诸多不正之处,而被哈尔哈齐控告。朕因其身系蒙古人,没给处分。念其虽有错误,若从内地派大臣,随同办事,自可得以匡正。因命诺木珲前往。现诺木珲在当地狂妄胡乱不能容忍。应当派遣人员,调查处理〔20〕。
所谓哈尔哈齐是库伦喇嘛官位,直译为门卫,可能是商卓特巴等库伦高官的类似侍卫的官职〔21〕。当时向青衮扎布告发诺木珲的哈尔哈齐似乎接受了大库伦商卓特巴逊都布多尔济的指示。据桑斋多尔济说这个人物是当时的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的叔父,在喀尔喀内部居于长老地位。桑斋多尔济在他的奏折里控告逊都布多尔济,与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和土谢图汗部亲王达喜丕勒等勾结,在每件事情上和桑斋多尔济作对,企图夺取他的地位。而且逊都布多尔济在父亲血缘上虽和青衮扎布没有关系,但在母亲血缘上有亲近关系。从而明确了在喀尔喀王公内部存在着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反对桑斋多尔济派别的事实,桑斋多尔济在喀尔喀内部处于孤立地位〔22〕。
这种事情就清朝对当时喀尔喀政策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利用喀尔喀王公统治喀尔喀的间接统治,若该王公没有一定的声望,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被孤立起来,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这样反而会使其他王公以反对傀儡立场聚集在一起。那么这就意味着喀尔喀王公的反清结合的形成。桑斋多尔济本人没有做到和喀尔喀内部其他王公协调一致,反而以大库伦为中心聚集了自己的亲近人员,并直接联系清朝权力,与反对派对立。清朝如果希望维持其历史的间接统治体制,必须由更稳当的王公来代替桑斋多尔济或使桑斋多尔济改变态度,乾隆皇帝选择了后者。可是从北京又不可能直接监视他,所以派遣满洲大臣,其意义就在这里。因此这时的满洲大臣被禁止过深介入喀尔喀内部事情,诺木珲被告发时皇帝说道:
由青衮扎布处上奏,为准备来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化身)赐给受戒喇嘛的物品,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等和诺木珲协议,从喀尔喀四部征收了一千两银子,诺木珲竟然检查呼图克图的物品并拿走了水獭等毛皮。这是很可笑的事情〔23〕。
诺木珲系驻库伦之人,所有招请呼图克图化身、因受戒征收银两等事,即使伊所应管,亦不过共同与闻而已,乃竟从中任性滋事,并少给商卓特巴价值,勒买如许绢布、毛皮,复借贷银两,至于修理伊住房一节,理应奏闻官给办理,伊又擅用喇嘛工价并纵容领催及家人恣意索银甚属无耻,卑鄙不堪〔24〕。
皇帝除了责备诺木珲乱用权力搜刮钱财外,还责备他参加有关大库伦问题的协议和检查呼图克图物品。
代替由于这件事情而被解任的诺木珲,派往库伦的是福德(Fude)。这个人物上任半年后又被解任了,其理由据说是因为对待喀尔喀王公态度傲慢。福德在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上任后,向皇帝建议要把喀尔喀归附时的谕旨重新读给王公们听。然而受到了皇帝的指责:
这是应由所有喀尔喀王公协议处理的事情,桑斋多尔济系喀尔喀人,他自己会见大家解决这件事情即可。福德为什么要参与呢?命令福德不要参与这件事情〔25〕。
在这里皇帝明言喀尔喀事情应由系喀尔喀王公的桑斋多尔济来管理,并不属于福德管辖内。但是福德并没有从这里吸取教训,又想把内地礼制强加于喀尔喀王公,致使皇帝愤怒,被解任。
就这样,满洲大臣的任命不是以夺取桑斋多尔济所主管的权力为目的的,而是为了阻止他的暴行,以维持旧制。但被派遣的大臣们没有能够理解这个目的,再三干涉喀尔喀内部事情,乱用权力,不正当搜刮钱财,强制实行内地礼仪。桑斋多尔济被解任后代替他上任的瑚图灵阿把大库伦的任命理解为属于副将军权限内,也是因为没能理解乾隆皇帝所意图的喀尔喀政策。满洲大臣本来是以对应管理大库伦事务的桑斋多尔济给与辅佐、监视为目的被派遣的,由于这种性质,没有定额,而是临时职务。可是喀尔喀的形势没有向皇帝所想象的方向发展,反而王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桑斋多尔济乱用权力,和俄罗斯进行秘密贸易,最终失势。由于喀尔喀的这种政治危机,满洲大臣在此以后仍继续被任命着。
结语
综上所述,历来被认为的由桑斋多尔济被派遣到大库伦而开始的大库伦蒙古大臣的设置,不是EE里所记载的乾隆二十三年三月的事,而在前一年他已在大库伦承担处理事务,但那也不是以大臣的资格进行的。派遣他,只不过是一直由土谢图汗部有力王公委任的,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涉事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大库伦管理政策的继续,并不意味任何新官职的设置。但是对由于过份的亲清立场在喀尔喀内部被孤立起来的桑斋多尔济,产生了以某种形式从中央给予支持的必要,因而被派遣的是大臣诺木珲。所以满洲派遣大臣不是象以往理解的那样,以夺取蒙古大臣的权力为目的,而是要辅佐桑斋多尔济并阻止他的暴行。确实从那以后大库伦实权移到了满洲大臣的手里,但那是桑斋多尔济死后进入乾隆四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像我曾经研讨的那样,乾隆四十年间通过《将军、参赞大臣、盟长、副将军办理事务章程》的制定和划定牧地,在制度上强化了对喀尔喀的统治。继桑斋多尔济之后上任的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在乾隆四十九年被解任,从此,实权名副其实地移入了满洲大臣的手里。乾隆二三十年间,乾隆仍继续其对喀尔喀的间接统治,而且企图宁可维持它。任命派遣满洲大臣也正是反映了清朝对喀尔喀的这种政策,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够取得和其它政策的整体性的理解。本稿确认了以上问题,暂时停笔。
(附记)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览史料期间,提供帮助的鞠德源先生和同馆的诸位,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杜荣坤先生深表谢意。
(说明)原稿注释当中的俄文、新蒙文由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翻译——译者。
乌云格日勒 佟双喜 译自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清朝与东亚细亚》山川出版社 1992年3月
注释:
〔1〕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蒙Qola dakin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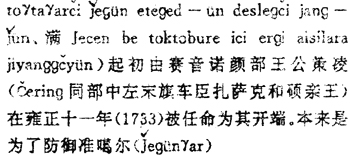 而设立的军官,同时带有行政官的性质。作为对其设置过程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有李毓澍的《定边左副将军制度考》(《外蒙政教制度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九六二年,台北,一—一○三页)。在该任中,继策凌之后有其子成衮扎布
而设立的军官,同时带有行政官的性质。作为对其设置过程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有李毓澍的《定边左副将军制度考》(《外蒙政教制度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九六二年,台北,一—一○三页)。在该任中,继策凌之后有其子成衮扎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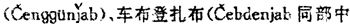 右旗代钦扎萨克多罗郡王)相继被任命该职务。对此可以参考Veronika Veit :《十八世纪喀尔喀蒙古乌里雅苏台将军》(《国立政治大学国际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一九八五年,台北,六二九一六四六页)。在策凌的经历当中有和桑斋多尔济的经历极其相似的地方。我认为对策凌和当时清朝对喀尔喀政策有必要再考证。笔者已在拙稿《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和他的立场——作为清朝对喀尔喀蒙古政策研究的导论》(《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哲学、史学编、别册第十三集,一九八七年一月,一六七—一八○页)。论述了任命青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的清朝对喀尔喀间接统治的性质。一方面同样的性质在策凌任职时更为明显,同时有必要考虑和准噶尔临战乃至临战形势下喀尔喀军事协力的必要性以及特殊性。换言之,如何理解对准噶尔战争要动员喀尔喀,却不依靠已形成的汗权威,敢于创立定边
右旗代钦扎萨克多罗郡王)相继被任命该职务。对此可以参考Veronika Veit :《十八世纪喀尔喀蒙古乌里雅苏台将军》(《国立政治大学国际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一九八五年,台北,六二九一六四六页)。在策凌的经历当中有和桑斋多尔济的经历极其相似的地方。我认为对策凌和当时清朝对喀尔喀政策有必要再考证。笔者已在拙稿《定边左副将军青衮扎布和他的立场——作为清朝对喀尔喀蒙古政策研究的导论》(《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哲学、史学编、别册第十三集,一九八七年一月,一六七—一八○页)。论述了任命青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的清朝对喀尔喀间接统治的性质。一方面同样的性质在策凌任职时更为明显,同时有必要考虑和准噶尔临战乃至临战形势下喀尔喀军事协力的必要性以及特殊性。换言之,如何理解对准噶尔战争要动员喀尔喀,却不依靠已形成的汗权威,敢于创立定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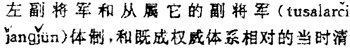 朝政策的特点是个问题。在这里把它作为今后的课题提出,待于考究。
朝政策的特点是个问题。在这里把它作为今后的课题提出,待于考究。〔2〕有关大库伦概说有A.A.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 第一卷,圣彼德堡,1896;普·都古尔苏隆《乌兰巴托市历史》首都,库伦,乌兰巴托,1956;(札奇斯钦中文翻译《库伦城小史》,《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四,一九七三年)还有关于作为寺院的大库伦,参考斯·普日布扎布《革命前的大库伦》(历史—财政编)乌兰巴托,1961。
〔3〕李毓澍《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一○五—一八四页。
〔4〕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弘文堂, 一九二六年)五二一六三页。
〔5〕A.A.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67页;И.Я. 兹拉特金《近现代蒙古历史论集》,莫斯科,1957,124—125页;策·索德诺木达格巴《满洲统治之下的外蒙古行政组织》(1691—1911),乌兰巴托,1964,33页;斯·普日布扎布《革命前的大库伦》,47—48页;策·那顺巴勒珠尔《外蒙古向满清进纳的贡品》(1691—1911年),乌兰巴托,1964,187页;G.C. 戈罗和娃《满族统治下的蒙古历史论集》,莫斯科,1980,39—40页;A.奥其尔《1911年蒙古人民为民族自由、独立的战争》(资料汇编)(1900—1914),解释298页,乌兰巴托,1982;李毓澍《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
〔6〕噶尔丹《额尔德尼额日克》(γaldan Erdeni yin erikekemek ü te üke bolai )Monumenta Histories Tamus Ⅱ, Fasciculus 1,乌兰巴托,1960,127页a—b面。
〔7〕同上策·那顺巴勒珠尔的序文。
〔8〕注〔5〕所举出的文献几乎都没有对大臣设置的时期加以考证。只不过根据EE的记载加以叙述。但是李毓澍把波兹德涅耶夫引用EE所叙述的部分和陈箓的《蒙古逸史》相对照,“辞句之间虽与逸史略有出入,但时间与内容,则均与逸史相符”(一二九页),因此认为乾隆二十三年设置了蒙古大臣。然而象石纯滨太郎早已叙述的那样《蒙古逸史》是否和EE属同一系统史料,或是抄译呢?不能否定这一可能性,因而李氏所采取的方法有问题(石滨纯太郎《蒙古逸史原本》,《艺文》第十年第七号,1919年7月)九○—九六页。另外, 可以参考中见立夫《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史料价值——博格多汗制蒙古国时代中国方面若干史料的考察》(《史学杂志》八五—八,1976年8 月)五一—六八页;石滨纯太郎《蒙古逸史考》(《龙谷史坛》二九,1942 年7月)三三—四○页。
〔9〕两书记载完全相同, 即“二十三年赴库伦协理俄罗斯边境事”。
〔10〕《由青衮扎布领导的外蒙古独立斗争(1756—1758)》(手稿汇编)齐木德编,乌兰巴托,1963,36号88—91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全宗三、编号八七(二)。
〔12〕《高宗实录》卷五二三,页三上一下,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癸丑(十八日)条。
〔13〕关于该事件概要参考拙稿《乾隆中叶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统治的强化和桑斋多尔济》(《东洋学报》,六九一三、四,1988年)。
〔14〕满文《月折档》全宗三、编号一五三(二)。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寄信档》全宗三、编号一三一(三)。
〔16〕关于桑斋多尔济参考注〔13〕拙稿。
〔17〕EE128页b面。
〔18〕中国方面的史料重要的是一贯把乾隆二十六年乃至二十七年的诺木珲的派遣认为办事大臣的初设,例如何秋涛在《北徼喀伦考》里叙述“是时库伦尚未派驻大臣,凡喀伦事务,俱系办理夷务之喀尔喀王统辖,至乾隆二十七年,始设钦差大臣驻库伦,专理恰克图贸易事。”还有矢野仁一认为比此文更为可靠的松筠《绥服纪略》里写道:“先是库伦所属边卡戌守年久凋散。乾隆二十二年,有前办夷务喀尔喀王丹津多尔济之孙桑斋多尔济,遵旨统理。因竭力整顿,安设卡伦,始克完善。迨后,夷务繁多,始驻钦差大臣,同桑斋多尔济总理其事,一切仰遵圣训,自是永为定例。”把满洲大臣派遣认为是“始驻钦差大臣”。换言之中国方面的史料没有记载桑斋多尔济为大臣。
〔19〕关于在乾隆二十年代展开的两者抗争的原委,俟在其它稿子里详细论述。
〔20〕满文《寄信档》全宗三、编号一二九(五)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谕旨。《高宗实录》卷六七九、页四上,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戊寅(二十日)条。
〔21〕汉文史料中有“哈尔哈齐”,大概是蒙语的哈戈勒戈其(qaγalγa
 i),参考田山茂《蒙古法典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7年)二九八页、注。
i),参考田山茂《蒙古法典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7年)二九八页、注。〔22〕满文《月折档》全宗三、编号一三六(二),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桑斋多尔济的奏折。
〔23〕满文《寄信档》全宗三、编号一二九(五),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谕旨。
〔24〕满文《上谕档》全宗三,编号一一○七(一),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谕旨,《高宗实录》卷六七九,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戊寅(二十日)条。
〔25〕满文《寄信档》全宗三、编号一三○(二),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谕旨。
